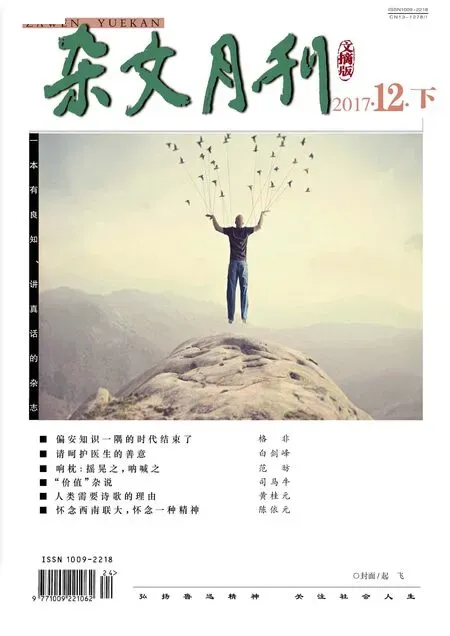茶客留言
想看最好的雜文,就訂《雜文月刊》
傅春貴(福建寧化)
一年一度的報刊征訂季節剛到,我就去郵局首先續訂上了一份2018年的《雜文月刊》。為何我如此速度去訂閱她呢?是因為這份雜志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她可讀性強,有特色,刊物有品位,從內容的選編至雜志的整體設計,一直深受我的喜愛。雖說她的外表不算華麗,但她卻含而不露,柔而不嬌,美而不艷,雅而不俗。她有時像一陣春風,讓我心花怒放;有時像一縷陽光,照耀著我人生的前進方向;有時像春雨,滋潤我的心田;有時則像一位良師益友,給我指點迷津,引導我們如何去為人處世。
《雜文月刊》,只有訂閱了才知道好看,這是我訂閱多年的真實感受。在此,我想向喜愛閱讀雜文的朋友們說幾句心里話:要想花有限的錢,看最好的雜文,就去訂閱一份《雜文月刊》,她的魅力會潛移默化地感染你,讓你變得聰明、理智、敏銳,具有獨有的品性和風骨。敬請訂閱,特此推薦!
為每個努力的孩子驕傲
苗志學(陜西佳縣)
讀《雜文月刊》文摘版2017年10月下,司徒偉智的文章《換一副眼光看“成功人生”》,我感觸很深。文章有一段話:杜魯門當選美國總統后,記者下鄉采訪其母親如何為兒子自豪,豈料她道:“我還有一個兒子,同樣使我自豪。他在哪里?正在地里收土豆。”真是一位豁達高尚的母親。
我沒有去過美國,對美國的國情不了解。在我們這里,兒子大小當個官,母親都會感到自豪,感到兒子爭氣,光宗耀祖。兒子當個農民,母親恐怕就沒這樣的感覺了。當官和務農,現實中給人的感覺很有落差。我覺得我們應當學學杜魯門的母親,轉變觀念,只要孩子努力工作,誠信做人都是父母的驕傲。
形式主義不能泛濫
梁勤學(山西運城)
受托編撰方志,荷重未敢懈怠。今年少讀了別的書,也幾乎不寫個人的東西了。但是《雜文月刊》仍是堅持拜讀的,又見重點標記的2017年6月下文摘版《扶貧不能糊弄》一文,重溫,同感不發似如有鯁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是甚感作者何君林先生敢于提出問題,對于當下一些地方扶貧中的形式主義提出尖銳的批評。同時以為問題并不只在《扶》文所指之地,實際上問題是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一個地方的窮困,幾十年來極少有人問津,忽地一遇應付檢查視察或重要活動,就來個公路邊沿路“嚴格”整治。而在背后掩蓋著的卻不只是衛生環境的臟亂差,甚而是房倒屋塌的窮困危境。另外,現在供農民使用的集體場地沒有了,一些秸稈還有用,農民涼在路邊門口,檢查時有妨“美麗”,就先藏起來,檢查一過就又給攤上了。
《扶》文的一個問題提得好:“都說早年間的扶貧,由于形式主義的泛濫,導致扶貧不見成效。沒想到現在都已經進入脫貧攻堅階段了,而仍有個別地方形式主義依舊泛濫成災……”在下是在鄉鎮工作過多年的,扶貧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早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就寫過此類批評形式主義的文章。其實那時一些地方的問題主要是不作為或作為不夠不力,大體上還不至于出現如今泛濫成災的形式主義面子工程“假作為”之害,可見當下的問題更值得引起各級部門重視。其次是此弊遠遠不止反應在扶貧上,不少的工作中同然。譬如抓黨建,有的小村僅只三兩百口人,而且不少的村民長期外出,不要說是群眾會,就連黨員會議都難開起。一個村委會三兩張桌子排在一起,上面滿滿地堆著一疊疊(數目約過200份)打印頂好的匯報表格材料,有的寫不成就湊,“扎扎實實”走過程。群眾沒人看,是讓檢查看的,基層干部疲于應付,有苦難言。
我們的工作所欠農村的太多,拉下了步子需要現在來補,所以扶貧變成了“攻堅”,長期性變成了緊迫性,方法上變成了精準扶貧,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滿打滿算還有三年。有人說到期建不成可以說成寫成。筆者堅信老百姓堅決不會要這樣“胡弄”和“糊弄”的“小康”。他們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小康,所以別再搞形式主義那種“套路”了,要為群眾真辦事,辦實事。
觸動我的三篇文章
李本華(湖南長沙)
《雜文月刊》文摘版2017年10月下這一期觸動我的有三篇文章。
一是《用生命贏得的誠信》。瑞士的雇傭軍以作戰勇敢,絕不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名揚天下,沒有想到瑞士銀行業的興盛與之有因果關系。也是的,為了誠信,連命都不要,且有幾百年的傳統,把錢存到他們銀行里自然是最放心的了。實際上,瑞士銀行的誠信也是名揚天下的。誠信,不欺騙,干事就一定最認真。只要認真,什么事都可以做到最好。瑞士手表不也是名揚天下嗎?“誠信”實在重要。
二是《戒尺回歸》。張老師十分勇敢,支持用戒尺懲罰犯錯誤的孩子。她認為,挨過戒尺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戒尺的羞辱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蘇聯的教育家馬卡連柯也打過學生,認為打是“閃電教育”。世界各國對戒尺有不同的態度。韓國老師有戒尺,美國有兒童保護法。我則認為老師不能擁有戒尺。家庭有無戒尺,沒有誰過問,也應該盡量少用。
三是《沒有人性不配叫圣人》。圣人也者,知行完備、至善之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連愛幼的人性都沒有,當然不配叫圣人。一針見血!太好了。
《我懺悔》警示意義非同尋常
李增錄(河北任丘)
從頭至尾讀罷《雜文月刊》文摘版2017年9月下的所有文章,可以說每篇都有所獲。尤其是對“警示檔案”欄目的首篇《我懺悔》一文,我翻來覆去讀了好幾遍,越讀感觸越深,越讀越覺得警示意義非同尋常。
該文作者高深先生,從1964年10月27日發表在地方報紙副刊的《從文嫂的遭遇談起——駁〈早春二月〉的活命哲學》一文,用現在的眼光進行懺悔。讀了文章,不由勾起了我心中的波瀾。
從文章的口氣判斷,我和作者是同齡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們被“階級斗爭”鼓動得熱血沸騰。當時,我26歲,在縣城中學教導處工作,因為正值青春年華,精力充沛,工作之余愛寫日記。至今,我還保留著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期間的日記。今天,我翻看這些日記,除了那些言不由衷的話語和漂亮的口號外,就是“學毛著”、學先進人物的感想,再不就是“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內容……都是那些表現自己思想如何先進的話語。因為那時我正在申請入黨,口頭上說是“為人民服務”,其實質卻是為了“撈黨票”,進而升官發財。經過萬般努力,目的沒達到,便在隨之而來的那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了,先整人,后挨整,把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耗費掉了……
回想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正如文中所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做過一些錯事。若要找個借口的話,可以叫當事者迷,或者是說受了某些說教的蒙蔽——其實無非是為了保護自己,甚至純屬投機。”所以,我也要懺悔。
《李約瑟之問》言之有理
郭樹榮(山東濟南)
《雜文月刊》文摘版2017年10月下所發禾刀先生寫的《李約瑟之問》,言之有理。
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時代,之所以科技不發達,蓋在于彼時中國是一個穩定的農業社會,“民以食為天”,天有了,便什么都有了,而且更有把科技鄙視為“奇技淫巧”的觀念存在,加上考取官員,也是考“文章”,而不以科技取人才,故而科學技術、科技人才不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