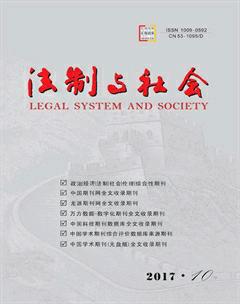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的負面效應分析
摘 要 改革開放后,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各種社會問題也隨之產生,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就是其中之一。適度的貧富差距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但如果差距過大,就會造成種種負面影響。本文從貧富差距對社會個體的影響切入,討論了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帶來的負面效應。
關鍵詞 貧富差距 社會流動 社會態度 個體心態
作者簡介:張融融,中共淮安市委黨校,講師。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0.308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窮人和富人在收入和財富上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按照國際上常用的基尼系數指標,我國的基尼系數自2008年達到峰值后,雖然總體呈下降趨勢,但始終處于0.4的警戒線以上,2016年達到0.465,中國的貧富差距情況仍然較為嚴重。貧富差距不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收入或財富差異,也是一種社會差異,社會成員因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差距造成了心態、階層、地位等多方面的變化。貧富差距過大將會帶來若干負面效應,造成社會流動減少,影響社會成員的社會態度和個體心態,非常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一、貧富差距過大減少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是個體或群體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移動,社會流動性高或低的判斷標準在于社會中有多少出身低微的人能夠憑借自己的努力實現階層攀升。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鼓勵人們開拓創新,為絕大多數人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底層民眾向上流動增多。但近些年來,由于忽略了公平的原則,最終造成了城鄉間、代際間、階層間貧富差距的固化,進而影響了社會流動。
(一)農民不易融入城市
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僅僅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卻沒有解決農民的富裕問題。與城市相比,農村的收入低,社保和福利少,農民要想獲得更多的收入和保障,只能通過進城打工來實現。但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并沒有成為城市居民中的一員。一方面,農民工沒有能力在城市安家。由于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基本都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打工,工資收入有限,他們基本沒有能力在城市購房安家。
另一方面,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生活圈。他們大多選擇租住城中村等租金便宜的地方,這里在人際關系、生活習慣、文化氛圍等方面和城市居民有很大差異。而且,農民工的流動性強,他們很難長期留在一個城市,亦很難融入當地生活。
(二)代際向上流動減緩
當下,“窮二代”、“窮三代”也引發了社會關注,在這背后,折射出社會階層代際流動的減少。對于大多數底層群眾的子女而言,教育是其獲得上升的唯一途徑。但是,教育市場化使城鄉學校、重點和非重點學校之間的教學條件和教學效果都存在差異,而以均衡教育資源為目的的學區劃分,并沒有給底層民眾提供相同的教育機會,富人比窮人更有能力進行各種教育投資。
當底層民眾感到教育改變不了身份地位時,往往讓孩子輟學去從事對勞動技能要求較低的工作。但是,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在市場上很難再有上升的空間。
(三)下層向上流動困難
改革開放初期,受改革“平等化效應”影響,我國貧富差距在一段時期內反而縮小(尉建文,2005),社會底層在改革中獲了利,還有機會由底層向上攀升。但是,隨著財富和資源在“先富群體”中日益積累,使窮人上升的難度日益加大。
上升難度加大主要來自市場對高效資本偏愛。早期創業中,富人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和資本,使他們在資源配置上更加高效,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現在,底層民眾即使有了“第一桶金”,也很難像前人一樣實現資本積累,他們無法與擁有高效資本的人競爭,只能從事一些小本生意。
上升難度加大還與知識經濟時代對人才的要求的變化有關。周曉虹教授認為,“由于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和科學技術的專門化,靠個人自學成才來形成具有優勢的人力資本的比例非常之低。”(周曉虹,2017)也就是說,底層人群如果不經過系統化、專業化的現代培訓和教育,他們很難靠自身努力成為現代精英,底層群體只能選擇一些對勞動技能要求低的工作。
社會流動的減少,將使底層民眾逐漸失去奮斗的期望,也容易產生絕望感。當個體向上流動的訴求逐漸聚集起來成為群體利益訴求時,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是一種威脅。
二、貧富差距過大改變社會態度
社會態度是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所普遍采取的態度,代表了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看法,對社會成員的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來,貧富差距持續加大造成了很多民眾對社會上的人或事的態度發生變化,不再相信市場機制下公平競爭的原則,出現了社會信任危機,影響了大眾的社會公平感。
(一)帶來社會信任危機
社會信任,是社會成員對他人行動合乎社會規則、規范的一種期待(福山,1998),較高的社會信任是維持社會互動和社會良性運行的保障,可以穩定社會情緒,減少社會交易成本。社會信任不足,將會影響到社會安全(馮仕致,2014)。目前看來,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信任危機主要集中在消費差距和風險分配的差異這兩方面。
其一,消費差距的影響。收入差距對消費增長速度有根本性影響(鄒紅、喻開志,2011),根據學者研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水平呈現出長期擴大的趨勢(曾國安、胡晶晶,2008)。消費差距對于社會信任的影響主要來自貧富群體在“公共消費”上的差異,這里的公共消費“是指城市居民基于政府提供的公共設施及資源所發生的個人消費,主要包括醫療、文教、交通三方面,近似于發展型消費支出。”(王克西、黨琳,2014)公共消費支出被認為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個體在身體、文化上的素質,有助于向上流動。公共消費差距越大,個體提升的機會差距就越大。雖然“機會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同經濟地位獲得的機會并不公平。缺少機會的底層群體往往會產生不公平的感覺,社會信任也會隨之瓦解。機會的不公平,還會使一些人采取非理性的行為去獲取財富,近年來引起熱議的殺熟、裸貸、傳銷、非法集資、電話詐騙、碰瓷等現象,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社會信任的認知。endprint
其二,風險分配差異的影響。風險是現代性的產物,與貧富分化相關聯的是,風險的分配呈現出與財富聚集顛倒的方式:“財富在上層聚集,而風險在下層聚集。”(烏爾里希·貝克,2004)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產生于兩種“脫域機制”——符號標志和專家系統——都以信任為基礎(吉登斯,2011)。但是,這兩種機制都是會受到財富影響,可以通過財富購買優先機會或操控標準或專家系統。因此,表面上是經濟實力造成的差異,其實是將自身的風險轉嫁給他人,是對風險的不公平分配。事實上,個體在某些領域風險的降低,與個體在其他領域風險的增加是并存的。因為,當所有人都有可能為了降低自己的風險而打破信任時——這對所有人來說就是風險增加。如此,將陷入信任和風險的惡性循環:為了降低自己的風險,不斷地打破信任,卻無法避免自己在其他方面風險的增加。在各種風險的交叉作用下,總體風險也在增加,逐漸引發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并最終指向對政府治理能力、社會文化的不信任。
(二)社會公正感降低
社會公正感是個體對社會公正的主觀判斷和反映,包括人們對社會分配、社會政策和措施公正與否的認識。貧富差距過大對人們社會公正感的影響主要源自官員腐敗和既得利益群體對利益的壟斷。在很多人看來,商人和官員之間進行交易,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這種利益交換,剝奪了大眾的公平競爭和公平發展的機會,使利益流向少數群體。面對這種潛規則,不只是普通大眾,就是社會頂層都缺乏社會公正感。這將造成人們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甚至進一步演化為成仇官、仇富情緒。
三、貧富差距過大引起個體心態變化
貧富差距過大時,底層和上層在收入、財富和地位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懸殊,影響了個體的心態,有兩種心態需要引起重視。
(一)強勢群體產生弱勢心態
早在2010年,一項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的調研結果就顯示,在對黨政干部、知識份子、公司白領進行調查時,這三類人群中認為自己屬于“弱勢群體”的分別占45.1%、55.4%和57.8%,這說明以往的“強勢群體”也產生了弱勢感,出現了弱勢群體泛化現象。產生這種心理反應,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在一定情境中產生了類似于弱勢群體心理狀態的弱勢心態,而把自己歸于弱勢群體。在資本社會,富者的財富呈現出幾何式增長,而普通大眾只能獲得少部分利益,機會也被壟斷資本擠占。面對富人群體,原來中等收入群體有了“強者”和“弱者”的對比,產生了強烈被剝奪感,進而產生弱勢心態。
必須強調的是,僅僅把“強與弱的對比”作為劃分弱勢群體的標準,將使真實的弱勢群體的呼聲不能及時被聽到,威脅到他們的利益訴求,甚至剝奪這些人獲得幫助的機會。
(二)大面積的中產焦慮
在我國,社會焦慮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中國現階段社會焦慮的表現程度和波及范圍幾乎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吳忠民,2012)。比起頂層和底層群體,最突出的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貧富差距過大和資源分配的兩級分化,也“擠壓了中產階級的資本獲取路徑”(嚴翅君,2012),使得中產階級向上流動變得異常困難。為了向上攀升,中產階級工作努力,希望早日躋身上層社會。他們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在子女身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希望子女實現向上流動。而藍領階層的興起,使中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優勢也在減弱,他們又十分擔心跌落底層。為了縮小與上層社會的差距,并區別于底層社會,他們模仿上流社會,努力營造自己的生活品位和生活方式,通過各種消費來實現自我認同。但是,教育和消費都意味著大筆的經濟投入,大大增加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因此,向上流動的困境和向下流動的危機,促成了中產階級普遍焦慮的心態。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流動的減少、社會態度的普遍消極和大面積的負面情緒將會大大影響社會活力,加大改革難度,阻礙社會發展。而這更容易造成富人群體和底層民眾的矛盾日趨激化,引起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同時,必須防止社會情緒的繼續發酵成階級意識的對立,否則,將威脅到整個國家的統一與和諧。面對利益群體的多元化,必須改革和創新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創新力,逐漸縮小貧富差距,才能保證社會的平穩發展和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1]尉建文.“U”型還是“倒U型”?——貧富差距演變及成因的社會學分析.理論學刊.2005(6).
[2]周曉虹,等.中國體驗——全球化、社會轉型與中國人社會心態的嬗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3]福山著.李宛蓉譯.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4]馮仕致.我國當前信任危機與社會安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2).
[5]鄒紅、喻開志.勞動收入份額、城鄉收入差距與中國居民消費.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3).
[6]曾國安、胡晶晶.論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及其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經濟評論.2008(1).
[7]王克西、黨琳.房價收入偏離度、消費結構差異于貧富差距擴大化.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4(2).
[8]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9]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10]吳忠民.社會焦慮成因與緩解之策.河北學刊.2012(1).
[11]嚴翅君.快速量增與艱難質變:中國當代中產階層成長困境.江海學刊.201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