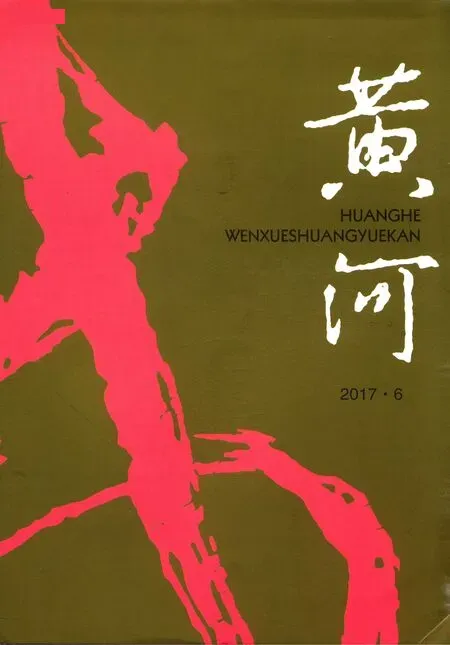燭影之歌
——為鮑貝詩集而作
續(xù)小強(qiáng)
燭影之歌——為鮑貝詩集而作
續(xù)小強(qiáng)
鮑貝已經(jīng)寫了很多的小說,足有幾百萬字了吧。散文呢,是她最早接觸的文學(xué)樣式,自然也是寫了很多,一時(shí)記人狀物,又一時(shí)行記漫談,結(jié)集的,竟也有好幾本了。如此的勤勞,有如一只不會(huì)冬眠的蜜蜂。
要說她以寫作為生,天天為寫而愁苦也不實(shí)。因?yàn)橛辛宋⑿牛憧梢娝粘I畹呢S盛,真像一個(gè)長不大的女孩子,她是天天在玩呢。這讓那些終日苦思冥想的職業(yè)作家情何以堪?文人總是相輕的。要說相輕也就是相競,百舸爭流,每天和和氣氣,文學(xué)的日子也就太平淡而平庸了。也許是長的小說,也許是不短不長的散文,她寫得有些疲乏了,又或許,她突然被文學(xué)的奇夢和野心驅(qū)使了,于是竟然又寫起了詩。一開始見她在微信里曬,以為她是在過家家呢。不期然,這個(gè)春天,她爆發(fā)似的作了一百首。我很好奇地討了來看,一首一首地讀下去,我的好奇真是一變而為驚異了。
我很早開始寫詩,卻也很早就停下了所謂向前而進(jìn)的步伐。現(xiàn)在只偶爾記下幾個(gè)字詞,甚或作上那么幾行。惶惶十年光陰,大約完全是惰乏而停頓了的。有時(shí)不免沮喪。可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老實(shí)說,自己確實(shí)沒了寫詩的心境,再準(zhǔn)確一些說,是丟了作詩的情緒。有時(shí)一點(diǎn)點(diǎn)的意念冒了出來,僅僅也就是零星的幽火,突然著了細(xì)雨,很快熄滅而不得呼喊了。被時(shí)間改造過后,冷硬得竟是連自己也不識(shí)了。
我總以為,詩歌先是抒情。這個(gè)情字,才是詩歌的核心。婉約也好,豪放也罷,抒情甚為要緊,若是無情,又何得抒,何得發(fā)呢?詩歌的好與壞,我固執(zhí)地以為首先便在這里。鮑貝的這部詩集,在我看來,首先也是勝在此處。整部詩集看下去,你可明顯地感受到她鼓脹如風(fēng)帆一般的情緒。這一百首詩,似經(jīng)過了多年的孕育,在這個(gè)春天突然爆發(fā)。她仿佛是一口氣完成的。我曾經(jīng)有這樣的本事,現(xiàn)在已是完全退化而成往事了。所以才特別地佩服。據(jù)我的經(jīng)驗(yàn),詩歌的寫作,是極耗神的一件事。哪怕作完一首短詩,也仿佛是跑了一次馬拉松似的。她如何堅(jiān)持得下來,她是如何投入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見,她一定是費(fèi)了許多的心力。
她似乎意識(shí)到了自己如此的狀態(tài),并用《春天的驚雷》這首詩做了描述:
我已感到心神不寧
周圍一片靜默
突然,地獄之光像鐵一樣炸裂開來
無情的閃電掠過所有角落和靈魂
驚雷從天而降
像身邊的一座大山轟然倒塌
像撕開地獄的冷酷面紗
我的心停止跳動(dòng)
意識(shí)停滯在紙上
一個(gè)模糊的墨水漬里
詩集題為“直到長出青苔”,這一個(gè)句子,仔細(xì)品讀,就暗含了一種倔強(qiáng)的不服輸?shù)膭蓬^。對(duì)不完美靈魂的嚴(yán)刑拷打,對(duì)愛與善的珍視和堅(jiān)守,都在這個(gè)句子中了。這部詩集絕大多數(shù)的分行,不是為了詩歌形式的刻意,而首先是情緒左沖右突的結(jié)果,是情緒的必然轉(zhuǎn)折,是情緒的幾何級(jí)數(shù)增長。她似乎要把自己的心掏空,所有的禁忌都被撕扯掉了。這些詩,有生命的快意在。詩本是極輕極輕的,以詩之輕透射靈魂之重,又以詩歌之重釋放靈魂之輕。這大約就是她詩情的的辯證法。
欲與力的噴發(fā),是她無畏的吶喊:
但我并未被這場浩劫擊倒
反而得以解脫
諷刺滲進(jìn)我的血液
羞辱成了我揚(yáng)起的旗幟
自嘲變?yōu)榇淀懙奶?hào)角
黎明即將來臨
我在黑暗中,感受一種偉大的榮耀
在不為人知的陰郁里,感到威嚴(yán)和顯赫
體驗(yàn)荒野僧侶和幽居隱士的崇高
對(duì)遠(yuǎn)離塵世的沙漠
重新?lián)碛辛诵碌恼J(rèn)識(shí)
在荒唐而高尚的時(shí)空里
我一遍遍地寫著救贖靈魂的字句
用遠(yuǎn)處并不存在的日落將自己鍍成金色
用放棄生命中的歡樂換來的雕像
裝飾自己
她端坐如圓,亦有沉靜在:
孤獨(dú)在塵土里堅(jiān)持了很久
幾座湖泊,在太陽升起時(shí)開始徘徊
清澈又柔和的金色,在朦朧中
擺脫了曾經(jīng)獲得的有形之物
穿透扭曲的高雅
她的懷疑壓制了好奇:
請告訴我——
一只蝴蝶如何占有花蕊的一席之地
在儀式到來之前
如何將華美的袍子拆散?
且聽她的自言自語:
躲進(jìn)黑夜里的我
像寒冷的春天,清澈而憂傷
我只是吃驚
連黑夜也不能把我照亮
我竟然忘了自己
忘了所有生活的目標(biāo)
忘了所有我要走的路
只是享受著虛無
那朵隱匿的悲傷之花
卻在意識(shí)的墻外綻放明朗而燦爛的事物
也無法將我安慰
在日復(fù)一日的倦怠中
我惟一的靈魂
是一縷拂過的輕風(fēng)
已經(jīng)抄得太多了。情之難為,大約就在它的不可捉摸。風(fēng)雨飄搖之下,欲言又止,可謂百轉(zhuǎn)千回。
我知道我失敗了
整個(gè)春天
我都在享受失敗所賜的朦朧和妖嬈
就像一個(gè)精疲力竭的人
享受著使她病倒的持續(xù)的高燒
你看,她用自己的詩,為一個(gè)讀者如我,已經(jīng)做了預(yù)言。
讀她的詩,不免自戀,總是想到自己。我作詩,不大喜歡宏大的內(nèi)容。也許,這源自我怯懦的天性。一句“吾心微小”,可見我個(gè)人的主張。“亮/我就退后/而不過去”,這更是我流露的本性。初中寫名字,我極煩“曉”字而喜“小”字,大學(xué)時(shí),編了一部薄薄的未刊的詩集,取的題目,是《自信的盲者》。后來,索性把“曉”徹底地改成了“小”,又把“盲”字砌進(jìn)了自己的齋號(hào)里,從此便想藏在“盲齋”之中而學(xué)古人了。
我以為,詩已是小技之一了。把許多的重負(fù)壓在詩歌的身上,我總以為是一件特別糊涂的事情。詩之于我們的有限性,恰如我們總是無法超出我們自己的影子。但詩歌的重要,似乎卻也正在于它的渺小,微弱,它的虛幻,它的精細(xì),它務(wù)虛的比例,它以全部的弱,給予我們最大的強(qiáng)。于是詩,便成了我們心靈碩果僅存的,一件掩耳盜鈴的華麗武裝。它飛蛾撲火,它火中取栗,它是情與愛天然的護(hù)身符。
鮑貝這部詩集的“上篇”,有三分之二的內(nèi)容,大約都可看做她一份極坦誠的自白。是自白,也是解剖。這些詩,有病歷的性質(zhì),有話劇的聚合,有告別的感傷,有幸福的影像,有痛恨的無奈,有感恩的珍重。
寂寞的字句倒映在電腦屏幕上
仿佛蝙蝠
在歸于洞穴的黑暗中猶豫
這些詩句一經(jīng)說出,便有了它們自己的生命,山河入夢,它們在世界的風(fēng)中奔跑,就是她,若是再重讀一遍,也難于斷定它們的來去。這些詩,一再沉思愛的艱難:
我們不能去愛。
到底是什么使我們墜入愛河?
我們傾盡所能地去愛,
卻不能占有身體和靈魂
也占有不了美。
以為愛上了一個(gè)有吸引力的身體,
但那仍然不是美,
只是一堆由細(xì)胞組成的肉體,
我們親吻和觸摸到的也不過是
正在腐爛的嘴唇,和潮濕的肉體。
甚至做愛
也無法抵達(dá)身體對(duì)身體的真正滲透。
這些詩,真的可以溫暖了一切愛的存在,如竹林的風(fēng)影,如從霧霾中奪回的燦爛的野花:
親愛的,只有你
才是我整個(gè)的春天。
愛如蒲公英的種子,微小,細(xì)弱,有誰還在意它呢?在這些詩中,“你”不是單獨(dú)的個(gè)體,她所質(zhì)詢的,是我們每一個(gè)人:
你愛得像刺猬
小心翼翼
猶如夜間的竊賊
終日痛苦、冷漠、一言不發(fā)
酒醉時(shí)你才喋喋不休
這些詩,像虛無的,一滴精靈的晨露對(duì)太陽黑子的警告。
詩歌之愛,是詞語之愛,亦是倫理之愛。或者說,詞語之愛,是抽象之愛,而倫理之愛,是具體、現(xiàn)實(shí)之愛。詞語之愛易,倫理之愛難。如此難易,亦是詩歌寫作的難易。“上篇”自白詩所無法包容的,便在那些解剖的詩里了。《野梅》《獨(dú)白》《野月亮》《梅花開了》《星期天》《月光下》《你忽然出現(xiàn)》《嫉妒》《夢境》,“一小團(tuán)的黑,折磨著一大片的空白。”這些詩走出了自我的虛空,在一種對(duì)話的關(guān)系中重新確證了自我,如燭與影,如,“你是我的人質(zhì)”。
倫理之愛表明,詩歌和現(xiàn)實(shí)和時(shí)代關(guān)系的密切。因了多種多樣的誤會(huì),說起“時(shí)代”,就仿佛在說一件和我們無關(guān)的毛褲或者是話筒。從個(gè)人細(xì)微的情緒和詞語中,我們依然可見一個(gè)時(shí)代的影子。一些偉大的寫作者們已經(jīng)代表了時(shí)代,但不妨礙有更多的以詞為墳的人,從某一個(gè)側(cè)面和角度,留下自己的記錄。無意與有意,即便是一首短詩,我們都會(huì)砌入自我對(duì)時(shí)代的觀感。個(gè)人的哀苦,也未必就全是個(gè)人的因由。從物的角度去看,時(shí)代的硬與冷,時(shí)代的熱與狂,必然會(huì)沾染到你細(xì)嫩的靈魂里。而作為詩人,作為一首詩,其必然會(huì)極為敏感地捕捉到的。我想,這也是詩歌現(xiàn)實(shí)主義之一種吧。
由鮑貝的詩,也可看到我們當(dāng)下時(shí)代的掌紋和面相。也許她是無意的,忘了功利,她才會(huì)寫得如此的輕松自然。我想讀過《昔日時(shí)光》《厭倦》的人,從中都可看到自己在現(xiàn)時(shí)代的倒影。《你好自殺了》是我極喜歡的一首頗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的詩:
“你好自殺了——”
每天早上醒來
總會(huì)飄過來這一句
當(dāng)一束冷淡的晨光,像痛苦的天啟
照亮你的床鋪
又一個(gè)安靜的夜晚從此消逝
盲目的生活,虛假的目標(biāo)
不可避免的活動(dòng)……
又將在白天紛至沓來
天光將百葉窗縫隙里的灰色疑問填滿,
你摁下開關(guān),窗葉瞬間收起,
仿佛所有的疑慮都被沒收
世界無限光明
你大口吞咽著一只面包,走向辦公室
凝重的神色像是被傳去法庭
在溫和的殘廢的空間里
另一個(gè)隱匿的自己
每天都在被判刑
當(dāng)暮色降臨,
你仍蜷縮在辦公室的角落里
徒然的悲傷如一輛無輪的馬車
骨頭一陣?yán)漕潱路鹪诤ε?/p>
你為一切而哭——
你曾緊握過的死去的手
你曾親吻過卻又離去的唇
你曾深愛卻未來得及安撫的靈魂
連最后的黑暗,
也拋棄了你
像一個(gè)從未被勸服的人
再次發(fā)起新一輪的抗議
夜晚的突然喧囂狂扯著你
你縱身一躍,
猛然將身體對(duì)折,掛在辦公室高樓的窗口上
想像著一個(gè)終于成功自殺的人
這些句子,如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對(duì)準(zhǔn)了你我焦慮的白發(fā)三千尺。
如果說,詩集的“上篇”,是個(gè)人主義的真;那么,似乎可以說,詩集的“下篇”,則是面對(duì)世界的善和美。“上篇”幾乎無一例外的,是獨(dú)居斗室的言語拼殺,緊張,急迫,節(jié)奏是逃離地球一般的加速度。而“下篇”,舒緩了許多,從容了許多,可見她多年行走世界的見聞。這些詩,確實(shí)有散文化的缺欠。敘述經(jīng)歷,描摹場景,記一個(gè)人,憶一些事,在詩和散文之間的游弋。亦可見她并不是一個(gè)只會(huì)暗自垂憐的個(gè)人主義者,她有大的胸懷,她的悲憫由善而至美。
“下篇”總題為“在路上”,這個(gè)詞已經(jīng)老套了很多年。許多人以為自己已經(jīng)“在路上”了。比如我,其實(shí)呢,只是說說而已,我們還沒有出發(fā),還在原地踟躕,像個(gè)螞蚱蹦跶了兩下,就以為自己走遍了世界,經(jīng)歷了風(fēng)雨。徒有一種精神,徒有一個(gè)神秘的暗示,仿佛一切都可以解決了——我們就是這么一步步把自己改造為鴕鳥的。我們?nèi)绱酥ΓΦ綉械脛?dòng),懶得放棄。鮑貝的“在路上”,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在”,是行動(dòng)起來的“在”。她是御風(fēng)之人,只一個(gè)凄美的背影,讓我們一再的恍惚。并有可能,拷問一下自己,是否應(yīng)該重新開始。
說了許多了,意猶未盡。
直到如今,我仍不知詩歌的形式為何。我越來越覺得,自己過去對(duì)形式的迷戀是錯(cuò)的。也許我變得更富有了,也許,我變得更貧乏了。總之,我此刻認(rèn)為,詩歌的形式問題就是一個(gè)偽問題。再寬容一點(diǎn)講,詩歌的形式問題,也是一個(gè)極次要極次要的問題。
這么說,不是為鮑貝的這部集子做辯護(hù)。恰恰相反,也許正因?yàn)樗龥]有形式的概念,她才獲得了分行的真正的自由。心地光明,自有詩情,自有詩行。
心地光明之心,即是“赤子之心”,這四個(gè)字,許多人都講過,作為一個(gè)曾經(jīng)寫詩的人,“直到長出青苔”,我似乎才領(lǐng)悟到。也正是因了這四個(gè)字的教誨,我才一直逼迫著自己非要作這么一篇文章,姑且以此,為序的同時(shí),亦作為我個(gè)人詩話的一個(gè)燭照。
責(zé)任編輯 郭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