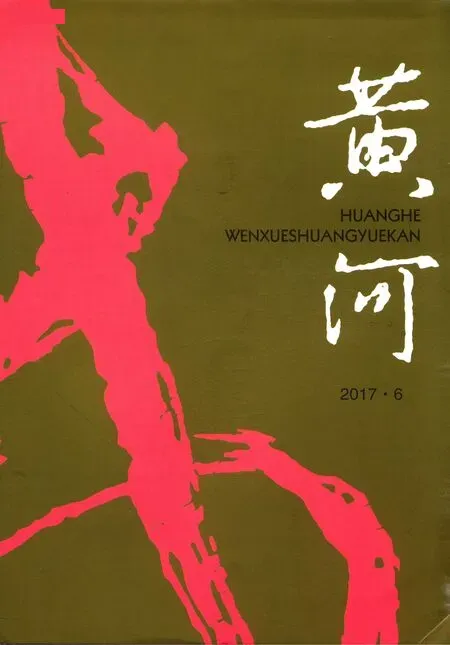也說魯迅雜文
楊柳岸
也說魯迅雜文
楊柳岸
在更多時候,我寧愿遵守沉默是金的教誨。晨起翻讀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讀到有關論述魯迅的幾句話語時,讓我有所思考,也有了說幾句話的念頭。比如在對夏志清說魯迅“在他轉向以后,雜文的寫作更成了他專心一意的工作,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他十五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讀這幾句話時,我覺得有必要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也主要是因為我對夏志清的學識一貫比較尊崇,所以偶有不同看法時也不愿藏拙,希望表達出來與他作跨時空交流。
對歷史上確定文本的評價也更多地屬于見仁見智的范疇,即便如治小說史大家夏志清者,于半個世紀前說那兩句話,除了有獨立見解之外,我認為也暴露出他的一些偏頗。當然,要理解偉人如魯迅者何其難也,有人說,理解了魯迅,就理解了中國,這話也不無道理。論魯迅,必談魯迅的雜文,因為魯迅最后十年的主要成績在于斯,是繞不過去的,所以夏志清這本小說史中也牽涉論及魯迅雜文,也可理解。除去他這話里的道德價值評判的因素外,要承認他所說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關鍵就看每個人是如何去理解那些所謂的“事實”。每個作家,即使是優秀作家偉大作家,都會有創作力衰竭的時候,創作力衰竭,是自然現象客觀規律,不應該作為指責或詬病一個作家的原因。“搬弄是非”這個詞聽起來刺耳,卻也是雜文的主要功能之一。那些回避矛盾混淆是非,做好好先生和事佬,這樣的事誰都會,用不著麻煩魯迅去做。至于說魯迅的雜文“啰啰嗦嗦”,就更要看每個人怎么理解。身處中國文化傳統中,要條分縷析闡明一件事理,談何容易!一般人往往會陷入百口莫辯的無奈境地,而魯迅卻以一支筆游刃有余,筆鋒所向被批者無以遁形,從效果看,魯迅的文章不但不是“啰啰嗦嗦”,反而可以說是非常精煉,惜墨如金,也留下太多的藝術空白和豐富思想空間。魯迅的雜文幾乎就是我們身處的文化和我們生存境遇的最真實寫照和象征。有如此文字留存于世,非天才而不能為。對這樣的文字略其無窮豐富的精神內涵,只從最淺顯的文字技術層面而概之以“搬弄是非啰啰嗦嗦”,如此論斷何其武斷!難道要用禪家的不立文字來要求魯迅嗎?
當然,夏志清所論盡管有些偏頗,但也算有自己獨立見解,至少也是一家之言,也是屬于五十年前那個時代氛圍下的產物,自有其難能可貴處,可以理解。其褒魯迅小說而貶其雜文,這其中也有小說史家自重其所操之術的因素在內,也不應過分苛責。但這些畢竟不是公正史家應該有的眼光。以現代眼光來看,寫作自由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自由。他有寫作的自由,也有自由選擇寫作內容的自由。作家在每一個年齡段,都有其文學觀世界觀。對文學一詞,應有寬泛的理解,一個作家有權力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雜文正是魯迅晚年最好的文學樣式,是忽略任何外在形式而直抒胸臆的文學。夏志清對魯迅雜文的否定,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他在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里也明顯表達出來了,那就是,他重文本,不贊成一個作家過多地參與社會事務,他以為作家參與社會事務是浪費生命,做外行的事。他的這個觀點后來被許多學者所用,用來指責魯迅。也有一些學者善意地替魯迅惋惜,惋惜他沒有把寶貴的生命用于做所謂的“純文學”,他們所謂的純文學,更多的是指小說,尤指長篇小說,雜文在他們眼里或許只能是“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的勞什子。我認為,這些都是狹隘的文學觀,是文學情懷不寬廣的表現。
雜文必定牽涉更廣泛的社會性事務。一般而言,有這樣一種現象,偉大作家似乎都會,也必須成為社會活動家。社會活動家幾乎是所有大作家的共同身份或頭銜。比如與魯迅幾乎同時代的托爾斯泰、泰戈爾、羅曼·羅蘭、羅素、蕭伯納等。魯迅和其中一些人還見過面,有過交往。相比較,魯迅沒有到過更多的國家,只是早年到過日本,如稱魯迅為社會活動家,有些勉強。作為一個偉大作家,他的各種言行,各種沒有形諸文字文本的行為,包括那些被人詬病的論爭和社會事務,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他無形的作品,是我們的文化財富。我們國家幾千年來講究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以魯迅的名望并懂多國語言與許多國際大師級人物有過交往,他如果想獨善其身,我想也不是難事。他若“灑脫”一些,也可以做個國際社會活動家,如林語堂“腳踏中西文化”。文化,其實也就是人格的沉淀。特別是偉人,他的影響力輻射力所及,人們會受益深遠。像魯迅這樣的人,他如果真能更充分地做個社會活動家,我們的社會環境也允許他,給他充分的條件,讓他最后十年做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活動家,那必將是我們國家之幸,民族之福。以此少一些文章文字,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他的那些言行,那些所作所為,都必將是我們的大文章,不立文字的無形大文章。
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事實上,魯迅沒有那么幸運,各種主客觀條件沒有允許他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每一個人都有自身的局限和命運,即使魯迅那一點或主動或被動而有的所謂 “社會活動”,也成為人們詬病他的一個理由。他如果早一點也玩一玩幽默和閑適,多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人們也許會把他當作梁實秋林語堂那樣的大師。從另一個角度也可看出,在當時的中國,成為社會活動家是多么難,而更多的是政客、投機分子。當時我們國家的文化土壤環境之惡劣,不足以把魯迅培養成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活動家,致使這位異端天才于中年便離世而去,徒留后人爭論短長。他那些論爭,那些“搬弄是非”,不是事務主義,不是庸俗現實主義者,做人做事一絲不茍、表里如一是他認真執著的人生態度與行為氣質決定的。他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那些所謂瑣事,聰明者是不屑于做的。那些事看似瑣小,但如果關乎大的道義,他必認真對待,不辭煩勞,洞燭幽微,小中見大,不避俗。就如同一個事必躬親,嘔心瀝血,哀民生之多艱的一家之長,是沒有閑情逸致去頻頻出鏡于各種光鮮的名利前臺,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幾乎沒有離開上海。國難累忠臣。一個偉人的民族擔當精神與勇氣,如他所說“雖千萬人吾往矣”,也多少有一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舍我其誰”的犧牲精神,他只能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這腹,這個貶義詞我們若用之于一些偉人,幾乎是人的普遍心態。對此我們應當以為愧,以保持我們的心靈與偉人的心靈連接的那僅剩的一點通道。
細讀魯迅雜文,便知其思想穿透力依然對當代社會生活與思想領域有諸多啟發,其文章的意義已經超越時代局限而具有了文學永恒性。魯迅的雜文有魏晉風骨,有晚明性情,有佛的悲憫情懷,有尼采托翁的人道主義,更有現代社會理念,其文字透出無窮的人格魅力和豐富的人性信息。即便只從文字技術層面上考量,魯迅寫小能見大,寫實能見虛見永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理解了魯迅的雜文,就更深地理解了魯迅,更深地理解了中國,也更深地理解了魯迅因何而偉大。
燕霄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