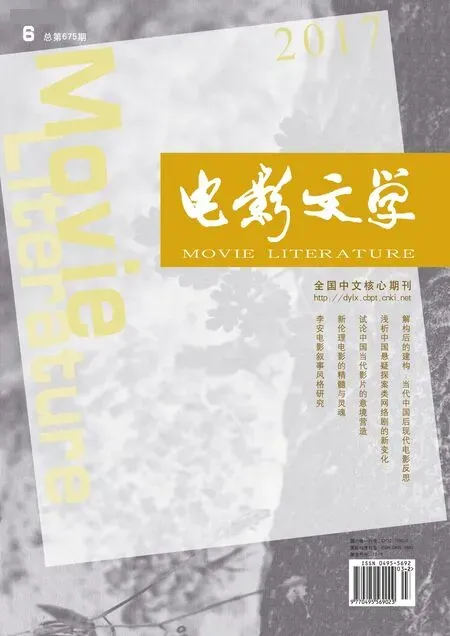解構后的建構:當代中國后現代電影反思
李 磊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9;山東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后現代電影理論從20世紀90年代起被理論界熱議,在這種理論支撐下,王家衛、周星馳帶有碎片化、戲仿、反諷等特色的作品被歸為后現代電影,甚至連文化反思作品、先鋒藝術作品都沾染上后現代主義色彩。今天,我們在經濟全球化與“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再來看待這一理論時,不得不思考這些后現代電影與中國當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現狀之間的關聯,以及后現代電影在當代所生發出來的新的美學體驗。“當代”時間維度在藝術創作中為表意主體劃分出了一個時段,這個時段的屬性與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具有內在認定與互指,當下社會的嬗變融會在人們的文化心理與價值觀念中。克羅齊指出:“‘當代史’只應指緊隨已完成的行動產生、作為對此行動的意識的歷史……它同任何精神活動一樣,是在時間之外(不分先后)、是與其相聯系的行動‘同時’形成的,憑借非編年史的而是觀念的差異,同行動相區分。相反,‘非當代史’‘過去史’是面對已形成的歷史。”①以此來看,“當代”的現代性意義就在于其不斷的生成性與未完成性,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內的語義表述。當下傳統與現代砥礪共生,人們在變與不變之中會重新評判剛剛結束的行為,讓最新的觀念不斷迸發正是中國電影在“當代”時間維度上的美學意義。
一、后現代的理論建構
從文化現象回到學術建構來看,后現代理論相當龐雜,國人最早接觸后現代主義這一概念是在1985年杰姆遜②的北大演講上。與利奧塔的語言學分析不同,以杰姆遜為代表的美國后現代理論,是從文化上談起的,特別是文藝作品的分析,以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對近代、現代、后現代進行了歷史分期,并總結出后現代文藝的一系列特征:平面化和零碎化、拼貼與戲仿……
麥茨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與“新浪潮”和“左岸派”同時出現的伯格曼、安東尼奧尼等人的作品稱為現代主義電影,而這同時也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發端的年代。但直至80年代,后現代主義電影才真正出現,1982年的《迷墻》被公認為是后現代主義的開山之作,而后現代主義電影的全面開花是在電影百年的1995年前后。《阿甘正傳》《低俗小說》《重慶森林》《暴雨將至》這些作品的風格差異很大,表現手法則帶給世人以新奇與驚詫。同一時期,中國出現第一部后現代電影《三毛從軍記》(1992年),雖然這部電影的影像風格和敘事時空并沒真正地脫離傳統電影敘事的連續性,但因其戲仿與反諷而載入了史冊。這正應和了杰姆遜對后現代電影所提出的“把舊的事物重新調配和組合,創出極具新鮮感的混合體”,“在這種嶄新的美感構成之下,美感風格的歷史也就輕易取代了‘真正’歷史的地位了。”③
中國后現代影視文本有三類,一類以王家衛執導的系列作品《重慶森林》《東邪西毒》為代表,第二類以周星馳出演的《大話西游》系列為代表。在王家衛的作品中,漂浮感、不確定是首先訴諸我們感官經驗的影像風格,作品的主題表達一種城市人生活的焦慮與震驚。在周星馳的作品中則體現出一種拼貼與戲仿,周星馳以“無厘頭”風格的表演構建出荒誕的重組故事。第三類以第六代、新生代導演的系列作品《讓子彈飛》《瘋狂的石頭》《刀見笑》等為代表,以先鋒的特質將票房帶入一種狂歡的時代,把這些風格鮮明的影視作品重新按照杰姆遜的理論進行關照與批評,會發現一種現代性體驗與后現代表征在文學藝術上的張力耦合。
二、現代性體驗與后現代表征的張力耦合
后現代電影從一種文化思潮到一種敘事手法,無形之中夸大了它的適用范圍。今天,大量的戲說劇、穿越劇因歷史感的消失被冠以后現代的封號,而有些文章將強調反思與批判的早期第五代電影也標以后現代,或許我們仍然應該回到杰姆遜的告誡中來進行電影文化的批評。杰姆遜北大演講的翻譯唐小兵也多次提到,“中國有沒有后現代主義”是很多人不斷提出的問題,“任何文本的解讀,不僅要探求文本內容所表現的形式,即了解意義形成的條件,研究內容本身在一定敘述環境里繼承的連續性和帶來促發的斷裂、非連續性;同時也要追尋文本形式中的內容,即提示隱含在形式之中的歷史過程、政治寓言及文化生產方式。”④我們嘗試以杰姆遜的方式進入后現代,后現代主義要旨在于放棄現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規范內容。現代主義的零散化是要讀者將碎片組合,后現代主義的零散化只是要讀者體會不同性和差異。現代派在緬懷過去時是痛苦的,而后現代面對過去時是隨意的。對于中國這個未完成現代主義的國家,無法放棄對于現代性的體驗,諸如無意識、存在主義、直覺主義所帶來的晦澀的學院派的理論尚未深層建構,就要打破它去重組拼貼,這不僅是在實踐中無法完成工藝操作,在思緒邏輯上也無法跨越理性主義鴻溝。特別是在影視藝術成為今天的大眾文化中的重要作品,在通過視聽拼貼出的文化板塊結構中,一個難以企及的空洞怎么能夠完成它在文化縫合中的任務?以此來觀照王家衛以往的電影,也仍是在完成現代主義的深層表現中都市的孤獨與焦慮。倒是被詬病為失去了太多王家衛色彩的《一代宗師》,反而因歷史影像、小品演員多了幾分后現代的拼貼。盡管《一代宗師》在對白中依然充滿了哲學意味的心靈雞湯和知音體,但其主題內核已經在講述一個家國情懷的故事,雖然宮二孤獨一生,卻擁有了柏拉圖式的愛情。
此外,后現代主義的影視文化內容也有著與前文斷裂式的標志,以視聽沖擊代替故事情節是后現代電影的標志之一。比起伯格曼、費里尼的現代主義電影,后現代電影中多數是大信息量的,或是通過剪輯、動畫、視聽分割來完成,像《羅拉快跑》中的多層敘事,《枕邊書》中的畫面疊加;或是通過人物表演、快速對白來強化碎片感,比如《低俗小說》中的怪誕表演、《阿甘正傳》中的歷史解構。正如杰姆遜指出的“仿像”在當代的重要性,“晚期資本主義世界是個超越文字的世界,人的生活到了這個階段已經邁閱讀和書寫以后的全新境界了”⑤。
當中國人的現代性體驗還在經歷現代化建設時,我們同時處在了后現代影像表征的解構時期,于是戲仿被當作后現代的典型呈現,這也使得《大話西游》系列因其戲謔與魔幻而被尊為后現代的又一經典,這的確是周星馳諸多無厘頭電影中最純粹的后現代風格電影,它用時空輪回、多重角色徹底解構了宏大敘事,暗合了利奧塔“無”就是本體的后現代詮釋。但是《大話西游》當年票房慘淡,它的火爆緣由幾年后的網絡傳播。因此,《大話西游》的后現代,給我們無法留下完整的故事,留下的是一句句經典對白。
后現代體驗是與中國的都市化進程同步的,而當下中國更多地處在一種傳統、現代、后現代并置中,必須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現代性仍然是中國當代的主流,在當代中國文化啟蒙與追求小康的整體狀態下,后現代只能成為一種奢求。
三、被解構的后現代
無論中國的后現代影像是從20世紀80年代的王朔開始,還是從90年代的《三毛從軍記》開始,經過了馮小則的“賀歲”、王家衛的“都市”、周星馳的“無厘頭”,如今的后現代影像必須從最初的一味解構走向重構當代的精神世界,因為我們看到了延續至今的后現代影像的式微。
(一)反諷的無力
反諷作為后現代的重要表現特征曾被姜文用到了最佳狀態,姜文用《陽光燦爛的日子》解構了傳統的“文革”敘事,用《鬼子來了》解構了抗戰敘事,用《讓子彈飛》解構了強權敘事。這些荒謬的世界里卻建構著一種藝術文本的自由獨立與反思,這其中充滿了反諷的力量。但《一步之遙》退回到一味的戲仿與拼貼,這對于今天經歷了種種后現代主義理論過目后卻依然處于后現代國家的當代中國觀眾來說,只能一笑而過。正如尼爾·波斯曼所說的:“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⑥
(二)“無厘頭”的衰落
20世紀90年代,周氏“無厘頭”橫空出世,令人眼前一亮。如今這種戲謔的影像風格已經成為基本敘事套路,連高校影視專業的學生也能隨手模仿上幾筆。作為“周星馳接班人”的盧雨喬更是在網絡微電影領域充分借鑒利用這些手法,《惡棍天使》《分手大師》甚至使“無厘頭”成為爛片標志。所以《西游·降魔篇》之后,周星馳的后現代就不能再實現對時代的超越,《美人魚》單薄的故事及情節設計,在重復90年代橋段的同時預示著“無厘頭”的沒落,直至《西游·伏妖篇》,我們還上了那張影票,卻找不到那時的快感。當“星爺”招牌的號召力只剩下情懷與敘舊時,或許在宏大意義上有所建構是周星馳不同于其追隨者的新的后現代審美趣味。于是,《美人魚》開始講述環保、世界等大義主題,似乎是對之前周星馳的一種背離,這也正是當代中國對后現代的態度從斷裂論到連續論的一種糾偏。《大話西游》的后現代,無法給我們留下完整的故事,卻留下了一句句經典對白。《美人魚》恰恰相反,用一個俗套完整的故事與當下的主流話題相契合。至于從環保主題中解讀出占領主題,是闡釋過度還是政治附會,成為后周星馳時代的隱喻。
(三)碎片的散失
后現代式的游戲寫作首先表現在藝術樣式的拼盤式組合。對于時間的多重體驗讓后現代影像一直呈現出碎片化的味道,從王家衛架空年代的時空游離到寧浩的多線敘事的時間洗牌,碎片為后現代注入了解構宏大事件的全新視角,不是一個人凝視下的世界,而是多人觀看的世界。在時間的游戲中,畢贛用《路邊野餐》提供了一個西方式的后現代,一個充滿魔幻現實主義的永無盡頭的黑洞。而賈樟柯《山河故人》同樣是在時間重整過程中,卻將碎片一一撿拾串接。《山河故人》中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三個世界,是當下中國正經歷的現代性體驗。
四、結 語
后現代主義電影的另一貢獻,就是將先前的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陳規和隔膜打破消解。藝術電影是艱澀的,需要靜心解讀。而大量后現代電影在保留了藝術電影的先鋒精神的同時將其速度化了,信息量、多元價值快速堆積到觀眾面前,電影也在消費社會里被物化了。所以說,同樣是一個仿象的世界里,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區別在美感的消費主義。中國的后現代主義電影如果想在商業領域成為具備經濟價值的產品,首先既要與現代主義藝術晦澀的自主價值斷裂,有選擇地展示知性的反理性主義、道德的犬儒主義和感性的快樂主義。同時,也必須看到新的電影創作形式要全面放開,是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批判,還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超越,而不是去追求一個后現代的軀殼。
詹姆遜說過:“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⑦所以,在保有后現代主義創作的同時要開展后現代主義批判,因為中國的現代性尚未完成,在反思與整合的社會化的進程中,理性的知識體系并沒有全面構建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意識形態建設的合理性。通過電影來完成中國人對于包括二元對立、法制規范、民主意識、政治啟蒙在內的一系列現代化工作,而不能一味地戲仿與虛無。
注釋:
① [美]B·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田時綱譯,《世界哲學》,2002年第6期。
② 國內譯著將美國文化學者Fredric Jameson分別翻譯為杰姆遜、詹姆遜、詹明信等。
③⑤ [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74-376頁,第371頁。
④ [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頁。
⑥ [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童年的消逝》,章艷、吳燕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頁。
⑦ [美]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當代電影》,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