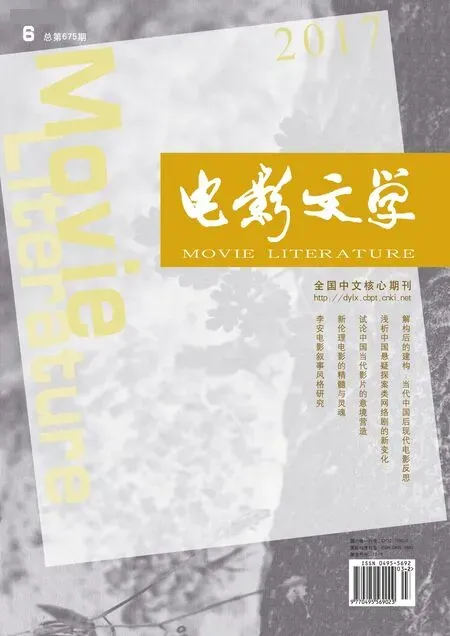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走西口”對內蒙古影視多樣性的影響
尹悅婷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一、內蒙古影視劇題材的多樣性
內蒙古影視肇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內蒙古影視作品由單一的對蒙古族歷史文化、社會生活題材的表達演變為多元的具有各地地域氣質題材的展現,作品的質與量也呈螺旋式上升。當然,現今的內蒙古影視作品題材雖然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但蒙古族題材仍占據主體地位。事實上,蒙古族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中國少數民族影視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它由發展之初對社會的寫實性表達逐漸衍生出各種不同的類型,如史詩、文藝、商業、動作等,在對中國影視劇傳統繼承的基礎上,形象地闡釋、展現和謳歌了內蒙古的蒙古族人民的民族精神與風貌。[1]不少優質作品在國內國際影壇上屢獲殊榮,為內蒙古影視增光添彩。
除了作為主體的蒙古族題材影視作品被公眾逐漸認可之外,內蒙古影視劇中具有其他地域性特征的作品也開始走上歷史的舞臺。眾所周知,內蒙古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地區,由于東西跨度較大,并與國內外多個地區毗鄰,這些毗連區在多年的交流融合過程中會形成許多獨特的地域文化,比如內蒙古東部區的赤峰、通遼、呼倫貝爾等地就具有明顯的中國東北地區文化特征,他們的生活習俗、方言以及信仰都與中國東北地區相似,這樣的地域特點反映到影視作品上就形成了與純反映蒙古族事跡的影視劇不同的內蒙古影視作品類型。
本文要重點剖析的“走西口”文化,也對內蒙古影視作品影響深遠。因為“走西口”的移民多數來自于晉陜地區,所以“走西口”文化帶有許多獨特的晉陜氣息,取材于“走西口”地區的內蒙古影視作品往往聚焦于農村改革問題,對內蒙古西部鄉村進行深刻的關注和寓意性的解讀。下面我們就著重解讀一下“走西口”文化對內蒙古影視題材多樣性的影響。
二、“走西口”文化的概況
(一)“走西口”文化的形成
“走西口”是我國近代的三大移民運動之一,主要是指以晉、陜為主流的內地農民因為惡劣的生存環境無法在故鄉繼續生活,而被迫移民到“口內”(指內蒙古自治區)求生,他們在口內或經商或務農,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晉陜蒙毗連帶,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會與自然環境,使蒙漢民族在長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戲曲、相近生活方式以及相同信仰習慣的文化圈。[2]
(二)“走西口”文化圈的特征
1.獨特的此地話——“西口”方言。方言作為語言的變體,根據其性質可以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內蒙古中西部以走西口后裔為主,所以使用“此地話”(特指內蒙古晉語)較多。據《綏遠通志稿》記載,綏遠地區漢人最初大都來源為山西,“由以晉北各州縣為繁,惟綏西五原、臨河、安北各縣局,則頗多陜西、河北兩省籍者,其他各縣,幾全為晉民”[2]。內蒙古“走西口”地區的方言是以山西、陜西漢語方言為基礎,融合、吸收其他地區漢語方言及蒙語、滿語等少數民族語言借詞而形成的獨具地區特色的漢語小方言。[3]在影視劇中使用“此地話”不僅可以描寫鄉村所具有的地域特性、農村生活的趣味性,還可以把劇中人物自身的感受,或是悲傷,或是歡喜,貼切、生動地通過方言表現出來。
2.相同的戲曲——“二人臺”。在內蒙古中西部“走西口”移民區域內,“二人臺”這種起源于晉陜黃土高原的戲劇形式較蒙古民族熱愛的長調與呼麥等藝術方式更受人歡迎。“二人臺”屬于大眾藝術范疇,劇目大多短小精悍,內容簡單明了,它在隨意和靈活的表演方式中形成了非常動人的民間特色。[4]在許多已經拍攝完成的“走西口”題材的內蒙古影視作品中,“二人臺”是以一種影像符號出現的,它的存在加深了作品的內蒙古“西部”風情,使得作品從相同題材與風格的內蒙古影視劇中脫穎而出。
3.相似的社會習俗與信仰習慣。總體來看,因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多為晉陜移民,所以許多生活習俗與晉陜人民是相似的。習俗方面,不少地區還保留著由西北傳入的“騾馱轎”婚嫁風俗,在葬禮上會雇用“鼓將”為逝者送行。呼和浩特與包頭的大部分地區保留了為12歲兒童“圓鎖”的習俗等。在信仰方面,由于走西口移民進入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后人生地不熟,精神上急需要尋求某種慰藉與庇護,所以西口地區建起了許多神廟,祭拜的偶像各不相同,佛家、道家、儒家的各路神仙都是人們心靈的寄托,這也就形成西口地區人民共有的信仰方式。黃土高原、窯洞、神廟等這些獨特的地理文化景觀經過導演巧妙的安排,可以表現出“西口”鄉村深厚的文化內涵。
三、“走西口”文化在內蒙古影視作品中的運用
最早反映“走西口”文化的內蒙古影視作品是內蒙古電影制片廠于1961年拍攝的二人臺舞臺紀錄片《走西口》。《走西口》是二人臺戲曲藝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個曲目,主要講述了清朝末年山西遭遇天災,因為饑寒交迫,太原佃農太春在新婚不久就遠走口外尋找生路。臨行時, 其妻玉蓮戀戀不舍、依依惜別的場景,反映了走西口移民與親人分離時的無限悲痛與不舍。《走西口》作為民歌或是作為戲曲,都繼承了古老音樂表現人類生存這一主題,以它極具自由灑脫的旋律和悠揚悲愴的歌聲,傾訴了人的生之痛苦和愛之艱難,這也使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戲曲藝術本身,成為記錄一個時代民族生存狀態的真實而震撼的史詩。[5]內蒙古電影制片廠用舞臺紀錄片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不僅為剛起步不久的內蒙古電影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還通過電影膠片的記錄手段使得當年珍貴的戲曲表演得以完整保存。從一定意義上看,這部影片起到了影視人類學影像資料的重大作用,為后人對二人臺戲曲流變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電視劇開始走上正軌,產銷量逐年遞增。內蒙古自治區也緊隨時代發展的步伐,除了積極發展電影產業來提升本地區的知名度,還大力發展電視劇市場,使得電視劇市場一時間百花齊放。內蒙古電影制片廠導演張元龍分別在1996年與2000年拍攝了兩部以“西口”地區農村改革為背景的連續劇,它們就是《黨員二愣媽》和《黨員金柱有點忙》,這兩部電視劇也都不負眾望地獲得了不俗的成績。《黨員二愣媽》獲得了第16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中篇連續劇、優秀編劇(劉彥武)、優秀錄音(朱文忠)。《黨員金柱有點忙》獲得了第19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中篇連續劇、第五屆神農獎金獎和2002年“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導演張元龍出生于內蒙古中部托克托縣的一個農村家庭,由于對農民感情上的親切,對農村生活的熟悉與熱愛,以及對西部農村改革發展的敏銳觀察力,他的大多數作品都以農村改革為主體,用自己對鏡頭獨到的把控能力,將農改過程中所發生的具有戲劇性的事件真實地表現出來,使得農改過程中不為人知的艱辛受到許多人的關注。1996年拍攝于內蒙古清水河縣的《黨員二愣媽》以樸素的寫實風格、平淡的演員表演以及原汁原味的方言對白,講述了一個為人民辦實事的基層女黨員的故事。導演通過走訪,深入了解當地的基層黨組織,發現那里的黨員干部雖然懷有滿腔為人民服務的熱情,但普遍文化程度低下,法律觀念淡薄,工作方法簡單。所以由斯琴高娃飾演的二愣媽擺脫了以往黨員干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成為一個一心想為大家辦實事,但有時方法卻也欠妥當的基層女黨員形象。為了改善村里小學的環境,她帶領村民私自砍伐了樹林,看到了貪污腐敗的林業局局長,她撲上去就是一頓廝打。這樣的形象雖給人潑辣的感覺,但是這種潑辣與倔強中卻也透露出二愣媽敢愛敢恨的鮮明個性,使得這個角色有血有肉、立體豐滿。2000年,由張元龍導演、著名表演藝術家黃宏主演的《黨員金柱有點忙》也在內蒙古清水河縣順利殺青,并于同年在中央電視臺進行播放。這部電視劇是張元龍“黨員”系列的又一佳作,雖然這部電視劇同樣講述了基層黨員為民服務的先進事跡,但是相較于《黨員二愣媽》,這部劇的“走西口”文化元素滲透更為深入。劇中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一排排錯落有致的石窯洞,原汁原味的此地話,獨特的“西口”地區民俗,無不透露出一種親切的感覺。劇中黃宏飾演的鄉黨委書記金柱為了能還上欠村民們的石料款,讓鄉長建東代表鄉政府去給縣上趙經理的孩子紅袖慶祝12歲生日,生日宴會上趙經理請了二人臺班子表演助興,為了顯示自己的誠意,建東還親自為趙經理搓糕面,炸油糕,院里一片紅火熱鬧。紅袖的長輩給她套上象征吉祥的面圈,口里還唱念著:“九石榴,一只手,守住親娘再不走。”這些“走西口”民俗元素的加入,使得這部以西部農村為背景的電視劇更接地氣,也讓觀眾得到了更多的共鳴,與劇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同時紅袖“圓鎖”這樣熱鬧紅火的氣氛與鄉政府外聚集的要不到錢的農民們形成鮮明的對比,突出了金柱作為鄉黨委書記在農改過程中的艱辛無奈與不怕困難的精神。
眾所周知,內蒙古中西部地區除了“走西口”移民之外,還分布著許多原駐的蒙古族人民。百年來,在兩個不同民族進行融合的過程中,碰撞出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火花,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相互交融,不止改變了雙方的生活習慣,更衍生出了許多有情有義的故事,2014年由內蒙古電影集團與準格爾旗委宣傳部聯合攝制的《漫瀚調》就是這樣一部深情之作。《漫瀚調》主要講述了在清朝末年,年輕人李河清“走西口”尋找父親,并在尋親的過程中與蒙古族女孩娜仁花發生了一段真摯而感人的愛情故事。這部電影也通過故事表現出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漫瀚調的藝術生成,展現了漫瀚調的藝術魅力。同時這部影片還以清朝光緒年間在鄂爾多斯大面積開墾土地為歷史背景,通過朝廷無節制的開墾與蒙漢人民共同反抗的尖銳矛盾沖突,展現了蒙古族近代歷史上聲勢浩大的“獨貴龍”運動,也借此展現出蒙漢民族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電影也用音畫交融的視聽語言再次對“走西口”民俗文化以及蒙漢民族融合進行更加全面的解讀。劇中所展現的漫瀚調以鄂爾多斯蒙古族短調民歌為基礎,吸收了來自晉陜地區爬山調的特點,是兩種風格的旋律互相柔和,兩個民族的語言互相使用,更加凸顯出了“西口”地區民族融合的和諧景象。
四、結 語
在中國電影與電視劇市場蓬勃發展、日益繁榮的今天,內蒙古影視也在堅持不懈地奮斗著,尋找著開啟高票房、高收視率秘訣的鑰匙。在關注與挖掘民族題材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其他優秀的地域文化,具有強烈地域特征的“西口”文化經過百年的發展積淀出豐富的內涵,這些內在的情感與故事也值得優秀的內蒙古影視人才深入挖掘,進行藝術創作,這樣不僅可以豐富我們的影視劇創作題材,更能使在影視劇視域下展示的 “西口”文化變成“西口”地區人文歷史、區域環境被重新發現和書寫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