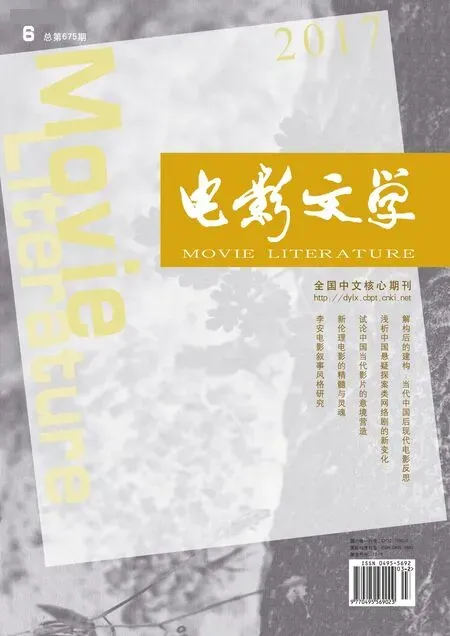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湄公河行動》:主旋律的類型化重構
羅翔宇 彭 晨
(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恩施 445000)
隨著消費時代的來臨,政治、資本和藝術之間構成了復雜的互動與制衡關系,這給當代電影創作帶來了全新的語境,傳統的主旋律電影從中心逐漸被邊緣化。然而,2016年國慶檔上映的《湄公河行動》卻憑借觀眾口碑實現了票房逆襲,并被多家網站評為“2016年度最好的國產電影”。一部以真實案件為創作基礎,以英雄主義為敘事基調的主旋律電影何以得到市場的青睞與追捧?必須承認,作為一部誕生于市場化語境下的主旋律電影,基于政治、資本和藝術之間的三重博弈,對主旋律精神進行類型化重構是《湄公河行動》贏得票房與口碑雙重成功的基本理路。
一、從宏大敘事到類型化敘事的策略轉換
電影作為一種敘事文本,總是不可避免地要被納入某種敘事框架中。傳統意義上的主旋律電影,由于負載著家國情懷所賦予的歷史感和主流意識形態所衍生的使命感,對歷史的影像書寫往往難以擺脫從大處著眼的表達慣性,“宏大敘事”因此成為主旋律電影的基本價值取向。然而,在“宏大敘事”的提出者利奧塔看來,宏大敘事其實包含著未經批判的形而上學。因此,利奧塔對現代理性主義進行了深刻反思,將“不相信宏大敘事”確定為“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立場。不言而喻,這也構成了今天電影敘事的一個總體語境。
毋庸諱言,宏大敘事使得主旋律電影淪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影像摹寫,在中國電影快速走向市場的進程中,主旋律電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困境,承載著強烈官方權力意識的主旋律電影敘事中本能地呈現出的崇高美學追求也被大眾有意無意地消解了。在這種尷尬的境地下,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策略轉型就成了無可回避的現實抉擇。
正因如此,盡管作為對當年震驚世界的“湄公河慘案”的影像再現,《湄公河行動》不可避免地要體現國家意志和權力話語——事實上,電影海報中也充分凸顯了“血性報國”這樣主旋律精神十足的口號,但號稱“類型片游俠”的林超賢依然放棄了宏大敘事的企圖,轉而回歸他最擅長和熟悉的二元對抗故事結構與警匪動作片類型化敘事的軌道。顯而易見,這其中有著來自資本力量的票房考量,但與此同時,權力體系希望借此打破傳統電影對主旋律精神的僵化表達的強烈愿望,也為林超賢提供了類型化敘事的可能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類型化已經被認為構成了電影敘事的基本邏輯。相對宏大敘事被拒斥的當代困境,類型電影有著更為頑強的生命力。“有一個根本的原因支配著類型電影的生存,這便是類型電影用不同的觀念與范式滿足人類具有永恒意義的情思和社會大眾心理情結。”[1]顯然,緝毒題材與跨國追兇,為《湄公河行動》提供了比其他警匪動作片更為豐富的故事資源,而家國情懷和復仇母題則在更深層次上引起了觀眾的共同心理情結。
從宏大敘事向類型敘事的轉型,體現的是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思維從政治導向向市場導向的根本轉變,而林超賢為我們帶來的是電影語言從戲劇沖突、場景設置和人物心理挖掘等多方面敘事格局的提升。我們看到,無論是情節建構、鏡頭運動,還是場景選擇、演員表現,《湄公河行動》都嚴格遵循類型化的故事結構技巧和電影敘事規律。影片從傳統主旋律影片的沉悶乏味和道德說教中跳脫出來,將警匪片特有的節奏感貫穿始終。在大量的快切剪輯與火爆場景的元素背后,呈現的是林氏警匪動作片獨有的暴力美學特征。
主旋律電影從神話回歸現實,并不意味著其內在的意識形態本質被創作者就此遺忘。《湄公河行動》在展現高剛、方新武等角色的現實悲情之后,更強調通過對他們自我犧牲和精神殉道橋段的盡情渲染,來最終實現對觀眾的道德感化與靈魂升華。正如安德魯所言:“類型是意識形態的特殊偽裝,它是決定各種文化機構及其實踐的一處廣闊無形領地中的可見的邊緣,它在暗中作用于觀眾的潛意識。”[2]在這樣的邏輯框架中,觀眾往往不知不覺被完成了文化消費中的精神洗禮和自我超越。
二、從真實故事到戲劇化處理的情節改造
眾所周知,《湄公河行動》以2011年震驚中外的“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和中國警察跨國追捕行動為故事原型,從案發到元兇落網這段驚心動魄的真實歷史構成了電影敘事的基本脈絡。從某種意義來說,影片為基于真實事件改編的主旋律電影提供了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范本和參考意義的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非虛構電影”已經成為全球電影工業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觀眾對源自真實世界的事件和人物有著本能的好奇心,這為“非虛構電影”準備了難得的心理土壤,畢竟,“一切藝術的存在都以審美主體的需要為條件”[3]。《湄公河行動》正是在這樣的接受心理中被觀眾所青睞的。
非虛構電影的一個吊詭之處在于,源自現實的故事框架要求劇情發展主線必須遵循真實事件的演進脈絡,而作為當年舉世矚目的新聞事件,湄公河事件的結局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公開信息,從而幾乎瓦解了電影敘事試圖在這里構建懸念的一切可能。沒有懸念就沒有敘事的魅力,但沒有真實性就背離了非虛構的定位,這就使得電影陷入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兩難境地。
對林超賢而言,“真實”并不意味著原樣復制驚心動魄的破案過程。要在權力話語和市場邏輯的雙重制約中有效打破觀眾對于主旋律的一貫偏見,關鍵還是在于對劇情的戲劇化處理。戲劇化因此成了非虛構電影在真實故事和電影敘事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有效路徑。在電影敘事的推進過程中,林超賢跳出了現實事件的已知結局給電影帶來的敘事羈絆,而將觀眾關注的重心引向對主要人物命運的關切,用包括警犬哮天在內的抓捕小隊成員的生死懸念,填補了主兇必然落網的結局預設所帶來的戲劇性缺憾。
由于題材的特殊性,電影必須將“通過合法方式帶回糯卡”作為劇情的預設前提,但實際上,抓捕糯卡的真實場景本身并不具有沖擊力,這為影片結尾構建戲劇化的高潮帶來了難度。林超賢最終選擇了在湄公河上用好萊塢式快艇追擊的宏大場面重構抓捕糯卡的場景。也正是在這里,方新武以自我犧牲將影片推向了情感宣泄的高潮,同時也為其射殺毒販而產生的內疚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出口,最終完成了自我救贖。
戲劇化不僅僅體現在電影主要人物的命運沉浮上,《湄公河行動》還通過細節的勾勒大膽表現了金三角的娃娃兵群體。吸毒少年的稚氣、人肉炸彈的冷酷、輪盤賭一槍爆頭的血腥,尺度之大令人觸目驚心。在這些橋段里,林超賢用熟稔的手法簡約有力地闡釋了他的暴力美學原則。青少年的恐怖襲擊在國內電影中尚屬首次呈現,林超賢的這個突破不僅有著戲劇化效果的考慮,同時也從側面勾勒了糯卡殘暴與泯滅人性的形象。相比較而言,這比影片對糯卡本人簡單直接的臉譜化表現更加具有震撼的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影片極力追求好萊塢式的寫實主義動作片風格,但《湄公河行動》在道具設計上還存在著港片常見的粗糙手法。同時,盡管林超賢最大限度地渲染了激烈的動作場面,但眾多戰術細節從專業角度來看卻顯得業余。比如,小分隊選擇清晨突襲糯卡營地,其實并不符合突襲行動的時間規律。另外,高剛單槍匹馬營救線人,卻因后援不足導致線人被滅口,這種“增援總是晚來一步”的橋段,盡管符合劇情推進的需要,卻是實際行動中必須避免的失敗樣本。這些缺憾都使得影片的非虛構風格產生了一定的搖擺。
三、從英雄主義到個性化硬漢的人物設定
傳統主旋律電影的核心人物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的英雄。自然地,基于英雄主義美學原則的“高、大、全”形象就成為主旋律電影人物塑造的主線。這使得英雄人物在電影敘事中往往被抽象為一個空洞的符號,而蛻變成政治口號的簡單圖解。
在新的文化語境中,人們的審美需求走向多元化與個性化,“躲避崇高”成為公眾的基本心態,盡善盡美的英雄主義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與當下社會審美意識產生了疏離。正如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大多是神與人的后代,也因此帶有超乎常人的神性色彩,然而,古希臘人并不賦予他們的英雄過分的崇高性,也不以此作為道德判斷的標尺,而是在神性與人性之間來立體建構英雄的性格與行為,把他們作為人生的一種折射。
從神性向人性的復歸其實已成為當代電影對主旋律的人物形象進行類型化重構的基本路徑。《湄公河行動》中,林超賢讓代表正義力量的警察形象走下了神壇,成為人格力量和性格弱點并存的人。英雄人物褪去了神化的光環,而被還原為個性化的硬漢,其語言動作——包括抽煙、粗口等,都有著充分的人性依據,讓人物呈現出原生的真實感。彭于晏飾演的臥底方新武是全片形象最為豐滿、性格結構最為復雜的人物。方新武在對線人逼供的過程中使用了酷刑,這種對警察使用極端手段不加回避的展示在內地電影中是極為罕見的。此外,他為替女友復仇私下射殺毒販,盡管“政治上不正確”,卻符合人物的復仇心態。電影敘事中對方新武偏離軌道的表現也有合理的鋪敘,因其常年在金三角當臥底,在心態和手法上必然要受影響,這構成人物真實行為邏輯的一部分。當然,林超賢不惜筆墨地表現了方新武在恢復理性后的糾結與反省,最后還借高剛之口,表達了方新武“內心不安”的心理狀態,實際上對其復雜人格進行了合理化的解釋和背書。
其實,方新武這個角色是出自林超賢的戲劇化虛構——講述線人的故事正是林超賢的拿手好戲,同時也為《湄公河行動》這樣一部主旋律電影增添了一些港片的元素。應該說,方新武的存在為影片對人性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深挖提供了一個縫隙,看得出林超賢試圖到人物的心理底層探尋其“幽暗意識”的努力——雖然只是淺嘗輒止,但相對片中其他扁平化的英雄人物和臉譜化的反面人物而言,這依然是一個最具典型意義的個性化人物符號。需要注意的是,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下,真實可信的英雄形象更具有價值引領和人格示范的作用,但英雄的人格特征絕不是體現在性格弱點的糾結突變上,而是要深入挖掘其現實行為選擇和崇高美學意義的內在必然性。
毋庸置疑,作為一部警匪動作片,在極具視覺沖擊力的打斗場面背后,能否深入呈現警與匪這兩個激烈對抗的群體之間不同的行為邏輯和心理動因,無疑是判斷導演敘事功力的重要參照。然而,囿于商業電影的敘事定式,除了方新武之外,林超賢對其他人物的塑造則顯得單薄和平面化。尤其是糯卡這一核心人物,完全陷入臉譜化的簡單勾勒,在被貼上“殘暴”“喪失人性”等標簽之后,缺乏對其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從而使得反派角色淪為一個空洞的暴力符號,實際上也使得高剛們的行動失去了一個足以形成對等關系和體現本質力量的立體對象。同時,人物的扁平化與臉譜化明顯限制了演員的角色演繹空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除了直觀的視覺沖擊和淺表的精神狂歡之外,難以深入人物的心理底層去探究人性內涵——而這,正是林超賢們的現實困惑和必須超越的地方。
四、結 語
在政治話語和市場邏輯的雙重壓力下,主旋律電影通過類型化重構來獲得一種微妙的價值平衡無疑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類型化敘事、戲劇化處理和個性化人設也許正是《湄公河行動》在這種艱難平衡中為我們提供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創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