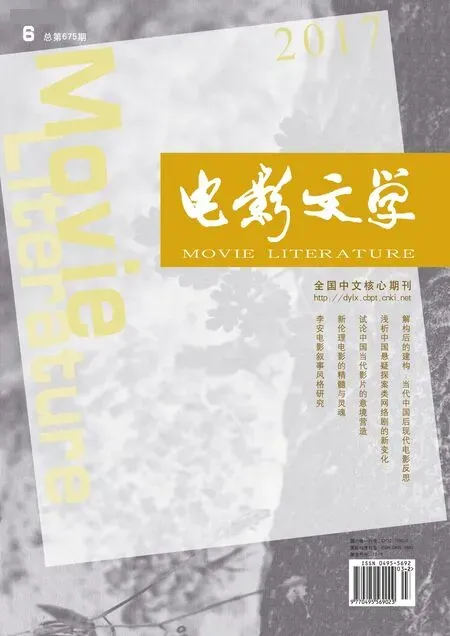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湄公河行動》:紅色電影轉型與英雄形象
趙博翀 李婷婷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030)
紅色題材電影是傳播社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國產紅色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紅色電影呈井噴式發展,如《地道戰》《董存瑞》《上甘嶺》等,主旋律紅色電影在該年代成為電影產業的主流。但在步入新時期后,隨著文化訴求多元發展、文化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以弘揚革命精神為主的紅色電影逐漸失去了市場,能否再度風行于世就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1]國家精神的塑造是紅色電影在新時期成功的關鍵,而縱觀近些年的國產電影,鮮少有影片能給觀眾帶來國家精神和價值的回味與想象。
影片《湄公河行動》的上映打破了紅色電影不叫座的桎梏,在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反響中,《湄公河行動》以突破性的勢態,從四個方面為主旋律紅色電影翻開了新的篇章。
一、供給側改革影響下影片敘事策略改變
事實上,源于中國電影市場內部自我謀求變革的力量似乎從未消失,一旦有了適合創新發展的政策、市場、媒介、觀眾等生態要素,便立即煥發出巨大的生命能量。[2]《湄公河行動》的火熱源于電影市場和觀眾心理的自我變革。當紅色電影走向衰落與國家主義意識不斷強化和蘇醒成為對比,中國電影市場的自我變革由此產生。如《湄公河行動》這種新型紅色電影在供給側改革的影響下,在敘事策略上與其他國產影片有著很大的不同。
整部影片圍繞抓捕糯卡展開,但在敘事上對傳統紅色電影卻極具顛覆性。傳統紅色電影力圖使片中人物形象都表現得極為豐滿,但本片中除了高剛和方新武,其他人的死亡或是受傷均未能在人物表現上有足夠的力度。無論是隊友的受傷還是哮天的死,都沒有給予犧牲者“放大式”的描繪。導演通過此種手法表達一種觀念:在國家利益面前,小我的犧牲是必然會發生的,另類的“英勇就義”的表達方式更是凸顯了影片中人物對于愛國主義使命的堅持與決絕。
這種敘事策略的改變是新時期下生態要素的變化所引起的,是市場自我發展和革新的必然結果。在傳統紅色電影中,統一性和原則性是紅色電影所傳達的基本原則,卻與當代電影觀眾崇尚自我的個性相悖。在本片中導演摒棄了主旋律電影常用的集體意識,用英雄敘事代替集體主義作為價值載體,用個體的情感來渲染國家尊嚴。
個體的英雄主義與人物情感的處理,都是電影市場自我變革后,導演依據觀眾需求所做出的迎合市場與政策的敘事策略。這些變化對于紅色電影來說是積極求變的一種方式。
二、非典型性的英雄塑造
英雄人物的典型性一直是國產主旋律電影走不出的桎梏,影片中為了凸顯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會避重就輕地將其塑造得完美無瑕,這種過于高大的人物塑造方式使得影片的說教性大大增強。目前,中國電影受眾以青少年為主,這些人崇尚自由,對不真實的說教方式感到反感。所以太過刻板、虛幻的英雄形象并不能獲得更高的接受度,也無法使觀眾認同電影傳遞的價值觀。
誠然,英雄主義是紅色影片的重要精神內核之一,也成為影片需要表達的正義的載體,但完美的英雄主義卻并不能與觀眾產生共鳴。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中出現了一些較為驚喜的變化,觀眾眼中的英雄人物開始變得接地氣,縱觀中國電影發展的歷程,更加接地氣的英雄形象是紅色電影發展的必經之路。
如果讓受眾接受英雄人物不完美的一面,則需要更加符合人性的人物設置以及更加合理的故事情節發展邏輯。觀影并非一種單向活動,電影創作者和觀影者通過影片相互溝通、相互說服,當受眾踏進電影院時,電影創作者更加需要尊重受眾的價值觀,信任受眾對人物的包容。
從早期紅色電影的完美英雄,到如今的缺憾式英雄,這種過程在中國電影發展中有跡可循:如《集結號》中的谷子地,導演在保留其英雄主義的同時,將人物的性格刻畫得更貼近現實,增加觀眾對人物的認同感。亦如《戰狼》中的冷鋒,以問題青年的形式另辟蹊蹺,將非主流的英雄形象和個人英雄主義作為代替集體主義的方式,使英雄人物浪漫化,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方式來塑造新型的英雄形象,來規避此種類型片給觀眾帶來的刻板英雄形象。
《湄公河行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得更加極致,方新武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更不是存在于小說中的浪漫主義形象,他并沒有明確的價值體系支撐,人物設置更接近于事實,即使是最后的犧牲與奉獻,也始終無人將英雄的頭銜給他,因為方新武緝毒的目的并沒有那么高尚,他是因為女友吸毒,所以他要更直接地打擊毒販,這種打擊罪犯的形式跳脫了中國警方的“嚴于律己”,私人情感的因素被放大,方新武槍殺邢登,更違背了警察的原則。這種反傳統化的形式將影片中的英雄塑造得更加貼近現實,也更容易使觀眾從情感上產生共鳴。
影片中,方新武的“不完美”體現在三點:第一點是影片開始他對待罪犯時采用了逼供的方式套取情報;第二點是方新武為了知道糯卡的位置,用直升機吊著罪犯進行逼供;第三點也是最為嚴重的一點,方新武在追趕當年殺害其女友的毒梟時,因仇恨沖擊頭腦,私自槍殺了毒梟。顯然,這三點可以體現方新武是一個不守規矩、心狠手辣的警察,并且在警察的身份和復仇者的身份中他選擇了復仇。但是觀眾并沒有對此感到反感,也不覺得方新武因此而發生了變節,觀眾本能地包容人物的情感選擇,也選擇了相信人物。
影片《湄公河行動》中,高剛和方新武兩個角色互為掎角,是一種英雄和普通人之間的辨析,在這種性格的糾葛下,傳統英雄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在影片中不斷切換,既滿足了觀眾對角色的認同感,又增加了傳統英雄主義下國家意志的傳遞。
雖然方新武的角色并非按照英雄的形象來塑造的,但是《湄公河行動》始終是一部顯然易見的紅色電影,影片不再通過人物來傳達正義的力量,卻始終立足人物。即使英雄的形象不再虛幻,但人物在影片中的轉變過程卻一直影響著觀眾對正義和國家的理解,電影創作者給予觀眾一部電影的時間,促使觀眾從一個普通人轉變成謳歌正能量的積極分子,這種轉變是由于觀眾對影片中的人物有著不自覺的代入感,方新武以一種看似“自私”的目的展開緝毒行動,卻在緝毒過程中慢慢升華了自己的思想境界,由小愛到大愛的轉變正是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個人理想和國家發展、社會需求的辯證結合。由此,在影片的開始,觀眾理解方新武,在影片的結尾,觀眾理解了影片。
三、愛國主義與民眾意識的重合
紅色題材電影除了展現與惡勢力斗爭的殘酷外,最重要的精神內核就是愛國主義。大量的紅色電影對于愛國主義的強調都是直接的,用鏡頭和語言不斷提示國家意識,使影片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行為與國家意志相關聯,但口號化的愛國主義語言在影片中不斷重復,卻讓影片產生了教條性,這種教條性被年輕觀眾所排斥,致使票房低迷。
在《湄公河行動》整部影片中,愛國主義并沒有被反復提及,只出現在影片開頭“公安部長”的話中:“當國民安全受到威脅時,國家不會坐視不理。”其他片段我們看到的只是高剛和方新武等人沖破一切阻力的行動。導演將說教淡化,用柔和的方式向觀眾傳達片中人物的信念,激發觀眾在認知和信仰上的認同感,使影片中的人物信念與觀眾意識重合。此類手法常見于近期香港警匪片的風格,如《寒戰2》中:“公仆,是我們的身份,我們的公權力基于民眾的信任 所以我們是民眾的仆人……”這段臺詞在影片的開頭不僅奠定了影片的紅色性質,也從心理上感染了觀眾。
電影中戲劇沖突和懸念是觀影持續性的保證,如方新武女友吸毒的場景放在全片開頭,輔以說明本片背景的畫外音。一來可以從更直觀的角度觀察吸毒者,二來也為影片中段方新武女友的故事設計懸念。觀眾在欣賞電影時對于情節的探索欲望的增強,是保證影片愛國主義內核、減少觀眾對說教排斥的重要因素。
愛國主義核心在本片中通過更加接近現實主義美學的方式表現出來。我們看到的是毒販所設置的各種困難、以身殉職和一往無前的主角們。導演通過情節的處理,用鏡頭和人物提煉出影片的核心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3]以本片來說,其社會效益就是民眾意識的共鳴性。中國電影市場發展迅速,但凝聚民族意識的影片卻少之又少,當美國的超級英雄們在銀幕前訴說著美國的價值觀時,中國觀眾更為期待的是一部可以與當前民眾意識相吻合并能夠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影片。《湄公河行動》中,大量的動作設計和鏡頭調動,是導演對于經濟效益的索求,也是導演較為擅長的部分。而影片開頭“公安部長”擲地有聲的話語和結尾處糯卡案的最終結案則是導演對于社會效益的貢獻的表達。
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紅色電影并非與電影市場的觀眾需求大相徑庭。在中國電影市場,成熟的導演會利用和借鑒好萊塢英雄電影的長處來滿足屬于中國觀眾自己的價值和認識。這類影片目前雖然并未成為電影市場的主力,但在中國觀眾的民眾意識不斷崛起的今天,這樣的影片已成為國家形象塑造和國家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途徑。
四、互聯網+語境下的話題時效性
隨著科技的發展,互聯網對于電影行業的影響越來越大,互聯網的點擊率、評分機制、話題關注度已成為電影傳播和票房的保證。而多途徑媒體的傳播速度也進一步推動著電影創作、推廣和發行的改革。
在此基礎上,對于電影創作者來說,話題的時效性就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網絡文學,還是游戲故事,當事件的關注度達到一定高度,依托互聯網的廣泛宣傳,是互聯網給予電影行業創作革新的重要方式。而對于紅色題材的電影來說,依托話題的時效性將近些年所發生的熱門事件加以整理,通過網絡發酵的方式篩選出可弘揚民族價值的事件,從而提煉出適合的故事,這是互聯網賦予紅色電影的市場機遇。
真實事件往往是現實主義的有利依據,《湄公河行動》的火熱正是依托了該真實案件的敏感性和將糯卡抓捕歸案的話題性。從《解救吾先生》《心迷宮》《追兇者也》到《湄公河行動》,真實事件依托網絡熱點都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
互聯網改變電影行業的不僅僅是題材的選擇,還有營銷方式。片方雖未利用明星和網絡對影片進行炒作,但《湄公河行動》在上映之初,因其本身事件的反響程度,各大網站通過對事件的回顧、案情的梳理,利用互聯網作為營銷渠道,依托事件本身的市場號召力,來對影片進行宣傳,無形中增加了觀眾對影片的關注度。在影片上映的過程中,又恰逢湄公河事件5周年,話題性和時效性再度依托網絡增加,且延長了本片的輿論熱度,從而吸引了更多的觀眾。
五、結 語
《湄公河行動》的成功是主旋律紅色電影一次頗有意義的轉型嘗試,商業價值和社會效益的重合是紅色題材的電影借英雄主義傳播價值觀和文化觀的一種途徑。從某種程度來說,《湄公河行動》的成功已遠遠超越了作品本身,在受眾心理、話題時效性、敘事策略、社會影響等方面都可作為研究的案例。本片的票房佳績也可以說明,中國電影觀眾對于主旋律電影是包容的,他們所排斥的僅僅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和虛幻的英雄形象。《湄公河行動》的成功雖然改變不了紅色電影長期以來在數量和質量上與其他類型影片的差距,但可以作為一種方向性的指引,若想在電影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紅色題材的電影必須出新求變,在各個方面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