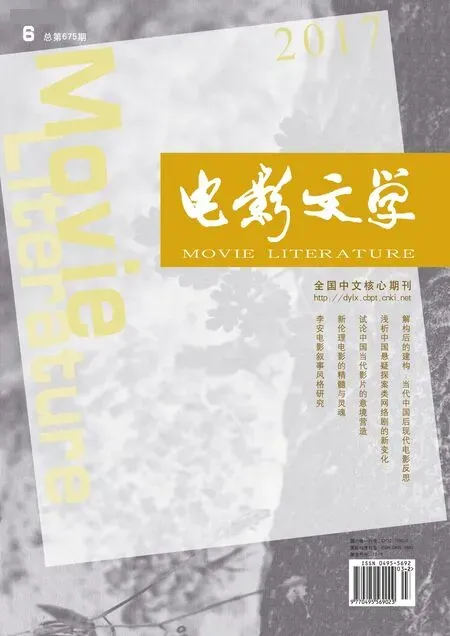論哈薩克族題材電影《鮮花》的敘事藝術
趙全偉 祁曉冰
(伊犁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新疆 伊寧 835000)
《鮮花》是一部反映哈薩克民族獨特藝術形式阿肯阿依特斯的影片,由新疆天山電影制片廠出品。作為一部新疆本土電影,該片濃郁的地域民族色彩使其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影片用倒敘的手法,講述了一個哈薩克族女阿肯的成長故事,同時為觀眾展開了一幅由雄雪山草原、駿馬歌舞組成的哈薩克游牧文化畫卷。
一、對哈薩克族阿肯阿依特斯的藝術呈現
電影《鮮花》講述的是一個哈薩克族女阿肯的成長故事,影片在悠揚的冬不拉彈唱聲中拉開序幕。片頭,喀拉峻阿依特斯培訓班的學生們彈唱著一支旋律優美的阿依特斯:“生命的長河直直彎彎,時而平靜,有時波瀾,珍惜生命的人啊,才能勇敢地跨過萬水千山,我的阿吾勒駐在青川河。夏牧場熱鬧非凡日日盛典,我無法言語美好的一切,我會像棗騮一樣飛奔絕不落后。”這支哈薩克族民歌為影片營造出濃郁的民族色彩。
影片主人公鮮花伴隨著冬不拉琴聲出生。冬不拉是哈薩克族傳統民間樂器,是阿肯阿依特斯演奏必備伴奏樂器,在影片中是一個重要的傳情達意的主導意象。電影開場,在一片黑暗的背景中,一束光從冬不拉琴箱上的圓孔中照射下來,鮮花的母親古萊依深深熱愛阿依特斯,臨產前背著家人偷偷跑去參加喀拉峻草原舉行的阿依特斯大會,結果鮮花在大賽上伴著冬不拉的琴聲降生了。
阿依特斯是即興表演的哈薩克族原生態藝術,有搖籃歌、挽歌、謊言歌、阿肯歌、哭嫁歌等形式。[1]《鮮花》以阿依特斯結構情節,表現主人公鮮花的成長與命運。“睡搖籃”篇中,鮮花在阿依特斯大會上伴隨少年卡德爾汗的歌聲降生,熱愛阿依特斯的古萊依在女兒“睡搖籃”儀式上給女兒送上了“但愿她成為有出息的阿肯”的祝福,然后就按照哈薩克族傳統的“還子”習俗將她過繼給了公婆做女兒。公公胡賽因是草原上著名的阿肯,在鮮花的搖籃邊用歌聲祝福女兒健康成長。“挽歌篇”中,鮮花遭遇喪父之痛。鮮花已經五歲了,卻一直不會說話,被同伴們稱作啞巴,此時因為父親的去世突然心慟而歌,創作了一首感人的挽歌:“生命的長河直直彎,時而平靜,有時波瀾。珍惜生命的人啊,才能勇敢地跨過千山萬水。”歌聲中有對逝者的哀思,有對生命的敬畏,有難以名狀的悲傷。哈薩克族的喪葬習俗中有唱挽歌的習俗,挽歌是歌者即興創作并現場演唱的,他們是詩人也是藝術家。開始說話唱歌的鮮花后來成長為草原上的著名女阿肯,同時也因為唱歌迎來了愛情。“謊言歌篇”中,鮮花與著名阿肯卡德爾汗對唱謊言歌,鮮花唱:“我把一根羽毛放在卡車上,卡車竟拉不動它癱在大路上。我讓老鼠拉著大車走,那車竟像暴風吹向前方。”卡德爾汗對唱道:“我在隆冬的雪原栽下一棵小樹,我讓黑色的甲蟲充當馬夫……”卡德爾汗唱:“我騎上最快的蚊子四處奔跑,去丈量每一片天空和土地。我讓一千匹駿馬游牧在我家的房頂……”鮮花機智地對唱道:“風干的羊肚掛在撐竿上飄動,大力士好不容易才將它掀動……”阿依特斯是即興演唱,謊言歌歌詞詼諧幽默,盡顯阿肯的機智與智慧。在這場謊言歌的對決中,鮮花與卡德爾汗這兩個阿肯在彈唱技藝的切磋中悄然萌生了愛意,兩顆心緊緊地系在了一起。卡德爾汗承諾來年的古爾邦節來看鮮花。“阿肯歌篇”中,二人鴻雁傳書,愛情不斷升溫,鮮花熱切盼望能早日見到卡德爾汗,但卡德爾汗由于演出繁忙失約,未能在古爾邦節到來時與鮮花相會。爽約遲來的卡德爾汗請求鮮花諒解,但鮮花經過慎重考慮拒絕了卡德爾汗。心有不甘的卡德爾汗要求對歌,表示只要鮮花唱贏了,就尊重鮮花的選擇。卡德爾汗唱:“你是潔白的天鵝,既能在湖里棲息,也能展翅飛翔。請你告訴我世上沒有的七樣東西。”鮮花唱:“鳥兒沒有乳汁,馬沒有膽囊,水沒有骨頭,石頭沒有根,天空沒有撐桿,舌頭沒有支點,魚兒沒有聲音。”鮮花贏得了對唱,卡德爾汗失望而歸,留在草原上的鮮花遇到了她“氈房的頂梁柱”——樸實的鄉村醫生蘇力坦。“哭嫁歌”篇中,鮮花與蘇力坦喜結良緣,婚禮上女伴們唱起了“加爾加爾”(哭嫁歌):“女兒大了該找婆家,加爾加爾。草木開花才能結果,加爾加爾。”鮮花也為自己唱起了哭嫁歌:“難以舍棄的情感無法遣散,再見了我吉祥的門欄。”歌聲中有對娘家親人的留戀,對未來婚姻生活的迷惘。
阿依特斯在哈薩克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哈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阿肯彈唱幾乎無處不在,無論難過悲傷,抑或歡欣激動,彈唱總是在哈薩克族的生活中靜靜流淌,抒發著哈薩克人民心中真摯而熱烈的情感,表達著哈薩克族群眾對生活的豐富體驗。影片中鮮花的人生烙印著深深的冬不拉的印記。影片采用倒敘手法,以鮮花母親翻閱鮮花的日記結構故事,日記里鮮花記錄了自己的出生、成長以及在一次次阿依特斯大會上的活動。面對一次次挫折和痛苦,彈唱始終是鮮花堅持走下去的精神支撐。仿佛一個輪回,鮮花的女兒也在她的冬不拉彈唱中出生、成長。一代一代的阿肯,一段一段的彈唱,影片始終圍繞冬不拉彈唱敘事,從鮮花教女兒撫弄冬不拉開始,也以冬不拉彈唱結束。
二、對哈薩克族傳統文化的詩意詮釋
作為一部新疆哈薩克族題材的電影,《鮮花》也廣泛展現了哈薩克族的民俗文化和風土人情,例如,反映哈薩克族物質民俗的氈帽皮衣、包爾薩克(一種哈薩克族的油炸面點)和馕、氈房與彩繡壁畫、馬拉雪橇、馬鞍皮鞭等,是影片中彰顯民族特色的重要元素。這些民俗事項直觀地呈現了哈薩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構成了影片主人公鮮花的生活場景,營造了獨特的草原文化氛圍,也在視覺上給觀眾一種具有濃郁異域風情的審美感受。電影的民俗性并不是簡單地追求記錄民俗,而是“將豐富多彩的民俗生活展現于電影中,作為電影敘事與審美構建的載體和手段”[2]。除了這些表層的以背景形式出現的物質民俗外,《鮮花》中具有深刻文化蘊含的是對哈薩克族精神民俗的呈現,包括歲時節慶、人生禮儀、宗教信仰、俗語諺語等,這些民俗文化巧妙地與故事融為一體,烘托著影片的氣氛,推動著情節的發展。
首先是節慶活動。哈薩克族的節日主要有古爾邦節、肉孜節、那吾魯孜節等,影片中重點呈現了古爾邦節的熱鬧場景。鮮花和卡德爾汗相約定情的時間是古爾邦節。與農耕民族張燈結彩慶祝節日不同,草原上的哈薩克族以其獨特的方式慶祝他們的傳統節日。在一片蔥綠的草原上,匯集著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牧民,每人一騎,揚鞭奔馳,好不熱鬧;角力、阿肯彈唱、叼羊等慶祝活動隆重登場,人們盡情歡樂,遼闊的草原連著遠處的雪山和湛藍的天空、奔馳的駿馬、搖曳的韁繩、矯健的青年、白色的氈房璨若群星。慶祝節日的人們在草原的懷抱中,在悠揚的冬不拉的琴聲中,在自由的環境里,盡情釋放自己的歡快和激動。
其次是人生禮儀。《鮮花》在細節處理上有著獨到之處,老人虔誠的祈禱、新生命誕生后的祝福、氈房里的衣食住行無一不在展示風情濃郁的哈薩克族民俗。鮮花在阿依特斯大會上出生,家人為她鄭重地舉行了“別斯克討依”,即“睡搖籃”儀式。氈房里的老婆婆將嬰兒放在搖籃里,爺爺胡賽因為她起名鮮花,并在她耳邊連喊了三聲“鮮花”,然后老婆婆拿起搖籃下托盤里的食物撒給小孩子們吃,希望嬰兒能和別的孩子一樣快快成長。鮮花身世特殊,作為家族中長子的第一個孩子,鮮花一出生就被父母按照民族的“還子”習俗過繼給了自己的爺爺奶奶撫養。所謂“還子”習俗,就是子女把自己的孩子過繼給自己的父母,這就近似于重組了一個家庭,家庭成員的關系被重新定位,爺爺變成了爸爸,媽媽變成了嫂子,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誕,但在以游牧生活為主的草原,卻有著極具人性化的意義。當父母逐漸老邁,兒女成家立業,把孩子過繼一個給父母,其實帶有一種“孝”與“反哺”的意義。父母有了過繼給自己的孫子陪伴身邊,可以再享天倫之樂,也可以在年老時得到這個過繼孩子的照顧。同時將孩子過繼給父母的已婚子女,因為有親骨肉在父母身邊的緣故也會與父母有更密切的聯系。鮮花過繼給了爺爺胡賽因,胡賽因夫婦老年得女,對鮮花疼愛有加,稱呼鮮花為“小羊羔”“小寶貝”。此外,影片還反映了哈薩克族的挽歌習俗和哭嫁習俗。在胡賽因的葬禮上,男人在茫茫白雪中駕著“雪爬犁”匯成一股流動在雪海之中的船隊,表達對逝者的哀悼和敬意;氈房里女人們以哀婉感人的挽歌表達對親人的悼念。古萊依唱的挽歌“我高高的城堡轟然倒塌,我盈盈的淚水滾滾而下”讓眾人動容。與之相對的,是在鮮花的婚禮上,在空曠的草原上,眾人圍繞氈房載歌載舞,用集體的吟唱表達對新人的祝福:“春天來了樹要開花,加爾加爾。女兒大了該找婆家,加爾加爾……你要到新的地方生活,加爾加爾。你要去的是善良人家,加爾加爾。”
此外還有語言民俗。胡賽因是草原上德高望重的老阿肯,能出口成章,嘴里不斷涌出富有哲理的哈薩克族俗語諺語。鮮花五歲了還不曾開口說話,母親憂心忡忡,胡賽因安慰妻子“別把紐扣那么大的事情,看成駱駝那么大”“人在幸福的時候流的眼淚才有價值”,這里的喻體完全取自草原,源于哈薩克族的日常生活。這些俗語諺語的使用,看似非常口語化、日常化,卻睿智巧妙,內涵深刻,反映著哈薩克民族的堅韌豁達、積極樂觀向上的民族性格和生命態度,讓人回味無窮。
三、對文化沖突的反思
《鮮花》也理性反思了哈薩克文化現代轉型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對沖。面對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沖擊,《鮮花》并未一味地表現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和矛盾,而是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展現現代化對哈薩克族生活的影響,如研究者所言:“巧妙地表現了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下來的哈薩克族人的民族心理。”[3]
影片中卡德爾汗和鮮花的愛情無疑是令人唏噓的。電影始終圍繞阿依特斯敘事,片中有兩次阿依特斯大會。鮮花在阿依特斯大會上,在少年卡德爾汗的彈唱聲中降生,按照古老的習俗,胡賽因抱著后來過繼給他做女兒的孫女,讓卡德爾汗親吻了鮮花的額頭以示祝福。鮮花和卡德爾汗長大后,兩人又因阿依特斯競技對唱聚在一起。兩人從“不打不相識”而后互相愛上彼此,然后遺憾地分道揚鑣。觀眾可能會以為是因為鮮花不愿意離開草原,而卡德爾汗卻已然心屬城市,才導致二人未能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些人認為影片借此表達了鮮花對草原的眷戀不舍,隱含了對卡德爾汗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背離了傳統,離開世居草原選擇的批判。其實,這是頗為片面的理解。鮮花不愿意離開草原,并非抗拒城市,在草原現代化推進下,鮮花不可能不被影響和觸動。從卡德爾汗用錄音機給她傳遞訊息開始,就已經在悄悄改變著這個草原姑娘。卡德爾汗積極地去城里發展,在給鮮花的錄音中勸說鮮花跟他去城市:“這里的觀眾很喜歡我的表演……鮮花,我覺得這里的空間比草原大得多。”鮮花非常猶豫矛盾,但最終還是出于對孤身一人留在草原的母親的擔憂,她不得不正視現實,拒絕了卡德爾汗,選擇留在草原。電影中卡德爾汗是一個能跟得上潮流的年輕人,在他和朋友策馬揚鞭之時,互相在奔馳的馬背上傳遞播放著國際巨星邁克爾·杰克遜的Dangerous的錄音機。他懂得接受外來新鮮的事物,對生活有自己的追求,他期盼自己的歌聲不僅響在草原,更希望草原之外的廣闊世界能有更多的人聆聽、了解哈薩克族音樂,欣賞優美的冬不拉彈唱。電影的最后,鮮花作為哈薩克阿依特斯的傳承人,自己辦了喀拉峻阿依特斯培訓班,這一結局恰好說明鮮花的扎根草原,不只是對傳統文化的執著,其實也和卡德爾汗的追求有殊途同歸的意義。所以說,鮮花堅守的不是傳統,而是對音樂的熱愛,只有真心熱愛音樂、熱愛阿依特斯,傳統文化才能舊樹結新果,煥發新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