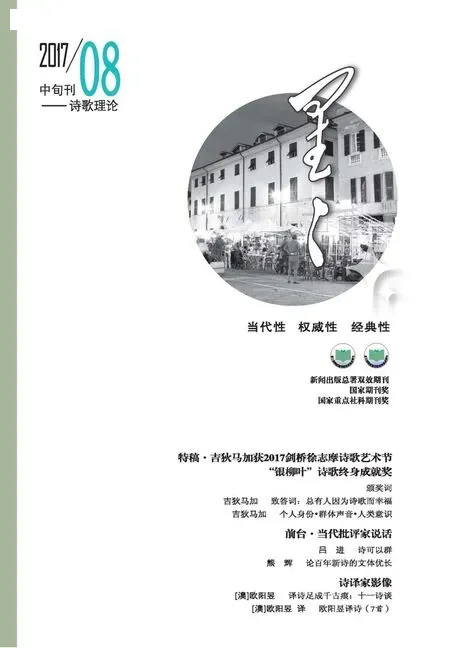論百年新詩的文體優(yōu)長(zhǎng)
熊 輝
論百年新詩的文體優(yōu)長(zhǎng)
熊 輝
舍棄沿用千年的文言書面語,采用明白曉暢的口語白話;背離傳統(tǒng)詩歌的藝術(shù)津要,保留分行排列的自由外型,遂在漢語文學(xué)的歷史中產(chǎn)生了一種新體,這便是我們常稱的“新詩”。在誕生之初的草創(chuàng)期,不管新詩遭遇了多少詬病,接受了多少冷眼,甚或在寂寥中一度面臨自我消亡的死路,但它在少數(shù)人刻意的“自娛自樂”中兀自生長(zhǎng),枝繁葉茂,遮蔽了昔日詩詞歌賦的天空,成為中國(guó)文學(xué)園地中不可或缺的構(gòu)成要素。
百年新詩的發(fā)生,堪稱文學(xué)發(fā)展的奇跡。在知識(shí)階層眼中,古詩文體觀念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早已根深蒂固,在沒有任何創(chuàng)作準(zhǔn)備的情況下,胡適諸君立意用觀念中的詩體取而代之。即便是在改革創(chuàng)新的浪潮中成長(zhǎng)起來的我們,想起新詩革命,尤有后怕,深恐它在“守舊派”的圍攻中不堪一擊。世事在偶然中演繹著必然,很多看似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卻因?yàn)閼?yīng)和了某些潛在的發(fā)展趨勢(shì),最終的結(jié)果讓人大跌眼界,硬是將不可能之事變成了活生生的事實(shí)。18世紀(jì)以降,世界詩歌朝著自由化方向發(fā)展,蘇格蘭的彭斯開始收集整理民歌,英格蘭的華茲華斯和柯列律治以“歌謠”的名義創(chuàng)作詩歌,他們的目標(biāo)就是要讓詩歌變得淺俗易懂,擺脫蒲柏為代表的古典主義詩風(fēng)的束縛;美國(guó)詩人惠特曼及至后來的意象派運(yùn)動(dòng),其旨趣無疑集中于解放英語詩歌的形式和語言。美國(guó)女詩人洛威爾的《意象派宣言》,被公認(rèn)為是胡適《文學(xué)改良芻議》的藍(lán)本,而另一位女詩人蒂斯代爾的詩作《關(guān)不住了》,被胡適翻譯成中文后視為新詩的“新紀(jì)元”,意即胡適心中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首白話新詩。由此不難看出,從新詩觀念到新詩作品,胡適的做法帶有很強(qiáng)的借鑒色彩。正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種“借鑒”帶來中國(guó)詩歌創(chuàng)作的巨大轉(zhuǎn)折,新詩“橫空出世”并迅速確立了文壇正宗地位。這其中的關(guān)鍵之處,在于胡適引入了什么樣的新觀念,更在于中國(guó)詩歌的發(fā)展需要什么樣的變革和突圍,又或者在于新詩的出現(xiàn)滿足了什么樣的時(shí)代訴求,幾種因素的集合,促成了新詩的發(fā)生。
百年新詩的發(fā)展,最大的成功是確立了自身的文體優(yōu)勢(shì)。胡適“一時(shí)代有一時(shí)代之文學(xué)”的說法,固然帶有進(jìn)化論的局限,卻也道出了文學(xué)發(fā)展的普遍常理,要不我們就會(huì)一直生活在古人的陰影里,“自我”永遠(yuǎn)進(jìn)入不了民族詩歌的譜系。正如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中談到,“后來者”詩人必須通過一系列的“修正比”,才能打敗強(qiáng)者詩人進(jìn)入歷史。著名學(xué)者趙毅衡先生是中國(guó)形式主義文論的開拓者,他在《斷無不可解之理》一書中,說中國(guó)詩歌表達(dá)的所有情感自《詩經(jīng)》就已有之,歷代詩人之所以還要不厭其煩地重復(fù)表達(dá),并佳作不斷,主要原因便是表達(dá)的方式不同。新詩較之古詩,最明顯的差別就是語言和形式的疏離,亦即文體各異。我們常常見到很多人拿古詩平仄押韻之類的優(yōu)長(zhǎng),來批駁新詩不押韻不整齊的“不足”,這實(shí)在有違比較的原則,好比拿馬的奔跑去比牛的緩慢,得出的結(jié)論當(dāng)然是前者優(yōu)于后者。殊不知,兩個(gè)本就不同的物類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比較?實(shí)際上,新詩文體也有自身的優(yōu)勢(shì),呂進(jìn)先生在《中國(guó)現(xiàn)代詩學(xué)》中認(rèn)為所有的抒情詩,包括新詩中的抒情詩都是“內(nèi)視點(diǎn)”文學(xué),我們不必拘泥于外在形式一端,而忽視了其內(nèi)在的形式特征。推而論之,與古詩注重外在形式相比,新詩更注重內(nèi)在節(jié)奏。郭沫若在《三葉集》中寫道:“我想我們的好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表現(xiàn),命泉中流出的strain,心琴上彈出的melody,生底顫動(dòng),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nèi)祟惖讱g樂底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guó)。”這雖有華茲華斯“詩是強(qiáng)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影子,但卻開辟了新詩內(nèi)在節(jié)奏或內(nèi)在音樂性的傳統(tǒng)。何其芳認(rèn)為,詩歌情感的跌宕起伏仍然可以造成很強(qiáng)的音樂性效果,大可不必像古詩那樣僅憑借外在形式來造成朗朗上口的音韻效果。于是,新詩因其“內(nèi)視點(diǎn)”的文體特征,建構(gòu)起了內(nèi)在韻律和節(jié)奏,比起古詩的外在音韻而言,不但不會(huì)制約詩情的表達(dá),反而讓形式與內(nèi)容合為一體,或者形式成為內(nèi)容的構(gòu)成部分,顯示出自身特殊的形式美感來。
新詩文體的另一優(yōu)勢(shì),當(dāng)然是語言的白話化。不少人認(rèn)為,新詩采用白話文或白話口語作為表達(dá)語言,是詩歌語言的退化乃至災(zāi)難,因?yàn)槠溲胖潞湍毜幕咎卣麟S之淪喪。應(yīng)該警醒的是,此時(shí)的白話與口語之間并非等同關(guān)系,否則清末流行的白話報(bào)當(dāng)被視為新文學(xué)的開端,又抑或是胡適所謂的古已有之的白話文學(xué)當(dāng)被視為新文學(xué)一脈相承的前生。僅就詩歌的角度而論,按照俄國(guó)形式主義代表學(xué)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散文或敘事文學(xué)的語言因語法的規(guī)約,造成對(duì)日常語言的陌生化,詩歌語言則因語法和表達(dá)的超出機(jī)制,造成對(duì)散文語言的陌生化。據(jù)此而論,日常的白話口語與詩歌語言之間相隔三層,即便是白話口語,只要它成為了新詩的語言,那就與日常的白話口語不可等同視之。根據(jù)黑格爾《美學(xué)》中的藝術(shù)觀念,呂進(jìn)先生將新詩語言視為“媒介”,即詩歌是最高的藝術(shù)形式,也是高度精神化的藝術(shù),其媒介也從日常的物質(zhì)中抽離出來而化為精神性的存在,故而詩歌是向散文借用文字媒介。從這個(gè)角度來講,新詩中的白話口語也斷然不是日常使用的語言。拋開俄國(guó)形式主義和黑格爾的詩歌語言觀,我們還可以從語言形成和演變的角度來加以分析,進(jìn)一步厘清新詩語言白話的文體優(yōu)勢(shì)。新詩語言在存在形態(tài)上與白話口語相似,但其來源卻相當(dāng)豐富,至少古代漢語、外國(guó)語言和日常口語是它的三大來源。古代漢語、日常語言和白話文血脈相連,彼此影響和滋生自不必贅述,僅就外國(guó)語言資源一端來講,胡適、傅斯年以及魯迅等人曾多次宣稱,要用外語詞匯的豐富性和外語語法的精密度來彌補(bǔ)漢語表達(dá)的缺陷,因此現(xiàn)代漢語幾乎與生俱來地具有“歐化”或“外化”的特點(diǎn),從另一個(gè)角度來講,也表明漢語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和吸納性。由以上分析可知,新詩因采用了白話文而更具文體優(yōu)勢(shì),新詩語言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shù)性和語言張力,更具有較強(qiáng)的接納性和適應(yīng)性。這似乎也印證了周作人在《新文學(xué)的源流》中所說,“舊皮囊”裝不下新思想,于是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必然會(huì)發(fā)生,直接的后果便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后,更適應(yīng)表達(dá)當(dāng)下思想和情感。
百年新詩的繁盛,不只體現(xiàn)為作品數(shù)量的劇增和佳作的涌現(xiàn),也體現(xiàn)為新詩批評(píng)的活躍。胡適在新詩發(fā)軔之初寫作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和后來的《談新詩》等文章,倘若算是新詩批評(píng)的早期成果,那聞一多、郭沫若、朱自清等人對(duì)新詩作品的評(píng)論或關(guān)于新詩問題的看法,便匯聚成了新詩批評(píng)的主流,才得以使今天的中國(guó)現(xiàn)代詩學(xué)蔚為大觀。詩歌評(píng)論也許并非源自批評(píng)的目的,而是根源于情感的交流。古時(shí)品茗或酌酒的興致,無外乎文朋書友的詩詞唱和;離別的憂傷或相逢的喜悅,也都消融成感人的詩句。有贈(zèng)有還,那些答謝的詩詞無疑成為對(duì)友人作品的最好回應(yīng);演變到今天,面對(duì)感動(dòng)自己的詩歌,書寫相應(yīng)的心靈感悟,或者與之相關(guān)的世風(fēng)民俗之雜感,就成為所謂的評(píng)論文章。隨著中國(guó)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xué)之建立,也隨著各學(xué)科門類的建設(shè)完善,專門從事新詩研究的學(xué)者日益增多,新詩研究?jī)叭怀蔀橐婚T“學(xué)問”,成為人們專攻的術(shù)業(yè)。當(dāng)然,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xué)評(píng)論,似乎肩負(fù)著更為沉重的使命,論者倘若不能窺見作品隱秘的意涵,僅談與己相關(guān)的感受,其評(píng)論會(huì)被嚴(yán)肅的學(xué)院派譏為“讀后感”。在西方文論和批評(píng)方法肆意橫行的時(shí)代,我們的確借助不同的視角看到了很多“空白結(jié)構(gòu)”,可供言說的內(nèi)容更為豐富。這樣一來,文學(xué)批評(píng)就不再停留在心靈的溝通層面,它更多地呈現(xiàn)出思想和哲理的色彩,文學(xué)批評(píng)儼然成為書寫時(shí)代的思想史。詩歌批評(píng)亦然,各種理性的分析充斥著詩歌評(píng)論界,只有心靈的碰撞似乎無以寫作評(píng)論,它越來越成為知識(shí)性的寫作方式,成為少數(shù)人可以從事的“行當(dāng)”。甚至有些人僅僅是借助評(píng)論之名,暗行闡發(fā)自我心跡或思想觀念之道,讓詩歌評(píng)論遠(yuǎn)離了作品和讀者。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文學(xué)評(píng)論包括詩歌評(píng)論的精英氣或?qū)I(yè)化,使其逐漸獨(dú)立成新的文學(xué)文本,或者使其具備了與普通文學(xué)文本不一樣的氣質(zhì),那就是理性的思考和深度的思想。
伴隨著新詩批評(píng)的興起,專門的新詩研究機(jī)構(gòu)逐漸建立,這真可謂百年新詩歷史中的大事。現(xiàn)代時(shí)期的新詩批評(píng),多為詩人談詩,雖免除了“隔靴搔癢”的弊病,但缺少系統(tǒng)性的言說思路,終難見到體系化的新詩研究專著。郭沫若、宗白華和田漢合著的《三葉集》,常被譽(yù)為是研究新詩的第一本專著,但其中對(duì)美學(xué)的論述不免破除該書談新詩的專一性,況且它是三人的通信集,還不能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新詩研究專著。廢名是將新文學(xué)引入大學(xué)課堂的先行者,其專著《談新詩》仍由獨(dú)立的論文構(gòu)成,實(shí)際上就是一部談新詩的論文集。1948年,朱光潛在正中書局出版的《詩論》是真正意義上的學(xué)者型專著,此書雖不專事新詩研究,但卻在中西詩學(xué)相互闡發(fā)的基礎(chǔ)上,開啟了中國(guó)現(xiàn)代詩學(xué)的開闊視野,具有狹義詩學(xué)的普遍性意義。學(xué)者型新詩研究時(shí)代的到來,應(yīng)該與新時(shí)期活躍的學(xué)術(shù)氛圍有關(guān),也正是由于大學(xué)集聚了一批專門從事新詩研究的學(xué)者,于是新詩研究機(jī)構(gòu)呼之欲出。1986年6月,西南大學(xué)的呂進(jìn)教授與方敬研究員、鄒絳研究員一道,建立起了新詩歷史上第一家獨(dú)立建制的新詩實(shí)體研究機(jī)構(gòu),開創(chuàng)了新詩批評(píng)歷史的新局面。呂進(jìn)先生專門研究新詩文體,是典型的“形式論”者,其代表作《中國(guó)現(xiàn)代詩學(xué)》的精要部分,就是談新詩的語言和形式,這是一部體系化的新詩文體研究專著,此外還出版了《新詩文體學(xué)》《現(xiàn)代詩歌文體論》《中國(guó)現(xiàn)代詩體論》以及5卷本的《呂進(jìn)文存》等。呂先生是那輩學(xué)人中將“新詩之所以為新詩”闡述得最清楚的學(xué)者,也就是說他充分把握了新詩的文體特征,而且他的研究系統(tǒng)性和思辨性很強(qiáng),有深刻的西方美學(xué)思想和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作為支撐,相較于那個(gè)時(shí)代的其他新詩研究者言,具有突出的新詩研究品格。2010年9月,北京大學(xué)詩歌研究院成立,院長(zhǎng)為著名詩歌評(píng)論家謝冕先生。謝先生的新詩研究富有才情和思想的洞察力,其著作《湖岸詩評(píng)》《共和國(guó)的星光》《詩人的創(chuàng)造》《中國(guó)現(xiàn)代詩人論》《新世紀(jì)的太陽》等便體現(xiàn)了這一研究特點(diǎn)。此外,安徽師范大學(xué)、首都師范大學(xué)以及南開大學(xué)等高校紛紛建立了新詩研究機(jī)構(gòu),在高校推行學(xué)科建設(shè)的語境下,顯示出新詩研究和批評(píng)的中興。
新詩百年,無論我們接受與否,它已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并發(fā)展下來,成為我們無法送還的民族文學(xué)遺存。站在新的歷史起點(diǎn)上,展望新詩的美好前程,祝愿新詩多出名篇佳作,似乎才是我們今天紀(jì)念新詩百年的題中之意。

熊輝,1976年生,四川鄰水人,文學(xué)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代詩學(xué)及翻譯文學(xué)研究,兼事詩歌評(píng)論,現(xiàn)供職于西南大學(xué)中國(guó)新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