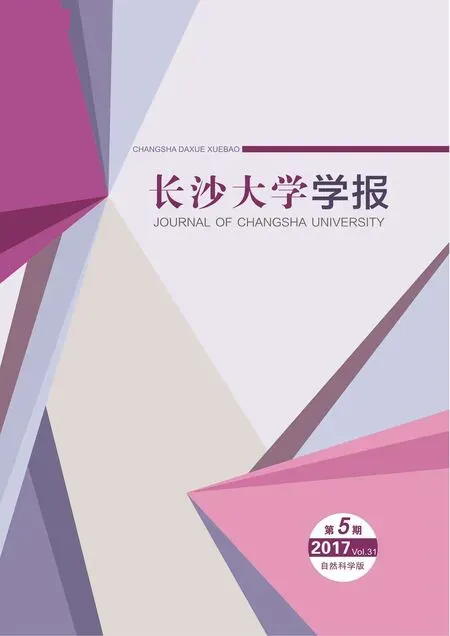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耦合分析
何如海,李 欣
(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耦合分析
何如海,李 欣
(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基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視角,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蕪湖市200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2000-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效益耦合協調度呈上升態勢,但程度不高;(2)經濟發展相對超前,環境保護相對滯后,社會經濟系統已出現對生態環境系統的限制作用;(3)兩大效益耦合協調發展波動性強,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有待進一步完善.今后蕪湖市應正確應對建設與生態的齊頭并進,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循環經濟的創新.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蕪湖市
城市土地具有位置固定性、差異性、耐久性、稀缺性、區位效益性、邊際產出遞減性等特性,是人類社會各類活動不可或缺的物質載體.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直接影響到城市空間結構的演化與城市的興衰發展,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高低[1].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反映了土地利用對城市發展所作的貢獻,是土地資源要素優化配置的集中體現,是投入資源價值實現程度的綜合反映.城市化的迅猛發展促使城市土地利用不僅激發出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同時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態環境效益也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2].目前,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在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方面多有研究和建樹,國外相關研究多側重于以 Costanza R(1997)為鼻祖的土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論[3]的研究,對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研究多集中于經濟效益;國內現有研究側重定性和靜態的探討[4,5],而定量和動態研究主要集中于東南沿海的發達城市[6,7]、全國范圍[8]以及干旱地區[9,10],而對于華東地區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程度的研究較少.本研究以蕪湖市為例,基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視角,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蕪湖市200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進行分析,以期為城市土地的高效協調利用和科學管理提供借鑒.
1 研究區概況
蕪湖市位于長三角西南部,介于117°58′~ 118°43′E、30°38′~31°31′N 之間,是華東地區重要的工業科教基地、長三角大城市.土地面積6026km2,占安徽省的4.32%.經政府初步核算,2015年,全市生產總值達到2457.32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十二五”期間,蕪湖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5%,居全省第一[11].
2 指標構建與研究方法
2.1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指標體系構建原則[12],綜合考慮蕪湖市實際情況及參照已有研究結果[13,14],選取的社會經濟效益有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地均城鎮三次產業從業人員人數、人均擁有道路面積、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總數、城市人口密度、單位土地面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單位土地面積固定資產投資、單位土地面積財政收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態環境效益有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森林覆蓋率、造林總面積、園林綠地面積、單位土地面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單位土地面積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
2.2數據預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1-2016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安徽省統計年鑒》、《蕪湖市統計年鑒》.由于衡量指標涉及多個領域,其單位、性質不盡相同,不能直接進行比較評價,因此需要對其進行統一處理,運用公式(1)將各項指標數據采取標準化預處理:

(1)
其中,Yi表示第i個指標標準化處理后的值;xi為第i個指標的實際值.
2.3研究方法
(1)權重確定與效益水平計算
采用熵權法計算各項指標權重:
(2)

(3)

其中,Ej表示第j個指標的信息熵;Wi表示第i個指標的權重.

表1 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兩大效益水平計算公式為:
(4)
其中,U1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水平;U2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生態環境效益水平;Wij表示第i個指標的權重;Pij第i個指標標準化后的值;n為年份數.
(2)耦合協調度模型
參照已有研究[15],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為:
C=U1×U2/[(U1+U2)/2]2
(6)

(7)
式(7)中, ?=W1/(W1+W2),β=W2/(W1+W2).
其中,C表示耦合協調系數;D表示耦合協調度;T表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綜合水平;α、β分別表示兩大效益重要程度的權數;W1表示社會經濟效益各項指標權重之和;W2表示生態環境效益各項指標權重之和.
參照楊士弘[16]等研究成果,依據蕪湖市具體實際,建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分類體系及其判斷標準(表2).

表2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分類體系及其判斷標準
3 結果分析
3.1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演變規律
選取蕪湖市2000-2015年兩大效益共19項指標,經過各項計算得到其指標權重(表1),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蕪湖市200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水平U1與生態環境效益水平U2、耦合協調系數C、耦合協調發展度D,并根據表2中的分類體系及其判斷標準得出評價結果(表3).

圖1 2000-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及其耦合協調度演化曲線

年份U1U2CD類型20000.17470.06730.80310.3230輕度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10.15190.12730.99220.3749輕度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20.14530.13750.99920.3768輕度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30.14940.19540.98220.4070瀕臨失調衰退類社會經濟受損型20040.16730.12930.98360.3860輕度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50.19900.10510.90470.3803輕度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60.09900.12970.98200.3313輕度失調衰退類社會經濟受損型20070.14140.16710.99310.3887輕度失調衰退類社會經濟受損型20080.17590.14550.99100.4022瀕臨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090.22650.14760.95560.4301瀕臨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100.25070.13530.91060.4295瀕臨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110.34460.16350.87300.4846瀕臨失調衰退類生態環境受損型20120.37410.19850.90600.5221勉強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20130.38510.31670.99050.5943勉強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20140.40390.33490.99130.6098初級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20150.44050.27700.94810.5941勉強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
從社會經濟效益來看,2000-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總體增長趨勢明顯,其綜合水平從2000年的0.1747提高到2015年的0.4405,增加了0.2658,年均增長速度為6.36%.其中2000-200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呈較緩的“U”型特點:由2000年的0.1747緩慢下降到2002年的0.1453,隨后由2003年0.1494緩慢上升到2005年的0.1990;2006年則出現了一個較明顯的拐點,由2005年的0.1990下降到2006年的0.0990,結合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十項指標,發現數據差異較明顯的是城市人口密度由2005年的3164.78人/平方公里降到2006年的1448.89人/平方公里,社會經濟效益隨之下降;此后,2006-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水平增幅顯著.該總體增長態勢基本符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這不僅得益于國家改革發展的政策紅利,同時也是由于蕪湖市社會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驅動作用[13].
從生態環境效益來看,同期階段性波動較大,其綜合值介于0.0673-0.2770之間,反映了生態環境的相對脆弱性與敏感性.總體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3年,生態環境效益由0.0673增長到0.1954,其中2000年和2002年增長較快;第二階段2003-2007年,呈“V”型特點:2003-2005年,由0.1954下降到0.1051,2005-2007年,由0.1051上升到0.1671;第三階段2007-2012年,呈較緩“V”型特點:2007-2010年,由0.1671下降到0.1353,2010-2012年,由0.1353上升到0.1985;第四階段,2012到2014年快速上升,其中2012-2013一年間漲幅最快,達到59.55%;2014-2015年,由0.3349下降到0.2770.
從兩大效益總體來看,均呈波動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效益波動較大.2000-2007年,兩大效益水平此起彼伏,高低不一,自2008年起,前者高于后者.這可能是受到“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的影響,保持了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社會經濟效益快速增長,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任務較為艱巨.
3.2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協調度
依據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分類體系及其判斷標準(表2),得到2000-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協調度評價結果(表3).可以看出,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協調度分類明顯,總體上升,呈階段性特點:第一階段2000-2007年除2003年處于瀕臨失調衰退類型,其他年份處于輕度失調衰退類型,耦合協調度波動較明顯,且2000、2001、2002、2004、2005處于生態環境受損型,2003、2006、2007處于社會經濟受損型,說明世紀之初國民經濟和社會在發展中也存在許多突出問題.相比之下,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超前,而生態環境保護則相對滯后,需要進一步協調兩者的關系,加大改革和發展.其中2006年耦合協調度較前一年下降0.049,與社會經濟效益下降相符合,這可能是由于2006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經濟增長方式處于轉型關鍵期.第二階段2008-2011年處于瀕臨失調衰退類型,且耦合協調度穩定上升,這說明“十一五”規劃期間更加注重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效益的耦合協調發展,經濟結構優化,社會發展活力增強,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第三階段2012-2015年除2014年處于初級協調發展類型,其他年份處于勉強協調發展類型,且后三年耦合協調度差別不明顯.自2007年之后,生態環境效益都低于社會經濟效益,且在2007-2011年兩者差距加大,隨后稍有緩和.
4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以蕪湖市為例,基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視角,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蕪湖市200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2000-2015年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效益耦合協調度一方面呈現總體上升態勢,另一方面仍是由失調衰退類向過度類以及協調發展類的一個漸變過程,耦合協調度總體不高.2000-2007年除2003年處于瀕臨失調衰退類型,其他年份處于輕度失調衰退類型,2008-2011年處于瀕臨失調衰退類型,2012-2015年除2014年處于初級協調發展類型,其他年份處于勉強協調發展類型.為了促進蕪湖市城市土地合理利用,要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循環經濟的創新[17].
(2)2000-2015年除2003、2006、2007處于社會經濟受損型,其他年份均是經濟發展相對超前,而環境保護則相對滯后,在經濟潛力得到釋放的同時,土地資源承載能力下降[13].蕪湖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演化進程表明蕪湖市社會經濟的發展以環境為代價的趨勢依然存在,經濟與環境新的博弈和矛盾激化趨勢已經呈現[14].
(3)蕪湖市城市土地利用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兩大效益耦合協調發展波動性強.未來幾年蕪湖市處于城市轉型關鍵期,區域可持續發展面臨更大挑戰.今后蕪湖市應正確應對建設與生態的齊頭并進,協調城市土地利用,加快發展新區,打造新的經濟中心和就業中心,提高蕪湖市整體經濟實力和政府財力,改善人們生活條件,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
[1]龍冬冬,黃善林,徐文越,等.黑龍江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時空差異分析[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11,(6):45-47,53,56.
[2]陳興雷,李淑杰,郭忠興.吉林省延邊朝鮮自治州土地利用與生態環境協調度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09,(7):66-70.
[3]Costanza R,Arge R,Groot R,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6):253-260.
[4]張巨東,張鳳榮.區域土地資源持續利用評價研究[J].國土資源,2004,(4):31-34.
[5]張富剛,郝晉珉,李旭霖.縣域土地利用協調發展度評價:以河北省曲周縣為例[J].水土保持通報,2005,(2):63-68.
[6]梁紅梅,劉衛東,劉會平,等.深圳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耦合關系研究[J].地理科學,2008,(5):636-641.
[7]曹堪宏,朱宏偉.基于耦合關系的土地利用效益評價:以廣州和深圳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0,(6):58-67.
[8]王雨晴,宋戈.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評價與案例研究[J].地理科學,2006,(6):743-748.
[9]羅橋順,黨紅,張智光.哈密地區生態經濟系統耦合度變化及原因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0,(3):162-165.
[10]趙曉露,高敏華,高軍.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關系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1,(1):91-95.
[11]蕪湖人民政府.經濟發展[EB/OL].http://www.wuhu.gov.cn/content/channel/544f4d5e0a86c15431845afd/,2016-08-16.
[12]林勇剛.城市土地利用社會效益評價指標體系探討研究[A].中國土地學會,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重點實驗室.2008年中國土地學會學術年會論文集[C].2008:6.
[13]張光宏,馬艷.城郊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動態耦合關系——以武漢市遠城區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4,(11):14-20.
[14]熊征,談兵,宋成舜,等.城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耦合分析——以武漢市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5,(2):278-283.
[15]陳玨,雷國平.大慶市土地利用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J].水土保持研究,2011,(3):116-120.
[16]楊士弘.城市生態環境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114-119.
[17]王偉娜,宋戈,孫麗娜.哈爾濱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關系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2,(2):116-120.
EvaluationofUrbanLandUseBenefitsinWuhuBasedontheCouplingAnalysisofSocio-economicandEco-environmentalBenefits
HE Ruhai,LI Xin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China)
Based o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y environment, the coupling benefit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of Wuhu from 2000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land use social economy benefits and ecology environment benefits in Wuhu from 2000 to 2015 is increasing, but the degree is not high. (2)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advanc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lagging behind, and the socioeconomic sub-system has shown a coercive effe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bsystem. (3)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enefits has strong volatility,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in Wuhu. Wuhu should t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and treat the co-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ecology correctly in the fu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ircular economy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social economy.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social economy; ecology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Wuhu city
F830.9
A
1008-4681(2017)05-0090-05
2017-08-29
國土資源部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項目(批準號:201111010);安徽省國土廳科技項目(批準號:2015-k-15).
何如海(1969— ),男,安徽合肥人,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與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
(責任編校: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