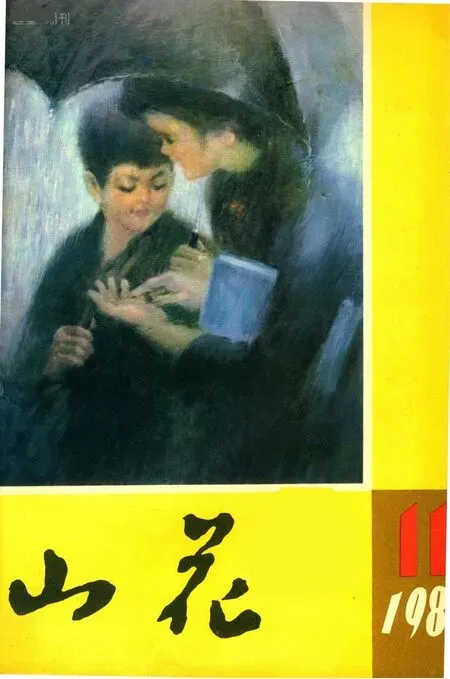水面以下
周海亮
發(fā)現(xiàn)小涓的時候,她睜著眼,紅著唇,頭發(fā)如水草般飄搖。淡藍的河水讓她的眼睛更加明亮,她盯住我,寒氣逼人。她懸浮在河水深處,陽光扎下來,她赤祼的身體散發(fā)出玉米般的金黃光澤。她隨著我激起的波浪翻一個身,尖挺的雙乳和平坦的小腹漾起陣陣水波。我脫下衣服將她包裹,如同包起一段潔白的藕根。我撫摸她,親吻她,擁她在懷,浮出水面。熱浪滾滾中,她像冰一般冷,羽毛一樣輕。
她早已死去。死去的她,澄澈潔凈。她的身體深處散發(fā)出薄荷般的清爽清香,我懷疑她就是一株剛剛死去的女人形狀的薄荷。我讓她仰躺岸邊,陽光傾瀉下來,她的眼睛緩緩閉上。我甚至聽見睫毛折斷的脆小之音,我貼緊她的臉,一條水蛭正奮力鉆進她的眉心。
我背小涓回村,兩個男人已經(jīng)候在村口。他們是下莊的村勇,要帶小涓回去。他們說夏里長知我找到失蹤的小涓,他會以十只羊做為對我的報答。
可是小涓已經(jīng)死了。我說。
所以要帶她回去。村勇甲說,帶她回去,才能安葬。
我盯住剛剛趕來的尚里長,我想知道他的看法。尚里長說,十只羊,不少。他低著頭,既不看我,也不看兩個村勇。他高我們一頭,然在我們面前,他明顯矮去半截。
下莊在河的下游,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據(jù)說隨便從陳年的掃帚上扯下一枝,插進土里,翌日就能長出一棵茂盛的毛竹。這些話是下莊人說的,即使是大話,他們也有資格。下莊共有三千多戶人家,這讓它更像一個城邑而非一個村莊,也讓下莊的里長更像一個國君而非一村之長。據(jù)說夏里長就像一只猿猴,長臂長腿,身材奇瘦,皮膚黝黑,卻紅著臉膛。據(jù)說沒事時他喜歡解下褂子,尋找藏在角落里的虱子,用指甲“啪啦啪啦”地掐。據(jù)說他雖守著一條水草肥美的大河,卻從不洗澡。也許他是泥土捏造而成,沾上水,就會變軟,泡癱,散開,胳膊啊腿啊,丟卸得到處都是。
相比下莊的熱鬧繁華,上莊乃真正的窮鄉(xiāng)僻野。這里只有三十多戶人家,交通不便,土地貧瘠。栽下一棵毛竹,不管如何用心,幾天以后,必成一把掃帚。好在有這條河。雖是上游,河水也很深,河面也很寬,灌溉不成問題。事實上除了我,灌溉是上莊人對這條大河的唯一理解和利用。只有我可以深潛河底,將藏在石縫間的蟹、埋在沙土里的蚌和游動在水草間的鰻輕易捕獲。我將它們拿到下莊的集市上,換回酒、煙草、農(nóng)具、牛羊肉、銀飾……河底是一處神秘并且詭異的所在,我遇到過碗大的田螺,鍋大的河蚌,磨盤大的甲魚,碾盤粗的水蛇……這些不足為奇。我還在河底見到過石像、陶器、巨鼎、古幣……我將它們打撈干凈,第二天,同一片水域,我又見到銅像、瓷器、盾牌、鎖鏈……如此反復。我懷疑當我扎進水里,水面以上的世間便不存在了。水面以下的世界在那一刻扭曲,進入到另外的空間和時間,或者秦,或者漢,或者皇宮,或者鄉(xiāng)野,或者戰(zhàn)場,或者墳塋……更或者,水面以下的世界才真實可信,而我一直生活在另外的扭曲的水面以上的空間和時間。不管如何,我從不打這些東西的主意,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將它們重新丟進河底,于是,從此以后,我再也尋不見它們,卻又有新的東西出現(xiàn)。每次它們都那般相似卻又那般不同,石像、銅像、陶器、瓷器、盾牌、骷髏、鐵甲、口紅……河底的世界,寂寞豐饒,令我癡迷。
在河底,我會懷疑自己飛了起來。巨大的浮力讓我生出翅膀,我在河底翻騰,翱翔,盤旋,直插云霄或者俯沖而下。很多時候我認為,不必將世界顛倒過來,河底就是天空。
我從未潛入過下游的水底,那里屬于強大的下莊。下莊的治安隊每天沿河巡游,見到不守規(guī)矩的人,便會大聲喝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那個不守規(guī)矩的人或被野獸攻擊而死,或被河水淹死,或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也曾有人報官,第二天,這個人溺死在河灘的馬蹄印里。蹄印里就那么一點點水,少到即使跌倒也淹不過他的鼻子,然他還是被溺死。他的身體里至少鉆進去三百條水蛭,水蛭吸光了他的鮮血和肌肉,內(nèi)臟和骨髓,發(fā)現(xiàn)他時,他已成為一張迎風招展的皮囊。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都不敢說。下莊是神和魔鬼共居的地方,他們種植玫瑰和罌粟,歌頌鐘馗和閻王,他們繁衍生息,熱愛生活。他們將捕撈到的磨盤般大的甲魚剁去腦袋,看它的無頭之軀繞打場爬行數(shù)日,直到風干成真正的磨盤。
與下莊人相處,我們心驚膽戰(zhàn)。每年我們都要向他們承諾很多次:絕不會污染一滴河水,更不會越過河界。做為報答,他們允許下游飄來的東西可以歸了我們。下游會有東西飄到上游?有。肺魚。
確切說不是飄,而是游。肺魚有肺無鰓,可以像人類一樣呼吸。它們的眼睛長在腦袋前方,鼻骨很高,有整齊的牙齒和小巧的下巴,有類似耳朵的突起。雖然可以上岸,它們卻不愿離開水,這讓它們的一生都在水里度過。肺魚在上游孵化,在下游成長,在大海里度過它的成年期,然后洄游至上游產(chǎn)卵,度過生命里的最后幾天。初春是它們產(chǎn)卵的季節(jié),初春也是下莊人的節(jié)日。為了肺魚,他們傾巢而出,布下天羅地網(wǎng)。他們甚至用上炸彈,“轟”一聲響,水面一片類人的腦袋。那些天,下莊的土地被肺魚的鮮血染紅,下莊的上空被魚腥氣味占領,久久不散,令人作嘔。僥幸逃脫的肺魚,游到上莊河界,產(chǎn)卵,死去,卵孵化,長大,越長越大,游經(jīng)下莊,游向大海。上莊的我們從不打肺魚的主意,我們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直至它們將卵產(chǎn)盡,浮上水面,掙扎,喘息,顫抖著青白色的干癟的肚皮,用沒有眼皮的眼睛瞪著我們。那是令人憂傷和恐懼的時刻,每到這時,尚里長就會帶領幾位老人在河灘上燃起香火,唱起哀歌。那些天我吃不下任何東西。我總是懷疑肺魚是水生生物在進化成人類的旅途中迷了路——它們僅僅進化出兩肺和腦袋的輪廓,卻沒有進化掉鱗片和尾鰭。或者它們干脆就是另一種弱小的低級的人類,它們溫順并且膽小,唯繁殖能力驚人。
除了肺魚,下游再不會飄來任何東西。所以事實是,我們是下莊人的奴隸,甚至,我們是下莊人的肺魚。
隨兩個村勇去往下莊之前,我回了趟家。我告訴我媽我要去一趟下莊,我會趕回十只羊。我推上地拱車出門,我媽追到門口,“嘰哩哇啦”地叫。我分不清她是在哭還是在笑,自她瘋掉以后,就再沒有人聽懂她的話,看懂她的喜怒。去年秋天我從河底撈出一個漂亮的骷髏,我把它帶回家,藏進陶罐,卻還是被我媽發(fā)現(xiàn)。讓她瘋掉的不是骷髏,而是從骷髏里爬出的一條肺魚。肺魚生出尾鰭狀的兩腳,垂頭駝背,就像一位老者蹣跚著穿過院子,我媽就瘋了。她是被嚇瘋的。之前她見過肺魚,卻從未見過會走路的肺魚。
我爹說,你該再要一頭牛。他總是貓在院角搓草繩,即使那條貌似老者的肺魚從他面前走過,他也沒有停下手里的活。
我將小涓抱上地拱車,隨兩個村勇上路。隨著顛簸,小涓變換出不同的姿勢,一只胳膊輕輕擺,一條腿輕輕蕩,如同活了過來。好幾次我停下車子,撫摸她光滑赤祼的臂膀,幻想她能活過來,可是她依然冰冷并且愈來冰冷。兩個村勇不斷催我快走快走,他們說天這么熱,別讓小涓的尸臭壞了下莊人的胃口。
我們坐在樹林的邊緣休息。從這里可以望見下莊高高的土墻,望見土墻上手持火銃和土墻外手持梭鏢的巡勇。他們是下莊的保護者,他們驍勇善戰(zhàn),以一當十。十只羊已經(jīng)候在路口,現(xiàn)在我只需放下小涓,將羊趕回上莊,這件事就結束了。
可是我不想讓這件事到此結束。
我對村勇甲說,我爹說應該再加一頭牛。甲說,十只羊不少了。我起身,推車,轉身,邁開腳步。乙說,你會后悔。我繼續(xù)走。甲撲過來,我飛起一腳,將他踹倒;乙撲過來,我閃開,他摔倒在地。我在下莊有過短暫的村勇生涯,我驍勇善戰(zhàn),以一當百。
我推小涓上路。我說,對不起啦,兩位兄弟。
一年里,除了最冷的那段時間,每天我都要潛入河底。很多時候我認為我也是肺魚的同類,只不過肺魚是長出肺的魚類,而我是長出鰓的人類。長時間離開水,我必死無疑。
做村勇的那段時間,恰是最適潛水的夏天。夏里長給我開出很高的價錢,那些錢足夠我買下整個上莊。然讓我動心的絕非是那筆錢,而是下莊遼闊的河底。我對那片河底向往已久,我渴望能夠得到夏里長的允許。
我在下莊呆滿一個月,然后離開。我沒有從下莊帶走一個銅板,我連夏里長的面都沒有見到。下莊對那片河域嚴防死守,即使一只鳥從天空飛過,村勇們也會如臨大敵,嚴陣以待。
清晨我回到上莊。我在院角搭了張床,讓小涓躺在上面。我守著小涓,看我爹一邊抽草煙一邊搓草繩。我媽在灶間做飯,她把風箱抽出哮喘般的聲音。灶火將她的臉映照出半紫半綠的調(diào)子,她一邊往灶坑里填柴,一邊“嗚嚕哇啦”地叫。
我爹說,你該把小涓送回去。
我說,我多要了一頭牛。
我爹說,咱不要牛了。
我爹扔下草繩,起身去關門。門將掩上的一刻,村勇乙從門縫擠進來。他沖我爹作揖,又沖我抱拳,說,十只羊,兩頭牛,給你牽過來了。
我爹說,怎么就你一人?
乙說,那兄弟死了。
我說,我不過絆他一跤。
乙說,可是他死了。
他是吃東西噎死的。乙說,夏里長賞他一條羊腿,他吃得太快,就噎死了。他死在夏里長面前。他吞下整根羊腿骨。他的眼珠子都憋出來了。眼珠子掛在臉上,一邊一個,不掉,琉璃球似的蕩啊蕩啊……
乙說的是他死去的方式,而非死因。他的死因并不難猜出。我爹不寒而栗。
十只羊和兩頭牛浩浩蕩蕩闖進院落,院落熱鬧起來。小涓依然靜靜地躺著,眼睛緊閉,嘴唇蠟一般白。卻有波濤涌來,院落變成靜靜的河底,砂土漫上小涓的臉和乳房,螺螄兇猛。
一只羊抖動著粉色的嘴唇,親吻了小涓的額頭。我揮手將羊趕走,對乙說,我不能把小涓給你。
我媽發(fā)出一聲驚悚的慘叫。她“嗚啦嗚啊”地跑過來,用又尖又長的指甲撓我的臉。我閃開她,對乙說,小涓是飄過來的。夏里長說過,下游飄過來的東西,便可歸了我們。
乙說,你知道這樣做的后果。
我說,你也會吃東西噎死。
或許淹死。
或許渴死。
或許被狼咬死。
或許被黃蜂蜇死。
求你。
滾吧。
乙離開,慢得就像一只蝸牛。從現(xiàn)在起,他的生命已經(jīng)不再屬于自己。那是他的事情,與我無關。現(xiàn)在我要做的,就是繞床搭起一頂帳篷,以免夜里的露水將小涓打濕。我長久地盯著小涓,我的舉動讓村人駭懼。讓他們害怕的并非我愛上一具尸體,而是我也將很快變成尸體,也許還有他們。
夜里我守著小涓,就像守著暖烘烘的新娘。月光似乎讓小涓生出銀光閃閃的鱗片,很多個瞬間,我懷疑小涓會坐起來,捊捊頭發(fā),伸展手臂,游向天空。她在如水的月光里遨游,飛鳥變成群魚,星星變成砂礫,參天古樹變成柔軟的水草,所有的高山,都變成河底。小涓并不看我,但她知道我在追隨她,守護她。小涓不停地游,不停地游,她累了,閉目休息。水面近在咫尺,她卻不敢浮上來。她在水面以下掙扎,她的臉變紅,變紫紅,變紫,變紫黑,變黑……眼珠凸起,舌頭伸長……小涓沉入河底,如一塊沉重的鐵。然后,田螺和河蚌將她侵犯,波濤涌進我的內(nèi)心。
下莊人在第二天清晨再一次趕來,這一次,換成了村勇丙。丙說乙在昨夜遭到一頭牛的攻擊,腦袋被頂出三個洞,內(nèi)臟被頂?shù)孟€。丙說直到現(xiàn)在乙也沒有死去,但早已無人將他當成活人,包括他自己。丙說乙還在嚎叫和呻吟,這讓他的生命努力抻長最后一點。丙笑笑,說,我來接小涓回去。
我說,不可能。
丙說,那么,兩天以內(nèi),上莊必滅。
丙并非要接小涓回去,他是來傳達夏里長的旨意。很久以前下莊曾與我們有過小的過節(jié),那次夏里長就有徹底滅掉上莊的打算。那一次尚里長和眾老人說盡好話,并將村子的所有財富以及最美麗的姑娘獻給夏里長,才僥幸保全了村子。后來我們得知保住村子的并非是那些財富和那個姑娘,而是夏里長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病——夏里長認為那場病必與他滅掉上莊的打算有關,恐懼之中,只得放棄。
尚里長得知消息,大驚失色。他跪下求我,說我中了夏里長的圈套。他說夏里長根本不想要回小涓,他只想找個借口滅掉我們的村子。我說他真想滅掉我們的話,就算我們躲過這次,也躲不過下次。尚里長說躲過一次是一次。我說我早受夠下莊的欺負,是時候反抗了。尚里長說這不是反抗,這是自尋死路。他看一眼小涓,他說就算她是仙女,我也不能以全村人的性命做賭注,何況她只是一具毫無用處并且將很快腐爛到惡心的尸體。我說她不是尸體,她是小涓。尚里長說現(xiàn)在我完全可以把你綁起來,連同小涓一起送到下莊。我說,我們還有機會。
我們還有機會。距此五十余里有座山,山里盤踞著匪。匪頭外號閻王,殺人越貨,壞事做盡。一次閻王盯上從附近經(jīng)過的一支部隊,他率眾匪與部隊激戰(zhàn)一天一夜,部隊死傷過半,匪幾乎全軍覆沒。閻王逃至上莊,扮成村人數(shù)日,才保得一條性命。因上莊有恩于他,閻王當即拍下胸脯,說以后上莊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但其實,我們救下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懾于淫威,懼他日后報復。
雖然閻王元氣大傷,但他依然是匪。他有能夠射出連發(fā)的步槍,有雖然上山不久卻訓練有素的匪兵,有兇殘的本性和令人聞之色變的名字。尚里長斟酌再三,決定試試。
我啟程時,村里百姓開始挖掘戰(zhàn)壕。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卻必須在三天之內(nèi)完成。戰(zhàn)壕會將我們的村子圍起,曲折迂回,就像一個壯年人流出的腸子。村人和我從閻王那里搬來的匪們將會守住戰(zhàn)壕,端著槍,將來犯的下莊人一個個射殺。這必是一場慘烈的戰(zhàn)斗,戰(zhàn)斗也許會維持一天,一月,甚至半年,一年。但我們有機會。我們甚至有希望將下莊消滅,讓他們從此歸順了我們。尚里長就是這樣被說服的。盡管他在下莊人面前溫順如一條狗,但我知道,他早想把夏里長踩在腳下,把下莊歸為己有。
他決定拼死一搏。
閻王見到我,如同我見到真正的閻王。他說假如幾年前的那支部隊是一桿槍,下莊就是一座炮;假如那支部隊是一條狗,下莊就是一匹狼。他說對下莊,對夏里長,他躲都躲不及,哪里還敢去惹?我說你可以不必出動兄弟,但你可以借給我?guī)讞U槍,就當履行你曾經(jīng)的諾言。閻王說現(xiàn)在我完全可以殺掉你,拿你的尸體去下莊領賞,你還不明白?我說抵抗總還有機會。閻王說,趁我沒有動手之前,你滾得越遠越好。
我空手而歸,卻在村頭遇到兵勇丙。他抱著三桿步槍,他將槍丟到我和尚里長面前。夏里長送你們的,丙笑著說,他說你不必去求閻王,他完全可以滿足你。
尚里長面如土色,牙齒發(fā)出砂礫磨劃的恐怖之音。其時戰(zhàn)壕已近完成,幾支鳥銃、梭鏢和一個巨大的弩炮已經(jīng)抵達指定位置。我爹貓腰站在一個缺口處,手持弩弓,正朝一個虛構的目標瞄準。我爹似乎對即將到來的大戰(zhàn)非常亢奮,他清楚拼死一爭還有保我性命的機會,否則這機會幾乎等于零。我媽一邊“哇嗚哇啦”地自言自語,一邊玩命揮動鐵鍬。石塊在她周圍上下紛飛,灰塵將她的眼睛染成灰色——將戰(zhàn)壕挖深一點再挖深一點,成為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是戰(zhàn)壕注定派不上用場。也許明天,它們就將被匆匆掩埋,或者被栽滿了樹。樹們將很快變得奄奄一息,成為圍繞村莊的掃帚林。夜里,掃帚林發(fā)出啾鳴之聲,村莊死一般沉寂。那時村子里將不會再有一個活人,村子成為墳塋,只剩下鬼魂們游蕩在村子的半空——下莊送來的三條步槍已經(jīng)出離藐視和挑釁,事實上,他們早把我們當成毫無抵抗之力的死人。
我回到院子,小涓靜靜地躺著,臉上掛著笑。那笑是我為她調(diào)整出來的,去找閻王之前,我用手輕撫她的唇,讓她微笑著等我。她微笑著等我,就像之前,我們很多次偷情的日子。
在下莊,我是最驍勇善戰(zhàn)的村勇。我渴望能夠留下來,背叛我的故鄉(xiāng),成為下莊一員。為了展示我的忠誠和殘暴,我掐死過一個報官的路人,然后將他投到河灘,讓他的鼻孔淹沒在淺淺的馬蹄印中。如此死法令夏里長大加贊嘆,他決定賞我三十大洋,卻拒絕見我。他拒絕見我,我就得不到小涓——我指的是明媒正娶,以及白頭偕老。
去下莊的第三天,我與小涓開始偷情。我們都相信迅速并且熱烈的愛情,三天對我們來說,已經(jīng)太過煎熬。盡管小涓從不多看我一眼,但我知道她在誘我。她誘我因為愛我,她愛我因為我值得她愛。她走在我左邊,她的右肩長出眼睛;她走在我右邊,她的左肩長出眼睛;她走在我前邊,她的后背長出眼睛;她走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到處都是她的眼睛,眼睛,眼睛。她的眼睛可能是一棵樹,一桿梭鏢,一粒砂,一縷塵煙……她愛上我,如一條絕望的肺魚愛上另一條絕望的肺魚。
最初我們在廢棄的倉庫里偷情。她走進去,片刻后我走進去,世界只剩下我們。倉庫里光線暗淡,唯小涓的身子白得耀眼。我們不必交談,不必眉目傳情,我只需上前,剝光她,攬緊她,抱起她,將她擎上一架古老的水車,抬起她的兩腿,伴著“吱吱呀呀”的木聲、風聲和水聲,我進入她無限的深處。她是一條河。她是一片岑寂并且嘈雜的河底。有她,我不再向往下莊的河底,不再向往世間任何河流的河底。與她同在,我不再羨慕任何人。
后來我們在糧倉里偷情。她仰躺在松散的玉米之上,我在她潔白柔軟的身體上灑滿金黃的玉米。我們翻滾,糾纏,釋放快樂又壓抑快樂,汗水將玉米沾上我們的身體,硌得我們疼痛難忍,卻不舍分開。后來玉米成為波浪,后來她成為波浪。后來糧倉成為河底,我見到河蚌,水蛇,瓷器,陶俑,慢慢爬行的甲魚和肺魚……我們將對方深埋進玉米之中,屏緊呼吸,貪婪并且吝嗇地撫摸對方的身體。糧倉外面,扛著長銃的村勇們在巡邏。這里絕非偷情的好場所,我們隨時有可能被擒。
再后來我們在房頂上偷情,在樹冠里偷情,在地窨或者山洞里偷情,我們小心翼翼,我們忘乎所以。我們也曾想到潛入到水面以下偷情,非常想,但當我說出這樣的想法,小涓的臉霎時變得煞白。她說,我爹會殺了你。
她說的沒錯。那是下莊的河域。那片河域絕不允許外人玷污。我注定成不了下莊人,那片河底就注定永遠不可能屬于我。小涓絕不會嫁給一個像我這樣差勁的上莊人,小涓說,這是家規(guī)。
你可以找你爹說。
他會殺死你,然后殺死我。小涓說,他能夠猜到所有。
只要我在下莊久留,我與小涓的事情必會敗露。我不想死,更不想小涓死,我只能選擇離開。與小涓最后一次偷情,我們回到第一次的廢棄倉庫,我把她頂?shù)綋u搖欲墜的木門上,我聽到她的髖骨發(fā)出樹枝斷裂的“啪啪”之聲。我從未如此深入小涓,似乎我潛入河底,被一只柔軟滑膩的河蚌緊緊吸附。小涓說咱倆私奔吧。我說你沒有機會。小涓說或許有。我說沒有。小涓說我有辦法。我說,你沒有。
我知道小涓的辦法。我不想讓她嘗試。
小涓絕不會有機會。小涓十八歲,十八年里,下莊是她的世界。當夏里長老去或者死去,她或許會成為下莊的新首領,或許不會。不管會與不會,她都不得離開下莊。夏里長不許她離開半步,否則,必死。
——小涓的辦法是,她將在下莊的河域下水,從水面以下游至上莊。我們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上莊會合,逃向遠方。
這不可能。下莊距上莊如此遙遠,即使一條肺魚,也需要時常浮出水面呼吸。但小涓決定去做,義無反顧。從我離開那天起,她就開始練習。她從下莊潛入水底,再從下莊浮出水面,無人知曉她在水面以下游行多遠迂回多遠。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她在白費力氣。令我驚異的是,一年以后,村勇甲偷偷給我捎來口信,說,小涓已經(jīng)接近成功。村勇甲是我的兄弟,假如無他暗中相助,我與小涓那么多次的偷情早被發(fā)現(xiàn),我在離開下莊以后,也根本不可能得知有關小涓的任何消息。
所以,他的死絕非因為他沒能帶回死去的小涓,而是他已敗露。夏里長遲早會知曉一切,甲的悲劇在于,沒能趕在夏里長對他下手之前,遠離下莊。
我也沒有。雖然我人在上莊,但夏里長若想取我性命,我絕沒有逃掉的可能。
我守在小涓面前,看她凝固的笑容在黃昏里愈發(fā)暗淡。然后夜晚來臨,尚里長、我爹媽、村勇丙和幾個村人來到院落。尚里長說我們做得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向閻王搬救兵,這將夏里長激怒。假如之前上莊還有一點點機會,這機會已被我們徹底葬送。
我可以帶小涓逃走。我對尚里長說。
夏里長會滅掉上莊。
或許可以報官……
如果你不想連累我們,就把小涓送回下莊。還有十只羊和兩頭牛。再帶上幾輛馬車,拉上糧食、酒、布匹和銀元……
他們會殺死我。
至少救下村子。
夏里長也不會見我。
這肯定。
可是我有話要對夏里長說。至少在我死去以前,有話要對他說。
這不可能。
那我只好選擇逃走。
不顧全村人的死活?
不顧。
包括爹媽?
包括。
帶上小涓?
帶上。
尚里長陪我坐下。他“咕嚕咕嚕”地抽著水煙,那聲音只屬于水底深處。少頃,他起身,問我,難道你不準備一下?我沖進屋子,提起早已備好的錢袋,出來,尋找院角的地拱車。從此我將與小涓浪跡天涯,直到小涓變成一具干尸,甚至枯骨。
我彎腰,試圖抱起小涓。尚里長突然在我身邊閃現(xiàn),手里多出一根木棒。木棒重重落下,我的世界變得模糊遲鈍。我倒下,我看見我媽瘋狂地撲向尚里長,尖銳的指甲撓著他的臉,又閃出利齒,切中他的脖子。我聽到尚里長發(fā)出殺豬般的慘叫,我看見他不停地沖村勇丙招手。我看到我爹飛奔上前,一腳將我媽踹開很遠。我看到眾村人拖來堆在院角的繩子,將我綁得如同一個結實的粽子。
尚里長是我的大伯,他與我爹是親兄弟。村人與我,他們選擇了村人。
他們大義滅親,我痛苦,我欣慰。
我與小涓被押解上路。身后,跟隨著浩浩蕩蕩的牛與羊,村勇與姑娘,馬車與村人。似乎村人是要去下莊朝拜,盡管他們不可能見到夏里長。但我可以。事情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了轉機,當村勇丙如實向夏里長稟報,我竟得到允許。
這正是我想要的。我必定會成功。上莊必定會成功。
一切都在艱難地按計劃進行。
去下莊做一名村勇是計劃的第一步。這計劃走向兩種可能:假如我能見到夏里長,我將成為刺秦的荊軻;假如我不能如愿見他,小涓將成為這個計劃里的重要一環(huán)。我將愛上她或者假裝愛上她,我將勾引她或者被她勾引,不管情況如何發(fā)展,計劃都不能被打亂——哪怕我真的愛上她。
計劃由尚里長、我爹、我媽和我四個人制訂,我們充分考慮到每一種可能,每一個方向。我與小涓在倉庫里偷情,在糧倉里偷情,在房頂上、樹冠里、山洞里、樹林里偷情,在任何地方偷情,我沒有愛上她。這很殘忍,然我說服不了自己。計劃中夏里長是我的獵物,小涓不過是引出獵物的誘餌。我實在無法愛上一個誘餌,哪怕她再漂亮,再清冷,再滑膩,再芬芳。我離開下莊,計劃拐一個彎,回到起始——我將在上莊的水底等待小涓,等待活著的小涓,或者死去的小涓。無論活著的小涓或者死去的小涓,尚里長都有辦法把我送到夏里長面前,盡管這萬般艱難萬般曲折,就像現(xiàn)在。然而,事實上,從離開下莊的那一刻,我就不再相信這個計劃會得逞。我想上莊注定還會被下莊欺負,那些可憐的人形肺魚還會死在排卵的途中,直至這個世界徹底不在。
但當我在水底見到死去的小涓,我想我真的愛上了她。愛情在那一刻真正降臨,它來得太遲,讓我無法挽救,更無法挽留。后來我想我絕非那一刻才愛上她,我早就愛上她——我早就愛上她,所以讓計劃繼續(xù)——我期待她能潛水過來,與我一起私奔。我把小涓抱在懷里,親吻她,撫摸她,求她活過來,可是她死得徹底。她無限地接近成功,可是她還是死在成功的途中。是誰將小涓殺死?尚里長?我爹媽?夏里長?我?小涓自己?村勇甲?突然之間,似乎這世上的所有人,都逃脫不了干系。
復仇的種子就是在那一刻種下的,然后,片刻之間,生根發(fā)芽,越長越大。村勇甲必將被夏里長殺死,夏里長必將被我殺死,閻王必會帶著他的匪兵按時殺到……這既是尚里長想要的結果,也是我想要的結果。不同的是,尚里長要的是上莊的未來,而我僅僅為了復仇。我還想到了另外的可能:閻王兵敗下莊,憤怒的下莊人將上莊殺得一個不留,包括雞舍里的雞崽和洞里的老鼠,包括尚里長和我爹媽。我已管不了太多。
我爹和尚里長將我捆綁得結結實實。繩子一圈一圈,排得密密匝匝,我僅能從“繩桶”里露出兩腿和腦袋。這種綁法無疑會讓所有人失去警惕,包括夏里長。但其實,那些繩子一掙就斷。我爹將大半輩子的時間和精力用來搓草繩用來研究草繩,卻并非為繩子更結實,而是更易斷。——在我出生之前,尚里長與我爹就開始了這個計劃。
密不透風的繩子掩住了我綁在后背的雙手。我的手里,藏著一把很小的象牙手槍。手槍是閻王送給我的,可裝子彈三發(fā),精準度極高。從屋里出來之前,我曾將手槍檢查一遍,確保萬無一失。然后,我將手指摳進扳機,尚里長和我爹將我捆綁。那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綁法,看起來無比結實,我卻能夠在瞬間將其掙脫,抬槍,瞄準,擊發(fā),擊發(fā),再擊發(fā),三顆子彈足夠將夏里長干凈利落地射殺。
我絕不會失手。夏里長在劫難逃。
村人在村口即被攔下。尚里長和我爹倒是進到村子,卻被擋在門口,每人發(fā)一只烤羊腿,啃得心驚膽戰(zhàn)。我穿過一道又一道木門石門鐵門,兩個彪形大漢始終與我如影相隨。終于我進到最隱蔽的內(nèi)室,夏里長在這里恭候我大駕光臨。光線昏暗的屋子被一道厚厚的布簾隔成兩半,我聽到布簾后面?zhèn)鱽怼皣W嘩”的水聲。
那不可能是水聲。夏里長怕水,拒絕水。沾水他就會變軟,變癱,散開,沒了人形,再也抬掇不起來。夏里長與水無關,連他的血管里,都流淌著土黃色的沙子。
我聽到一個干澀的聲音。那聲音應該屬于沙漠,屬于沙漠里的砂礫,屬于砂礫打磨砂礫,屬于砂礫迸裂,屬于迸裂的砂礫燃起赤紅的火焰。聲音里毫無一點點水汽,那絕不可能屬于人類。
那聲音說,讓我看看他。
有人彎腰,抬手,由下至上,掀動布簾。一縷陽光恰在這時斜照進來,布簾后面的人影,若隱若現(xiàn)。
我的身體在剎那間崩緊。我掙脫草繩,舉起手槍,動作一氣呵成。我扣動扳機,瞄準那個模糊的晃動的影子。我見到三顆暗紅色的子彈排成整齊的一列,呼嘯著奔向那個怪異的影子。我見到布簾被完全掀開,我見到子彈繼續(xù)沖刺,沖刺。我見到夏里長。之前我無數(shù)次想過夏里長的恐怖模樣,然見到他,之前那些想像,全都可以用“美好”來形容了。
夏里長是人。夏里長不像人。他半躺在浴缸,脖子以下,全都浸泡在水里。他的皮膚比嬰兒還要嬌嫩百倍。他半透明,蠕動的內(nèi)臟、淡藍色的血管和白色的骨骼隱約可見。他柔軟如水母般不停扭動的身體那樣之小,遠不及一個初生的嬰兒。可是他的臉,遠比世界上最蒼老的老人還要蒼老,比最干燥的沙漠還要干燥。那張臉黑灰色、粗糙龜裂、溝壑縱橫、長滿霉斑。他的五官在臉上胡亂地堆積,不仔細看,很難分出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哪是嘴巴。就算分得出,那五官也不似五官,它們更像幾個窟窿或者劃痕。似乎連他的眼珠都是由泥土捏成,不僅毫無光澤,并且不見一點水色。他的模樣讓人惡心,也讓人憐憫。他讓我想起某種水生動物,又想起死去多年的腐朽的樹樁。甚至,他讓我想起肺魚,想起肺魚已經(jīng)進化成半個人類,想起肺魚在進化成人類的途中迷路,然后長成夏里長這般惡心并且可怖的模樣。或許夏里長真的是肺魚吧?他是進化得最快的最接近人類的肺魚。之所以他要殺光肺魚,正是想阻止這種偏離正軌的進化。也或許,他在人類進化成肺魚的途中迷路——誰敢肯定人類不會進化成肺魚呢?——他試圖殺光所有肺魚,正是為了保全人類。我盯緊滾燙的子彈奔向陽光,距他的額頭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那個剎那,我突然想收回已經(jīng)射出的子彈。我想饒恕他,就像饒恕一條可憐的肺魚。可是,晚了。排成一列的三顆子彈將陽光劈成兩半,距他的額頭近在咫尺。現(xiàn)在我很想這三顆子彈變成三顆毫無殺傷力的大棗。變成三顆大棗,只是驚嚇他,警告他,甚至取悅他,卻不能取他性命。不可思議的是,這樣想著,子彈們果真變成大棗。三顆大棗一樣的暗紅顏色,一樣的子彈形狀,在他的額頭上擊出一樣的極輕微的鈍響,“啪啪啪”掉落地上,彈起,再掉落,世間終變得寂靜無聲。我看到夏里長泡在浴缸里的小小身體發(fā)出一陣急迅的抽搐,然后,本來五官不清的腦袋突然清晰地顯出一張空洞的嘴巴。嘴巴“哈哈”大笑兩聲,說:“有意思!”
夏里長覺得有意思。他或許以為我在逗他開心。他這樣想是有道理的——世間絕無刺客試圖用三顆大棗結束一個人的性命。總之夏里長竟然慷慨地放我離開,在我身后,他將一缸水攪得混濁。
我回到上莊的河域。我將潛入水底,然后一路往下,潛向下莊。我絕不會浮出水面,一次也不會。不管我能否成功抵達,都抱了必死的信念。即使到達,我也會將自己活生生憋死在河底。我可以饒恕夏里長,卻不能饒恕自己。我將為小涓殉情,不久以后,我就能如愿見到她。
扎進河水之時,我聽到岸上有人大喊:“夏里長被大棗射死啦!”夏里長被大棗射死,這不正常,這很正常。他本就是一條魚,一顆大棗或許足可以將其射殺。還或許那根本就不是大棗,那只是三顆偽裝成大棗的子彈。還或許他因驚嚇或者興奮而死——因一顆大棗受到驚嚇,因一顆大棗興奮過度。既然世間的一切全都那般詭異,世間的一切詭異也都歸于正常。
我潛下去,潛下去,潛下去。我見到石像、陶器、古幣、盾牌……我見到小涓睜著眼,紅著唇,赤祼身體,頭發(fā)如水草般飄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