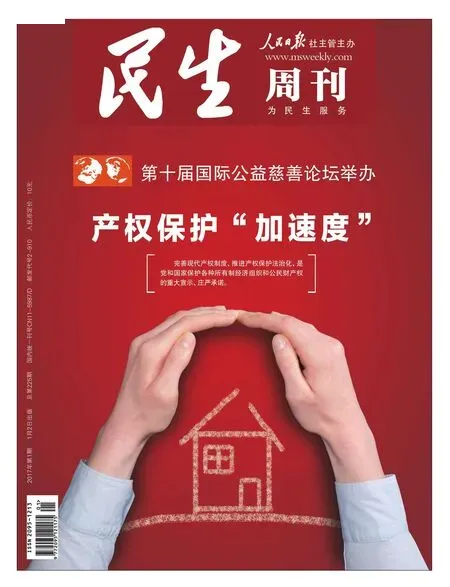北京垃圾分類何時落實到位?
□ 《民生周刊》記者
北京垃圾分類何時落實到位?
□ 《民生周刊》記者趙慧
推行垃圾分類多年,北京與許多城市一樣,基層實踐不斷涌現(xiàn),市民意識也大大提高,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tǒng)卻一直沒有建起來。
嘗試垃圾分類還不到兩年,退休教師張麗曼已經(jīng)可以做到自家生鮮垃圾不出門,她用垃圾做成的環(huán)保酵素擦洗地板、澆花甚至洗頭。家里的廢舊電池、廢舊燈管、過期藥品等有害垃圾,她也會收集起來投放到社區(qū)家庭危險廢棄物回收處。
張麗曼居住的金榜園小區(qū)并非北京垃圾分類試點小區(qū),居民分揀出來的有害物品只能在小區(qū)集中存放。過期藥品的下一個去處在哪里?廢舊電池如何送到工廠熔化分解?無處安頓且日漸壯大的廢棄物堆場,成為小區(qū)最頭痛的事。
作為生活垃圾產(chǎn)生量最大的城市,2015年北京制造了790.3萬噸生活垃圾,其中近四成焚燒處理,約三成生化處理及填埋,只有少量采用其他處理方式。
推行垃圾分類多年,北京與許多城市一樣,基層實踐不斷涌現(xiàn),市民意識大大提高,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tǒng)卻一直沒有建起來,城市垃圾分類始終“血脈不通”。
社區(qū)黏合劑
金榜園小區(qū)嘗試垃圾分類有相當?shù)呐既恍浴!拔飿I(yè)成本在增加,但物業(yè)費不能漲,物業(yè)公司只能減人,造成服務質(zhì)量下降,業(yè)主和物業(yè)的矛盾日益尖銳。”作為海淀和諧社區(qū)發(fā)展中心的生態(tài)學者,張麗曼一直研究社區(qū)治理,她告訴《民生周刊》記者,這是近年很多老舊小區(qū)出現(xiàn)的共同問題。
建成于2001年的金榜園小區(qū)就曾經(jīng)是個“問題社區(qū)”,業(yè)主與物業(yè)公司打了多年官司,業(yè)主拒繳物業(yè)費,物業(yè)公司無心管理小區(qū),雙方關系劍拔弩張。
為了緩解矛盾,也為了減少物業(yè)支出,金榜園小區(qū)開始倡導垃圾分類。首先做的是落葉堆肥。以往,小區(qū)落葉都是作為垃圾由環(huán)衛(wèi)工人運走,僅清運落葉的費用每年就要兩萬元。
如今,物業(yè)公司將落葉收集到一片空地,加入菜葉果皮等廚余垃圾制成的環(huán)保酵素,層層堆積,最終發(fā)酵成肥料。這些肥料不僅可以用于小區(qū)綠化,還會分發(fā)給養(yǎng)花種菜的居民。
目前,金榜園小區(qū)已經(jīng)可以做到可回收廢物不出社區(qū),小區(qū)垃圾量明顯減少,物業(yè)也節(jié)省了大筆垃圾清運費。但是,對于居民分揀出來的廢舊熒光燈、廢舊電池、廢舊小家電、過期藥品、過期化妝品等危險廢棄物,還只能存放在小區(qū)專設的家庭危險廢棄物回收處。
張麗曼介紹,通過不斷溝通,有些廢舊危險物品他們已經(jīng)可以送到專業(yè)的處理廠分解處理,但過期藥品還是無處運送,只能暫存在小區(qū)。
盡管金榜園小區(qū)的垃圾分類只實現(xiàn)了小區(qū)內(nèi)部循環(huán)利用,但已經(jīng)帶來了巨大改變:小區(qū)環(huán)境日益美化,居民與物業(yè)的矛盾大為緩解。
“我們就是希望找到一個共同點。推行垃圾分類后,業(yè)主看到社區(qū)環(huán)境美化,雙方的關系也不像以前那樣緊張了,物業(yè)費繳納比例從最低時的23%漲到了80%,下一步會倡導居民主動在家中做好垃圾分類。”張麗曼說。
臺灣綠色公民行動聯(lián)盟理事賴偉杰告訴《民生周刊》記者,據(jù)他觀察,開展垃圾分類就是讓社區(qū)居民共同做一件事情,可以拉近日益冷漠的人際關系,垃圾分類一定程度上會成為社區(qū)居民的黏合劑。
農(nóng)村同步進行
2016年12月3日,北京已進入隆冬,而在昌平興壽鎮(zhèn)的桃林村正在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千人凈村行”活動,來自全國各地的環(huán)保人士和志愿者來到這座京北小村莊,為農(nóng)村環(huán)境治理助力。
同時啟動的還有桃林村垃圾分類不落地工程。當日,在桃林村村干部的帶領下,參會者一同喊出“垃圾不落地、地球更美麗”的口號,隨后,志愿者們開始親手撿拾垃圾,為村民講解垃圾分類知識及環(huán)保酵素制作方法,村里也計劃拆除垃圾回收點。
事實上,桃林村的這一做法借鑒自相鄰的辛莊村。在辛莊村,垃圾分類在7位倡導者的帶領下早已開始,村莊環(huán)境大為改善。
相比城區(qū),“垃圾圍村”現(xiàn)象近年來尤為突出,且由于清運和末端處理設施嚴重不足,亂倒、亂埋、亂燒的垃圾對農(nóng)村土壤、水源、大氣造成嚴重危害。
針對很多地方“先城市、后農(nóng)村”的垃圾分類思路,北京零廢棄發(fā)起人毛達認為農(nóng)村地區(qū)垃圾分類應同步進行,“農(nóng)村地區(qū)、城鄉(xiāng)接合部垃圾強制分類更為迫切,更需要通過源頭減量和分類回收來緩解壓力。”
“北京農(nóng)村垃圾分類有好的樣板可循,較早開展起來的優(yōu)秀示范有門頭溝區(qū)的王平鎮(zhèn),最近涌現(xiàn)的有昌平區(qū)興壽鎮(zhèn)的辛莊村、桃林村。相關部門應該盡早將這些農(nóng)村垃圾分類的示范經(jīng)驗進行總結,在繼續(xù)給予有力支持的基礎上,推廣到更多的地區(qū)。”
農(nóng)村推行強制分類有不少有利條件,廚余垃圾更容易就地處理,喂養(yǎng)動物或堆肥還田,成本較低。環(huán)保部水環(huán)境管理司農(nóng)村處調(diào)研員孔源對《民生周刊》記者表示,農(nóng)村垃圾分類的優(yōu)勢很明顯,比如農(nóng)村可利用空間大,而且屬于熟人社會,便于動員和監(jiān)督。
何時是適時?
2016年9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對外宣布,“十三五”期間,北京將研究適時推進生活垃圾強制分類。何時是“適時”、怎樣推進,引起環(huán)保人士及公眾的普遍關注。
渠成水到,賴偉杰用這4個字概括臺灣推行垃圾強制分類的經(jīng)驗所在。在他看來,政府層面垃圾分類、自愿回收制度建立起來后,居民對于垃圾分類,已經(jīng)很難稱其為“強制”,其實是居民個人自覺自愿的行為。
然而,對于北京等城市“箭在弦上”的垃圾分類工作,毛達則認為應體現(xiàn)強制原則:“強制就意味著必須有人承擔垃圾不分類的法律責任,而只要有法律責任存在,就必須清楚設定問責的界限和標準。垃圾分類的強制性應體現(xiàn)在清晰的管理目標、實施范圍、規(guī)范對象和問責制度上。”
他認為,首先要設定垃圾減量目標。垃圾分類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垃圾焚燒和填埋處理量,從而提高資源化利用率和減少末端處理產(chǎn)生的二次污染。只有明確“十三五”期間甚至未來更長時間內(nèi)垃圾焚燒和填埋處理減量目標,才能從根本上指導強制分類的方向和進程。
“5年后,北京垃圾焚燒和填埋處理總量應較2015年減少35%。當然,未來北京的總人口可能會繼續(xù)增加,給目標實現(xiàn)帶來壓力,但垃圾減量還可通過按量收費、禁用或限用一次性物品、強制回收、倡導節(jié)約等手段實現(xiàn)。如果措施得當,可以抵消人口增長帶來的垃圾增長量。”
其次是公布強制分類目錄。在毛達看來,經(jīng)濟價值高、易于回收的廢棄物不需強制就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回收利用。“應納入強制分類目錄的是那些難以通過市場機制分類回收的垃圾。”
此外,明確責任主體及其法律責任也至關重要。在毛達看來,垃圾強制分類管制的主體對象必須同時包括政府、企業(yè)、社會單位和市民個人。
“垃圾強制分類從長遠計,一定會減少整個垃圾管理系統(tǒng)的社會成本和環(huán)境成本,但短期內(nèi)意味著整個城市垃圾運輸和處理體系都要改革,其轉換過程需要資金投入。”毛達說,推行生產(chǎn)者延伸責任制是促進產(chǎn)品生態(tài)設計、預防垃圾產(chǎn)生以及清潔回收利用資源的重要制度,也能為分類回收利用體系提供穩(wěn)定的資金來源。
他建議,北京應在全國率先設立垃圾分類回收基金,凡納入強制回收目錄的產(chǎn)品生產(chǎn)企業(yè),若不能建立起自身產(chǎn)品的回收體系,都應該向基金繳納委托處理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