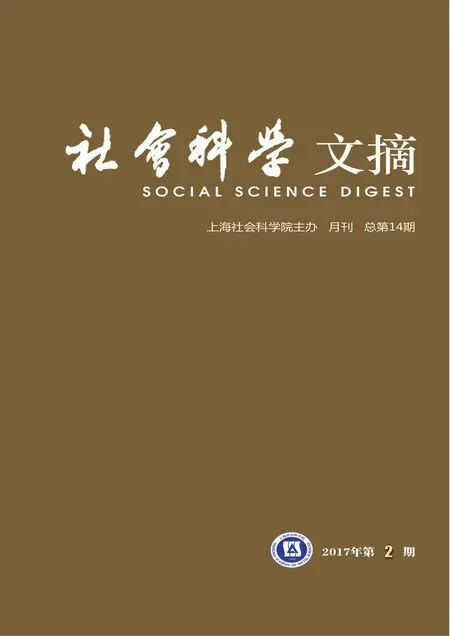交易成本、城市發展與新市民住房制度調整
文/孫斌藝
交易成本、城市發展與新市民住房制度調整
文/孫斌藝
作為人口和物質在空間上集中的一種形態,城市是現代經濟、社會、文化、技術、行政等各方面力量的交匯點。城市有助于發揮生產和分銷體系的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深度分工情形下的協作效率。由于城市道路、橋梁、公用設施、住房等具有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這種公共品具有生產上的非競爭性和消費上的非排他性,由此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這類物品,即市場會出現失靈。于是,必須由政府運用行政管理手段提供這些物品,促進城市的持續發展。
在人口和物質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中,人們交往更為頻繁,分工更為專業化,交易規模和頻率急劇增加,交往集聚現象出現,交易成本水平變化,尤其是像我國在較短時期大規模城市化,原有協調城市內部各種關系的內在和外在制度不敷使用,城市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極大地限制了城市績效水平提升,阻礙了城市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整個城市經濟體系經歷了巨大的重塑過程,新進入城市的人口不斷融入城市。較短時間集中進入城市的人口與原有城市人口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城市原有市民與新市民的沖突。本文所稱的新市民,是指由人口的機械增長形成的某一城市的新增人口,這類人口與所進入城市原有市民擁有不同的亞文化特點,實際生活中表現為城市的外來人口尤其是未獲得所進入城市戶籍的人口(如新近畢業未達到進入城市落戶條件的大學生)、農民工等等。新市民融入城市首當其沖的就是“住”的問題,各種制度失衡、不協調和沖突集中反映在新市民的住房問題方面。
制度、交易成本范式和城市交往集聚
制度在現代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中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可以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有習慣、內化規則、習俗和禮貌以及正式化內在規則。外在制度主要表現形式是國家法律。由于城市的復雜性,城市的發展過程與外在制度的日益細化和繁瑣聯系在一起。由國家出面建立的各種法令、法律、規章、政策和標準等都是外在制度的表現形式。例如,土地所有制、金融制度、戶籍制度,以及由國家制定的反映在各種規章中的制度類型。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國城市中出現的一些行政機構負擔過重是與外在制度缺乏內在制度基礎聯系在一起的。
表征城市特點的關鍵因素在于人口規模以及帶有不同制度烙印的群體差異,人口數量的急劇膨脹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相關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突出表現在相鄰關系、交通狀況、城市內人群分工、空氣、噪音和光污染、城市生態環境、人們交往距離與居住距離的分歧等方面。
當人口和各類物質要素在空間上集中時,集中程度越高,人口密度越高,人們對交通、基礎設施等的需求也會提高,人們之間的各類交往(包括各種交易)水平越高,從而對協調人們行為的制度的需求水平越高。當制度有效時,由于交往集聚所帶來的城市交易成本水平會趨于下降;反之,城市交易成本水平會趨于上升。其中,城市居民的居住狀況是集中反映交往集聚水平和狀況的重要表征,也是城市各種沖突的聚焦點。尤其是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城鄉分隔在持續了幾十年后,在較短時間內放開,新近擁入城市的居民與原有居民在遵循的制度規則方面存在巨大的落差,這種城市內沖突更加明顯。
城市發展中新市民住房問題的制度限制
城市發展中新市民進入城市、融入城市面臨著一系列的制度限制,新市民直接感受到的各種住房方面的“歧視”,導致城市發展中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大大抵消了城市集聚帶來的成本節約。同時,由于新市民與原有市民內化的制度規則不一致,人們在經濟交往中無法形成穩定的預期,或出現預期錯配,從而使這些問題更加突出。主要體現在:
1.戶籍制度
我國的戶籍制度是限制新市民融入城市最大的制度障礙,尤其是對新市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一線城市,往往對新市民采取強制性的行政限制,制定了進入城市長期居留的較高門檻。這對于只具備初步勞動技能甚至只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存在戶籍制度限制時,勞動力流動會受到阻滯,導致城市勞動力布局存在結構性失衡,提高了城市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固化了勞動力市場運行,從而使新市民的住房選擇范圍無法與其就業相匹配。
2.土地所有制、土地流轉制度及金融制度
當新市民試圖進入擬長期居留的城市時,往往會發現由于我國的土地制度、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等制約無法實現資產流動,資產固化的限制導致其擬購買或租賃城市住房時缺乏必要的啟動資金,如新市民中的農民工原有的集體土地資產無法進入市場變現,從而抑制了新市民改善居住水平的條件。
另一方面,在城市“匿名社會”的條件下,資產固化無法使其市場價值顯性化,導致新市民在購買住房時往往缺乏足夠的資產作為擔保獲得金融支持,大大抑制了其購房支付能力。
3.與身份相關的公共服務制度
長期以來,人們的身份與其戶籍所在地的公共服務捆綁在一起,新市民身份通常也意味著只能享受所進入城市的一部分公共服務,或者同等情況下被迫付出較大的代價才能享受同樣的服務,通常涉及到子女就學、醫療、福利保障等各個方面。當新市民無法享受這些公共服務時,他們就無法做出合適的住房決策。
這種狀況反映了目前城市的各種公共服務制度改變了新市民的住房決策條件,增加了其合理決策的交易成本,間接地也使城市集聚所帶來的正向效應被抵消,加劇了新市民的居住困難。
4.就業、創業和產業政策
我國一線城市往往視小而散、低資本密集高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落后產業,在產業政策方面施加了許多限制性條件,直接或間接地抑制了這類產業的發展。然而正是這類產業能夠吸納大量的勞動力,而其提供的各種產品和勞務正因其分散、靈活才為城市所必需,才能滿足城市對這些規模小、分布廣、需求波動性大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抑制這類產業會極大地損害城市的協同發展。
當新市民就業受制度性限制無法穩定下來時,那么相應的居住安排就會轉化為臨時性決策,由于缺乏對制度的長期穩定的預期,因工作調整頻繁導致居住地不斷搬遷,增加了新市民的實際居住成本。
5.慣例、習俗和倫理規則的沖突
每個新市民尤其是成長期處于不同地域的人群,往往在成長過程中內化了相應的習俗、處理事務的慣例或習慣、與周圍人群和社會相處的倫理規范,這些內在制度隱含在新市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帶有本能的性質。由此,新市民群體(地域群體)與相隔距離較遠的所進入的城市之間存在緊張的文化沖突,體現在居住方面就是嚴重的不信任,居住中相鄰關系復雜,容易誘發各類社會矛盾。
受這種亞文化性質的制度吸引,來自同一地域的新市民往往具有在所進入城市的特定區域集中居住的趨勢,當集中居住地某些負面活動達到一定水平時,由此將產生嚴重的城市病,提高了城市發展的交易成本。
促進城市發展、有效解決新市民住房問題的制度調整方向
促進城市健康發展且能有效解決新市民住房問題的合理制度框架,要求各類制度具有降低城市交易成本、具有正向激勵作用、鼓勵不同形式創新性試錯的作用,具有在住房問題上激勵其進行長期決策、提升其總體經濟福利的效能。因此,促進我國城市發展的新市民住房制度的調整方向應當包括:
一是改革農村土地所有制,允許農村土地實質性流轉,單個農民可以將土地在市場上自由交易,農民轉化或不轉化為新市民由其根據自身條件自由選擇。土地實質性自由流轉,可以促使土地資產的市場價值顯性化,新市民尤其是工作波動較大的農民工可以藉此支持獲得進入城市的初步保障和啟動資金。
二是改革戶籍制度,將目前的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制度分離,剔除公共服務的身份限制,依照人們的納稅情況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消除對新市民的身份歧視,使其住房決策只需考慮其經濟承受能力和自身偏好。
三是在強化對各類金融機構規則性、普適性監管的條件下,放開各類金融機構的微觀性貸款限制,允許其與各類主體包括新市民自由協商金融條件,新市民可以根據自身條件獲得金融機構不同的金融支持,滿足其購買或租賃住房的需要。
四是取消各類創業、就業限制,允許企業和新市民自由競爭、自由擇業,取消各類執業資格對新市民的限制。
五是取消各種住房市場的限制條件,允許新市民基于自身條件購買城市任意數量和品質的住房。
結論
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新市民住房問題能夠通過制度調整予以解決。城市人口導入,會提高城市交往集聚水平,交易成本水平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與之相適應的城市內在和外在制度都具有降低城市交易成本的特性,提升城市發展水平,反之,無效的制度會導致城市發展受挫。我國現階段由各種制度性因素導致新市民住房問題日漸嚴重,亟待通過制度調整以化解制約城市健康發展的沖突和協調失靈。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副教授;摘自《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