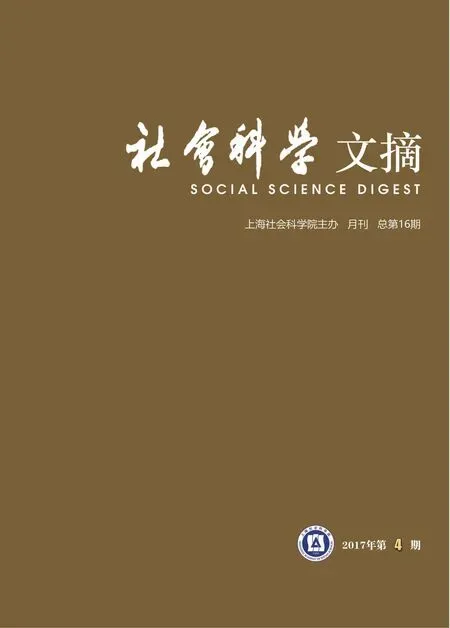學(xué)科特質(zhì)、評價標(biāo)準(zhǔn)及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學(xué)發(fā)展不能回避的幾個問題
文/龔放
學(xué)科特質(zhì)、評價標(biāo)準(zhǔn)及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學(xué)發(fā)展不能回避的幾個問題
文/龔放
把握學(xué)科特質(zhì):“像河一樣無常流淌”,抑或“像樹一樣依次生長”?
事實上,人類認(rèn)識客觀世界所形成的知識系統(tǒng)是復(fù)雜多樣的,是有各自的特性、特質(zhì)的,不能用狹窄的口徑、單一的尺度去觀照、衡量,去約束、規(guī)范。英國學(xué)者托尼·比徹曾經(jīng)專門論述不同的知識體系和學(xué)科文化,他把既有的學(xué)科分為兩類,其一是“規(guī)則性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areas of contextual imperative)”,即“具有嚴(yán)格定型的解釋順序,每一項新的研究成果在整個知識的描述中有它適當(dāng)?shù)奈恢谩保鼈儭跋褚豢脴湟粯硬粩嗌L,每一新的樹枝又依次生長出新的嫩枝”。此類學(xué)科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俄羅斯化學(xué)家門捷列夫發(fā)現(xiàn)元素的性質(zhì)隨著原子量的遞增而呈周期性的變化。他編制了第一個化學(xué)元素周期表,不僅把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63種元素全部列入表里,初步完成了使元素系統(tǒng)化的任務(wù),而且還在表中留下空位,預(yù)言了類似硼、鋁、硅的未知元素的性質(zhì)。第二類學(xué)科屬于“聯(lián)合性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areas of contextual association)”,它們“由許多觀念群構(gòu)成,沒有明確具體的框架”,好像“河在流淌,流向無常”。例如,關(guān)于高等教育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rèn)識,顯然無法像元素周期表和太陽系行星運行規(guī)律等“規(guī)則性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的知識那樣精確無誤而且可以重復(fù)驗證,它們往往充滿著不確定性,而且不可重復(fù),難以類比。例如,同樣是發(fā)生在20世紀(jì)60年代,中國的紅衛(wèi)兵運動與法國的“五月風(fēng)暴”,以及席卷美國的反越戰(zhàn)學(xué)潮,就有著完全不同的動因,呈現(xiàn)的形態(tài)和產(chǎn)生的影響也截然不同。
此后,托尼持續(xù)不斷地對學(xué)科分類、學(xué)科特質(zhì)以及學(xué)科文化進(jìn)行調(diào)查研究,并將自己的新見解發(fā)表在與保羅·特羅勒爾合著的《學(xué)術(shù)部落及其領(lǐng)地:知識探索與學(xué)科文化》一書中。其中最有價值的貢獻(xiàn)是:將廣義上的學(xué)科分為“純硬科學(xué)”、“純軟科學(xué)”、“應(yīng)用硬科學(xué)”與“應(yīng)用軟科學(xué)”等四類;依據(jù)學(xué)科研究對象的特點、知識發(fā)展的性質(zhì)、研究人員和知識的關(guān)系、研究流程、研究成果的信度和研究標(biāo)準(zhǔn)及研究成果的表現(xiàn)形式等等,總結(jié)歸納了不同學(xué)科的“現(xiàn)實特征”,“即學(xué)科研究特點與現(xiàn)實世界的差異”。在托尼看來,存在不存在一個邏輯嚴(yán)謹(jǐn)、天衣無縫的學(xué)科整體框架,是區(qū)分硬科學(xué)還是軟科學(xué)的重要標(biāo)識。所謂硬科學(xué),是指“邏輯嚴(yán)謹(jǐn)?shù)囊幌盗杏^點,就像我們做拼圖一樣,每一個新的學(xué)術(shù)發(fā)現(xiàn)都天衣無縫地鑲嵌進(jìn)這幅圖畫里”;而所謂軟科學(xué)則“表示各種觀點鏈接松散,沒有很強的關(guān)聯(lián)性,沒有很強的整體發(fā)展框架”。
令人感概的是,迄今為止,我們在討論學(xué)科建設(shè)時,很少考慮軟科學(xué)與硬科學(xué)這一基本的差異。我們在檢驗和判定是否構(gòu)成一個真正的學(xué)科,是否已經(jīng)從“前學(xué)科”或“潛學(xué)科”發(fā)展、成長為獨立的、成熟的學(xué)科時,最看重的判據(jù)就是:是否擁有嚴(yán)密、嚴(yán)整的學(xué)科理論體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題、規(guī)律等所構(gòu)成的嚴(yán)密的邏輯化的知識系統(tǒng)”。而我們學(xué)科建設(shè)的首要目標(biāo),也無一例外地將學(xué)科理論框架的確立,將特有的概念、范疇、命題、原理、規(guī)律等構(gòu)成的嚴(yán)密的、邏輯化、體系化的理論框架,作為我們追求、向往的“金蘋果”!根本沒有考慮它是否是一個主觀想象的、實際并不存在的東西!
《高等教育哲學(xué)》的作者約翰·S·布魯貝克顯然“不相信會有一種可以通過共同捍衛(wèi)其純潔性而永世可靠的、單一的、不變的、理想的大學(xué)教育‘觀念’”,他也“不打算為所有的學(xué)術(shù)機構(gòu)提出一種共同的哲學(xué)”。因為他深知,“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歷史發(fā)展中一樣,高等教育哲學(xué)的許多方面也是隨著歷史發(fā)展而逐漸顯現(xiàn)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大學(xué)面臨著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以及不同類型的社會需求,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給高等院校發(fā)展的壓力與推力也各不相同。所以,引領(lǐng)大學(xué)回應(yīng)這些壓力與挑戰(zhàn),滿足相關(guān)社會需求并取得各自的合法性的觀念與舉措也各有千秋。先哲和前人在成功解決他們面臨的矛盾與困難并成功推進(jìn)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留下的哲學(xué)思考、行動方略與變革舉措,無疑是彌足珍貴的,是后輩與來者解決自己的問題、回應(yīng)當(dāng)下的挑戰(zhàn)時可以借鑒的參照系,但它們“像河一樣流淌”,并不能像拼圖那樣一一鑲嵌無縫。
根據(jù)托尼·比徹的研究發(fā)現(xiàn),高等教育學(xué)與法學(xué)、行政管理學(xué)等應(yīng)用社會科學(xué)一起,隸屬于“應(yīng)用軟科學(xué)”,其特質(zhì)是:“實用性、功利性;注重專業(yè)(或半專業(yè))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個案研究和判斷法;研究成果為規(guī)約或程序的形成。”我完全認(rèn)同托尼·比徹的判斷,即高等教育學(xué)是應(yīng)用軟科學(xué)之一;我們必須尊重此類學(xué)科的特質(zhì),即“實用性”“功利性”和“注重專業(yè)實踐”,據(jù)此調(diào)整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及突破口和著力點。我們高等教育學(xué)科建設(shè)的方略必須改弦更張,必須放棄探尋、構(gòu)建一個邏輯嚴(yán)密、范疇特殊、嚴(yán)謹(jǐn)規(guī)整、天衣無縫的高等教育學(xué)理論體系的目標(biāo),而將研究并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中的重大現(xiàn)實問題作為首要任務(wù)。
必須強調(diào),這樣提出問題并非貶低或者取消我們對高等教育學(xué)科理論的探討,而是認(rèn)為,高等教育學(xué)科的真正有價值的理論成果絕非在書齋案頭冥思苦想、演繹、建構(gòu)的產(chǎn)物,而是在高等教育實踐中成功解決當(dāng)時、當(dāng)?shù)赝怀龅拿芎图值碾y題后的必然結(jié)果。就像當(dāng)年洪堡與費希特、施萊爾馬赫等創(chuàng)建柏林大學(xué)的實踐——旨在為德意志民族的重新崛起提供新的精神力量與智慧人才——其結(jié)果是不僅“用現(xiàn)代的方式重建了大學(xué)”(阿特巴赫語),而且“使舊瓶裝入了新酒,舊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學(xué)府如此徹底地按照一種理念進(jìn)行重塑,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語)這注入的“新酒”——嶄新的大學(xué)理念——也就成為重塑現(xiàn)代大學(xué)的精神財富,成為高等教育學(xué)的理論精粹之一。
確定“驗證真理”的標(biāo)準(zhǔn):不同“廳堂”自有不同
對于學(xué)科特質(zhì)及其“驗證真理”方法的差異性,美國學(xué)者約翰·S·布魯貝克有過相當(dāng)精辟的論述:“實際上,在學(xué)問的圣殿里有許多廳堂。在有的廳堂里,學(xué)者是通過在隔音的實驗室里撥控制盤來驗證真理的。在另一些廳堂里,他們是通過在喧鬧的城市、福利中心、診所、法院等地方參與工作來積極驗證真理的。還有一些廳堂里,一些孤軍奮戰(zhàn)的思想家是在靜寂的圖書館里通過鉆研故紙堆來驗證他們的思想的。”這其實是在啟發(fā)人們必須思考并有所抉擇:我們是如何“驗證真理”的,是在“隔音的實驗室里撥控制鍵盤”?還是在圖書館“鉆研故紙堆”?抑或深入現(xiàn)場“參與工作來積極驗證真理”?這不僅因軟、硬科學(xué)而有別,還因知識生產(chǎn)的模式不同而不同。
托尼·比徹等在長達(dá)7年的時間中通過兩個國家、18個學(xué)術(shù)機構(gòu)、跨越12個學(xué)科的1220名學(xué)者教授的調(diào)查訪談,用大量鮮活的資料深化了在“學(xué)問圣殿”的不同“廳堂”驗證真理的不同特點、方式與結(jié)果。如他強調(diào)物理學(xué)等“純硬科學(xué)”的發(fā)展特點是“累積的;原子論的(晶體狀的/樹形的);與普遍、數(shù)量、簡化相聯(lián)系;客觀性,價值中立的”。而“純軟科學(xué)”如歷史學(xué)、人類學(xué)等的發(fā)展卻迥然有異,呈現(xiàn)“反復(fù)的;有機的(與河流相似);注重細(xì)節(jié)、質(zhì)量與復(fù)雜性;主觀性、受個人價值觀的影響”等鮮明特點。“純硬科學(xué)”如物理、化學(xué)、數(shù)學(xué)等等主要“為某種發(fā)現(xiàn)或?qū)δ撤N現(xiàn)象進(jìn)行解釋”,其研究成果常常以學(xué)術(shù)論文的形式呈現(xiàn),其對真理的驗證和知識的陳舊標(biāo)準(zhǔn),都有明確的原則并容易達(dá)成共識,因而具有國際可比性,其學(xué)術(shù)前沿所在與學(xué)術(shù)影響力大小,也可以量化甚至排序。而“純軟科學(xué)”重在“對某種現(xiàn)象進(jìn)行理解或鑒賞”,往往見仁見智,研究成果也難以一一證實或證偽,對新知識的確認(rèn)和原有知識陳舊的確定標(biāo)準(zhǔn)常常“存在爭議”,學(xué)科發(fā)展的標(biāo)識與研究成果的評價也有所不同。
國務(wù)院文件強調(diào),雙一流建設(shè)必須“堅持以績效為杠桿”。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績效”?是發(fā)表SSCI或者CSSCI論文的數(shù)量?是高影響因子學(xué)術(shù)期刊的發(fā)文量?還是世界EIS學(xué)科排序前1%?或者,是完成國家級、省部級課題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
我曾經(jīng)參加教育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重點資助項目“中國人文社會科學(xué)學(xué)術(shù)影響力研究”,主持教育學(xué)子課題的研究,兩次嘗試運用科學(xué)計量學(xué)的理論與方法,借助《中文社會科學(xué)引文索引》即CSSCI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分析我國教育研究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我發(fā)現(xiàn),運用科學(xué)計量學(xué)來分析教育研究機構(gòu)、期刊及學(xué)者個人的學(xué)術(shù)水平和學(xué)術(shù)影響力,確實有說服力!但同時我也發(fā)現(xiàn),期刊論文或?qū)V氨灰奔啊氨灰省彼从车模瑑H僅是學(xué)者教授的研究所得,即他的思想、觀點對“文本”的影響力,而教育研究的真正目的,卻在于影響教育實踐,包括影響教育決策、影響教育教學(xué)和教育管理改革,在于為一線的教師和學(xué)生、為各級各類學(xué)校管理者提供新視野、新思路和新見解!
什么是真正的影響力?什么是真正富有含金量的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績效?是對教育宏觀決策的影響,是對學(xué)校治理方略的影響,是對教師的教與研,對學(xué)生的發(fā)展與成長的真切而實在的影響!前者如匡亞明、劉丹、李曙森、屈伯川等四位老校長關(guān)于建設(shè)“重中之重”的“8.35建言”,后者如蘇聯(lián)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如“慕課”的開發(fā)與創(chuàng)新……這些,才堪稱對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教育變革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才堪稱引領(lǐng)一個時代教育發(fā)展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在高等教育學(xué)的學(xué)科建設(shè)中,如果仍只注重核心刊物、影響因子的評價,一味倚重SSCI發(fā)文量和引文評價,而忽略甚至無視對大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經(jīng)歷、學(xué)習(xí)投入、學(xué)習(xí)質(zhì)量的研究,忽略甚至無視對課程、教法的研究,對第一線從事教學(xué)、教育管理者的研究和影響,那就將只能是一種典型的“異化”,只會催生一批擅長紙上談兵、熱衷自娛自樂的所謂“學(xué)者”,根本無助于中國高等教育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也難以真正提升高等教育學(xué)的學(xué)科水平!
轉(zhuǎn)換研究范式:數(shù)據(jù)羅列不能代替思想的凝練
研究方法的選擇,歷來是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20世紀(jì)90年代初討論高等教育學(xué)的發(fā)展方略時,曾有不少同仁將能否找到高等教育學(xué)自己的、特有的研究方法,作為我們學(xué)科趨向成熟的一個依據(jù)。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教授認(rèn)識到,不必刻意追求為我獨有的一種研究方法,也許,借助社會科學(xué)的多學(xué)科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就是高等教育學(xué)的方法論?
伯頓·克拉克是最先倡導(dǎo)并嘗試“打開多盞聚光燈”,即借用社會科學(xué)多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的。他在《高等教育新論——多學(xué)科的研究》中文版序言中特別強調(diào):“各門社會科學(xué)及其主要專業(yè)所展開的廣泛觀點,為我們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工具……每一觀點有它獨特的優(yōu)點,也各有其缺點,我們需要了解那些優(yōu)點和缺點是什么。利用這些優(yōu)點,我們可以發(fā)展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識到這些缺點,我們可以避免每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的‘井蛙之見’和缺乏辨別力。”潘懋元先生組織他的弟子們,在借助多學(xué)科的方法研究高等教育方面進(jìn)行了十分成功的初步的實驗。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的是,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的引進(jìn),為高等教育學(xué)科的深入發(fā)展與繁榮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毋庸諱言的是,我國高等教育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同樣存在“邯鄲學(xué)步”“東施效顰”式的弊端,近年來,高教研究界盛行的以量化、數(shù)據(jù)替代嚴(yán)肅的分析思考,就是一例。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在《現(xiàn)代大學(xué)論》一書中討論了“研究究竟由什么構(gòu)成”的問題。他強調(diào):“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確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學(xué)、社會科學(xué)和教育學(xué)領(lǐng)域這種做法相當(dāng)普遍——不是研究。未經(jīng)分析的和無法分析的資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構(gòu)成研究。……有沒有圖表、曲線和百分比,這些也都不是研究……” 弗氏的許多觀點曾經(jīng)一再被中國學(xué)人援引,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的教育學(xué)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獨到見解,卻很少引起國人關(guān)注。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科學(xué)研究?弗氏說:“科學(xué)的本質(zhì)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種思想,雖然他堅持這種思想的方式可以十分靈活。如果事實與他的看法相反,他必須隨時準(zhǔn)備修正或放棄自己的想法。無休無止的計算絕不會產(chǎn)生理論、原理或思想。”所謂“思想”,就是真知灼見,就是對于歷史、現(xiàn)狀,就是對于高等教育這一復(fù)雜系統(tǒng)的準(zhǔn)確把握和深刻認(rèn)識,對于其發(fā)展進(jìn)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的相對靠譜的預(yù)測。高等教育現(xiàn)狀和歷史的研究必然涉及諸多信息、資料、數(shù)據(jù)、案例,真正的科學(xué)研究是對這些信息、數(shù)據(jù)的去偽存真的分析和鞭辟入里的解讀,是對這些數(shù)據(jù)起伏變化原因的追溯和探討!思想和觀點來自這些分析、解讀與探討。我們不能用羅列一大堆數(shù)據(jù),繪制一系列曲線圖、直方圖或者餅圖,甚至列出一長串漂亮的“結(jié)構(gòu)方程”公式,來代替我們的批判性思考和獨到性闡釋。遺憾的是,這樣的研究陣勢、研究范式卻在期刊論文、學(xué)位論文及課題結(jié)題報告中風(fēng)行一時、大行其道,似乎沒有曲線,沒有百分比和方差分析,沒有計算公式,就不成其為“科學(xué)研究”!其實,如弗氏所云,許多所謂的問卷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分析“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要么是憑調(diào)查開始時的常識就顯而易見的,要么是最終得不到可靠證據(jù)支持的”。
今天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了大數(shù)據(jù)時代,我們的高等教育研究,也需要實證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分析,來把握趨勢、診斷現(xiàn)狀、研究問題,來替代想當(dāng)然、拍腦袋的決策管理模式。但是,這些問卷調(diào)查的設(shè)計,應(yīng)當(dāng)科學(xué)、自洽;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收集,應(yīng)當(dāng)全面、客觀、可持續(xù)。
最后強調(diào)一下案例分析法。“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述了夫子自道的一段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認(rèn)為,從方法論的角度解析孔子這段話,還是很有見地的。與其泛泛而論、“載之空言”,不如抓住具體“行事”,在描述與評析中將所思所得“深切著明”地闡發(fā)出來。英國學(xué)者托尼·比徹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作為“應(yīng)用軟科學(xué)”的高等教育研究,應(yīng)當(dāng)采納的研究方法是:“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個案研究和判例法;研究成果為規(guī)約或程序的形成。” 與法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科的案例法有所不同,高等教育學(xué)科的案例研究除了具體院校的案例之外,還可以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地區(qū)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成功與失敗、高等院校的崛起、轉(zhuǎn)型或衰落、分合……將當(dāng)時當(dāng)?shù)禺?dāng)政者的判斷、決策、執(zhí)行,以及研究者的思考、批判、爭論和建議等等,匯集成一個個專題研究案例,作為高等教育思想素材,以供后來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們思考、借鑒和資政。
5年前我曾經(jīng)建議在高等教育學(xué)研究方面做好三項工作:第一,選擇、確定研究的真命題。第二,厘定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范疇,逐步凝聚共識,規(guī)范高等教育研究群體多采用的“符號概括”,界定相關(guān)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并盡可能與國際學(xué)術(shù)界接軌,避免出現(xiàn)“雞同鴨講”的局面。第三,積累、匯集高等教育研究共同體的“范例”,可以分專題遴選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評述,逐步形成共同體的“話語體系”。時至今日,高教研究界對于“選擇、確定研究的真命題”和“厘定基本概念與范疇”正在形成共識,而對于“范例”的選擇、匯集與研判,對于高等教育研究思想庫、范例庫的建設(shè)等,尚需繼續(xù)呼吁,并大膽嘗試。
(作者系常州大學(xué)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專家、南京大學(xué)教育研究院教授;摘自《中國高教研究》2016年第9期;原題為《把握學(xué)科特性 選準(zhǔn)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學(xué)科建設(shè)必須解決的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