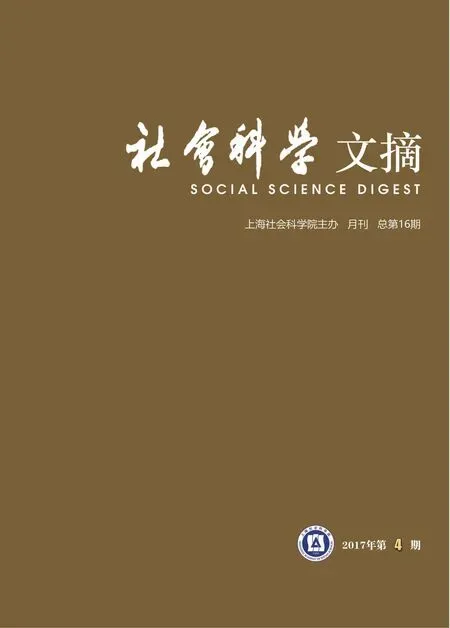國家控制與醫生臨床自主性的濫用
文/姚澤麟
國家控制與醫生臨床自主性的濫用
文/姚澤麟
在現代社會中,生物醫學模式的興起使得醫生獲得了較高的經濟地位、職業聲望與文化權威。在療治疾病方面,他們保有至今無法撼動的權力。而在被賦予巨大權力的同時,他們在工作中卻通常不受外部主體的干涉,外行通常很難對其“指手畫腳”。于是,現代社會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外人不能辨識醫生的執業行為,那么如何確保其所作所為能夠符合“客戶”也即病人的利益?同時,集各種權力于一身的國家能否保證醫生在執業過程中將病人利益置于首位?本文以田野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用當代中國經驗回答這一職業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當下,我國城市地區的醫生似乎正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處境之中。他們的執業行為多被人所詬病,醫生被認為嚴重喪失職業道德,因為他們唯利是圖,將本應置于首位的病患利益拋諸腦后。在社會大眾看來,于自身的經濟利益與客戶的健康權益之間,醫生似乎總是選擇前者,而這就是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所在。因此,患者不再信任醫生,甚至攻擊醫生。我國醫生這種“不道德”的執業行為,顯然昭示著國家對該職業實施的社會控制的失敗。那么,在當代中國,國家究竟對醫生職業施加了哪些規范與控制?為何最后會歸于失敗?國家控制及其后果與看病難、看病貴、醫患關系惡化等一系列醫療領域當中的問題有著怎樣的關系?
文獻回顧:醫生執業行為的社會控制
根據弗萊德森的經典論述,“職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是職業的核心特征,是“一種對其工作的合法控制的狀態”。這種控制意味著無論從業者是否能決定執業的制度設置,其在執業過程中可以自由地做出決策和處置;而且,只有職業本身才能評判其工作表現,外行無法置喙。沿著弗萊德森的思路,霍夫曼在研究捷克的醫生職業時提出法團自主性(corporate autonomy)和臨床自主性(clinical autonomy)兩個概念,前者指“組織起來的職業群體定義有關自身工作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政治權力”,而后者則指“對工作場所中決策的控制”。二人都認為,臨床自主性是“中性”的,其中并不涉及倫理或價值的面向。臨床自主性只是醫生對醫學知識的完整(并不一定“合理”)的應用,醫生只是根據專業知識對病人病情做出診斷與治療,卻并不意味著其一定遵循將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職業倫理。如此,倘若外行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醫生執業行為的恰當與否,那么醫生的臨床決策與行為如何能夠得到有效的社會控制,從而保證其不為了追求私利而侵害病患的權益?
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功能主義者的回答是,通過有效內化角色期待可以實現對醫生的社會控制,但這顯然不符合事實。那么,在現代社會,“對其他所有一切擁有最終權力”的國家能否實現這一點?理論上講,現代國家對于職業生活似乎既有干預的能力、又有干預的合法性。但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蘇聯和東歐社會,還是我國的臺灣地區,“國家”干預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最后,西方民主國家總結出一條規范醫生執業行為的經驗,即“要控制這群技術菁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們的利益整合到集體性的組織空間,讓他們分享決策權力和責任。這種國家與醫療專業關系的制度化,一方面形成‘專業自主權的保護膜’,使國家的政治權威尊重專業領域的技術權威,另一方面則凝塑醫療專業的集體責任,確保他們的合作”。
國家對醫生職業的干預與控制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相對穩定,總體上國家能力依然強大。醫學職業則仍舊公立醫院,進而依附于國家,同時亦由于現行政治體制下醫生缺乏獨立自主的職業協會維護自身權益,因此,醫生職業缺乏法團自主性。在這種條件下,國家單方面安排了有關醫生執業行為的制度設置,而醫生職業無法與國家就此進行協商。這集中體現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的“畸形市場化”,即一方面公立醫院須自負盈虧,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僅占其總收入的不到10%;另一方面,多數醫生仍然依附于公立醫院,國家嚴格管控著醫療服務的價格和醫生的勞動力價格。
“事無巨細”地對醫療服務的價格管制產生了“價格扭曲”的后果。尤其是反映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和知識價值的那部分價格只占醫療服務總價格的很小比例,因而成為醫療服務價格中價格扭曲最為嚴重的要素之一。醫生通常都會拿醫療服務的定價與其他行業的收費相比。以理發費、美容法、停車費等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收費標準為參照,醫生深感自身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價格畸低,根本無法反映他們的知識與技能,于是他們感受到了極大的不公。然而,缺乏法團自主性的醫生又無力改變這一不合理的制度設置。那么,國家是否就成功地對醫生實施了社會控制,從而遏制了醫生的逐利傾向,使其執業行為最終以患者的利益為依歸呢?
公立醫院中的雙軌分配制
我們的研究發現,國家控制的政策效果并非如國家所愿,而是呈現出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這集中體現在公立醫院的雙軌分配制和醫生的“雙向支配”地位中。
改革前,國家通過單位向醫生發放固定的工資,工資與醫生的工作表現與工作業績沒有關聯。公立醫院企業化改革開始后,醫生的收入結構逐漸演變為兩個主要部分:由國家控制的正式收入(formal income)和不受國家控制的非正式收入(informal income)。
正式收入是合法的、由醫院發放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基本工資完全依照國家有關部門制定的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基本工資標準執行。而“績效工資”則是根據醫生的工作表現和醫院與科室的經濟收益而給予的獎金,其數額可達基本工資的2至6倍。通過績效工資,醫生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與由其醫療服務所產生的經濟收益掛鉤,這是醫院調動醫生積極性的一項最為基本的手段,但也催生了醫生的誘導需求與過度醫療問題。
不過,誘導需求與過度醫療亦來源于“非正式收入”的驅動。此種收入主要是指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的收入,常常是非正式的、灰色的,甚至是不合法的。這主要包括來自藥品和醫用耗材的“回扣”與紅包,回扣直接來自藥品企業和醫用器械公司;而紅包則來自患者。追根溯源,回扣與紅包都來自于患者。二者皆是身在體制內的醫生將自己的職業權力進行轉換而得到的經濟利益。這種執業行為邏輯的根源,一方面是公立醫院自負盈虧后的創收壓力,另一方面則是醫生深感自己的勞動力價值無法在現行醫療服務價格體系中得到反映的一種反應。在無法改變相關制度設置的情況下,醫生們發現,積極提供服務,甚至誘導需求與過度醫療是一些可行的辦法,從中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績效工資和非正式收入,借此彌補其較低的正式收入。但誘導需求與過度醫療意味著醫生執業行為的失控,也即意味著醫生對其臨床自主性的濫用。在這種誘導過程中,醫生職業的道德基礎已經被此種濫用臨床自主性以從病人中攫取經濟利益的行為所深深腐蝕。
公立醫院醫生的“雙向支配”地位
公立醫院及其醫生的“雙向支配”地位為醫生通過雙軌分配制攫取更多經濟利益提供了便利條件。以藥品為例,從藥品的下游也即患者來說,公立醫院和醫生面對的是一個個的“散兵游勇”;從上游來講,作為壟斷的藥品終端銷售者,公立醫院及其醫生在面對藥企時亦占據強勢地位。
醫生對患者的支配地位首先是因為專業人士與外行之間的知識鴻溝。但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醫生職業群體依附于迄今仍然主導醫療服務市場的公立醫院,這一事實加強了醫生在面對患者時的優勢地位。既有調查顯示,患者雖然對公立醫院所提供的服務不甚滿意,但在公立醫院主導的醫療服務領域,他們幾乎別無選擇。最終,患者對公立醫院的“高度認同”就使得其在藥品銷售中對患者保有支配地位。此外,醫療保障的定點制度也極大地排斥了患者前往非公立醫院就醫或者去藥店購買藥品的可能性。從這個邏輯上講,近年來醫療保障覆蓋面和待遇的提高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公立醫院在藥品銷售中的壟斷地位。
除了對服務對象的支配,公立醫院的醫生還支配著醫藥廠商。回扣的存在說明了醫生面對醫藥企業和醫藥代表時的強勢地位和壟斷權力,而這還是以公立醫院在醫療服務市場中的統治地位為基礎的。基于在醫療服務領域的主導地位,公立醫院實際上成了目前最大的“藥品銷售商”,而公立醫院里面的醫生則是具體的“售藥者”。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以藥養醫”政策恰恰賦予了公立醫院抬高價格銷售藥品的機會。因為公立醫院的終端銷售壟斷地位,醫療機構的進藥價格低于報給政府的價格,這樣既能做到政府所規定的最高收益率為15%的規定(“明扣”),而與此同時,還有藥企對醫療機構的銷售返還(“暗扣”)。因此,盡管公立醫院藥品銷售的收益率名義上不超過15%,但實際上卻遠遠超過這一限度。這也就意味著藥價名義上由政府嚴格管制,實際上卻掙脫了管制而有著高昂的流通成本。
結論:臨床自主性濫用的后果及其治理
本文的研究表明,經濟改革開始后,非公立醫療機構并沒有蓬勃發展,公立醫院仍然占據著醫療服務市場的壟斷地位。但與此同時,公立醫院卻經歷了一種“畸形市場化”的改革過程,從而呈現出一種怪異的“兩面性”:一方面,政府依然控制著醫生職業,同時也對醫療服務的價格繼續實行嚴格管控;另一方面,公立醫院又被要求自負盈虧,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支持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于是,對于身在其中而又不得脫身的醫生來說,其一方面需承擔來自于組織的自負盈虧的壓力,另一方面又面對著自己的勞動價值被嚴重扭曲的現實,他們開始向病患提供誘導需求和過度醫療服務,通過將自己的行醫權轉化為經濟利益的方式,獲得了非正式收入,從而彌補了自己由于國家的不當控制而導致的較低的正式收入。這就是公立醫院中的雙軌分配制。
同時公立醫院的醫生又通過其雙向支配地位便利地“駕馭”雙軌分配制,不斷獲取經濟利益。這種雙向支配地位要從公立醫院對醫療服務市場的壟斷地位中去尋找根源。正是由于公立醫院的主導地位,才導致一方面,公立醫院與醫生對患者就醫占有支配地位,患者除了公立醫院幾乎沒有其他可靠的就醫選擇,而且現行的醫保制度更強化了這種效應;另一方面,公立醫院與醫生對醫藥廠商亦占據支配地位,因為公立醫院乃是藥品與器械的銷售終端,這些產品能否被使用最終取決于醫生對患者的臨床處置。因此,無論是公立醫院當中的雙軌分配制,還是這些醫院及其醫生的雙向支配地位;無論是醫生勞動力價值被嚴重扭曲,還是其可以借積極甚至過度提供醫療服務而換取經濟利益,最終都導源于一個事實,即醫生對公立醫院的依附狀態以及與此緊密關聯的職業法團自主性的缺失。
在這種體制下,醫生群體雖然通過“發揮所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身的經濟損失,但這種常態化的“不道德”的執業行為亦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因為這種行為是以醫生濫用臨床自主性為前提的。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由國家所設定并施行的對醫生行醫的社會控制機制基本是失效的,甚至已經走向了其制度目標的反面,可以說最終導致了“三輸”的結果。首先,對醫生職業來說,盡管很多從業者依靠其臨床自主性獲得了經濟收益,但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包括整個職業的公共形象受損、患者對其信任缺失,甚至人身安全不斷受到威脅。而且,既然醫生個體的經濟利益可以通過此種方式獲得滿足,那么通過集體行動來維護整個職業的利益也就不會提上議事日程。換句話說,這種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斷強化著這一體制,阻礙了任何對依附狀態的可能變革。其次,對患者來說,他們深切地感受著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是由國家的不當規管所導致。國家將醫生束縛在公立機構導致醫生人力資源不能因應市場需要而進行有效配置,從而導致了看病難,而醫生的誘導需求和過度醫療行為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看病貴。患者最終將不滿、埋怨、憤恨,甚至暴力都導向了直接面對他們的醫生。最后,對政府來說,雖然目前醫生職業很大程度上承當了“緩沖器”的角色,但民眾和醫生不滿的情緒不能不說是對政府治理和社會穩定的一種潛在威脅。
所以,目前這種情況亟需改變。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國家無法有效監管醫生的執業行為,因而醫生能夠通過濫用臨床自主性來彌補自身的經濟損失。法團自主性的喪失是這些問題的根源。由此可見,重構醫生職業與國家之間的制度化關系,從而賦予該職業法團自主性是國家應該考慮的政治社會議程。法團自主性的獲得至少可以給醫生職業帶來兩個積極的后果。其一,醫生職業由此可能形成維護自身利益的行業組織,從而真正代表廣大醫生更多地發聲并參與到國家的政策制定當中,逐漸改變目前一系列不合理的醫療衛生政策。其二,自治的行業協會的組建可能形成自我規范(self-regulation)的制度環境。這種自我規范一方面是醫生個體通過加強職業倫理的熏陶而加強自我約束,另一方面則是醫生職業群體內部形成更為有力的同行評價與監督,再輔之以外行主體的制約。
按照上述邏輯,本文似乎給讀者這樣的印象:只要國家放開控制,醫生濫用臨床自主性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本文的確采取了制度解釋的視角,但并不認為制度變革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一個職業的發展需要外部的制度依托,亦需要內在的精神支撐。職業道德規范的建立或重建,同樣是應對當下種種問題的必要措施,在醫生的職業教育和執業階段都應該加強并內化職業規范與倫理教育,自治行業協會的創建將有助于實現這一點。本文雖未詳細論及此點,但堅信這亦是應對醫生職業自主性異化問題的極為重要的手段。
就本文所集中探討的國家控制而言,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應當是逐步開放醫生的執業自由,給予民營醫院和私人診所以與公立醫院相同的地位,展開平等的競爭,由此形成醫生的勞動力市場,改變大多數醫生迄今為止仍無可奈何地依附于公立醫院的狀態。執業自由會帶來醫生的流動,非公立醫療機構的成長與發展會對公立醫院形成競爭壓力,改變公立醫院對醫療服務市場的壟斷,推翻其與醫生的雙向支配的優勢地位,最終促使其與醫生變革當下一系列違犯醫學職業倫理的行為。由此,本文所分析的一系列問題才可能得到緩解或解決。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摘自《社會》2017年第2期;原題為《國家控制與醫生臨床自主性的濫用——對公立醫院醫生執業行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