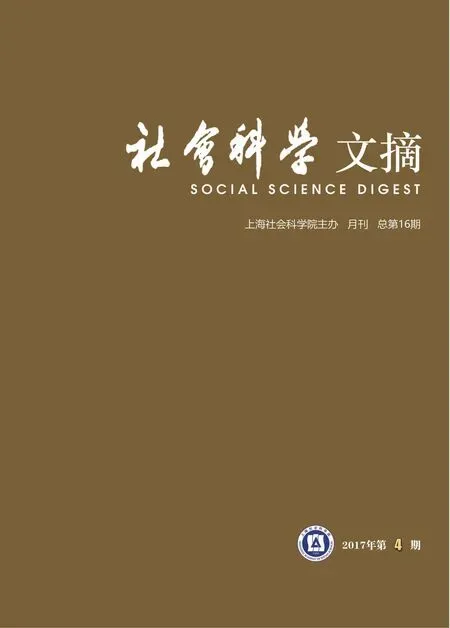由明入清:社會結構的變動
——以八旗、保甲制度的考察為中心
文/趙軼峰
由明入清:社會結構的變動
——以八旗、保甲制度的考察為中心
文/趙軼峰
明清政權更迭不僅帶來國家政策調整,而且帶來社會分層結構的改變。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隨著原為邊疆地區性制度的八旗體系通過中央權力輻射全國,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構成一個依附于皇室同時相對于社會其他人群又享有多方面特權的特殊階層,從而使層級性社會區分大幅度凸顯。八旗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旗體系內部的多層級身份區分,擴大了依附性社會關系的規模并增加了底層人口奴仆化的通路。保甲制度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清前期普遍推行,體現了政治專制與社會等級深化的深度結合。社會結構在清代的此種推演,與商品經濟在明清兩代相繼活躍繁榮相比,顯示了更多的斷裂性。
八旗制度與入清社會層級的復雜化
本文所說社會結構指依據社會地位差異而構成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在國家體制中的關系格局。明代中國社會有四個基本階層:貴族、士紳、庶民、賤民。貴族居于社會層級結構的頂端,依托帝制體系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特權,具有較強的封閉性。以功名與官職為標志的士紳階層受科舉制度調節,具有一定開放性,享有一定政治和社會特權。庶民階層總體地位穩定,職業和空間流動性都趨于增強,軍、匠、灶等戶與民戶之間的差別明顯縮小,但庶民中社會權利略低于民戶的人群依然存在。奴仆階層人數趨于增加,蓄養奴仆的階層面有所擴大。同時,明代層級性社會結構“兩邊小,中間大”。居于社會等級地位頂層的貴族,并不是主要的社會政治權力主體,而是龜縮在社會頂層的寄生性人群,并未落實為普遍的貴族統治。總體而言,明代中國社會結構具有趨于平面化的傾向。處于變與不變糾結中的明代中國社會,經過明清政權更替之后,在清代又有怎樣的推演?這是本文要討論的基本內容。
如前所述,明代社會具有層級結構,但因為處于頂層的皇室貴族與處于底層的奴仆和賤民遠不如處于中間的士紳、庶民兩個階層龐大,所以對于社會絕大多數人口而言,層級差異并不十分貼近。而清朝入關之初以武力強令漢族剃發易服,推行“首崇滿洲”、“旗民分治”的區分政策,體現出民族統治的特色。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說,民族統治與貴族統治都以強化社會層級區分為特征,區別是,民族統治是從原社會外部強加形成,貴族統治則可以是原社會固有,也可能是伴隨民族統治而從外部強加的。
明朝社會殘存的貴族制和處于發達狀態的士紳特權制,經與清朝的民族統治結合,形成重新強化的貴族制、延續的士紳特權制與民族統治交融的格局,社會身份界定社會成員地位、權益的意義增強,社會分層趨于強化。將這種轉變落實于社會的體制因素,首先是八旗制度。
八旗是清軍入關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的氏族首領主導的兵農合一社會體制。氏族組織是建州女真實現對周邊征服與擴張性融合的主導組織架構。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滿洲八旗體制,實際上圍繞愛新覺羅家族,將滿洲人眾整合到統一的軍事社會體制中,構成國家制度的支撐體系。這一整合,大大強化了處于擴張期的滿洲社會的整體性、軍事化程度以及共同對外行為能力。在此種體制內,八旗人丁主要從事軍事行為,依靠戰爭虜獲和奴仆農耕等方式加以供給,從而圍繞八旗,又形成了龐大的依附者社會群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八旗滿洲是個整體的軍事貴族階層。其成員無論地位高低,相對于社會其他階層說來,都是享受特殊權益的人群。滿洲人口有限,而急速的社會擴張需要更強大的軍事力量,于是部分順服的蒙古人、遼東地區漢人被編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稱為八旗蒙古、八旗漢軍。這些人在社會組織方式和社會角色地位意義上,與普通蒙古、漢人皆有區別。八旗制度隨之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擴展到滿洲社會之外,形成了在原本族屬意義上并不一定屬于滿洲但在社會體系意義上附庸并趨于融入滿洲的一個社會層。清軍入關過程中,滿、蒙、漢八旗作為核心軍事力量,最大限度地分享了征服收益,同時又保持了與八旗以外社會之間在組織方式、角色身份、法律權益各方面的差別。八旗在清入關后,沉淀成為清前期中國社會的一個規模龐大、高度體制化且內部結構復雜的特殊社會。
入關戰爭期間,八旗人眾就得以分享清軍征戰的收獲。入關之后,清朝在京畿地區實行圈地,繼續依照分享戰利品原則,對八旗人眾加以報償。隨著戰爭逐漸停止,虜獲收益不再成為八旗收入的主要來源,清朝對八旗實行國家供養制度。八旗人眾別立戶籍,由八旗組織單獨管理,實行“旗民分治”。因為八旗與非八旗之間有嚴格區隔及八旗內部長期保持著森嚴而復雜的等級和類別,所以清朝特別重視記錄八旗系統內部人員身份的“旗檔”。“旗民分治”具有人為強化社會區隔的含義。清前期劃定旗民居住分界,禁止混居。旗人與非旗人之間通婚也受到一定限制。作為特權階層,八旗人眾享有法律特權。民人犯法,有笞、杖、徒、流、死五刑;旗人則輕刑同樣處置,重刑可以折枷,杖刑得以改鞭刑,死罪得援引本人或親屬軍功免死。八旗人眾除了作為清朝地位優越的軍事力量之外,還享有進入國家權力體制的特殊渠道。八旗本身是一個龐大的體制系統,其內大量官職,專歸旗人。在旗制以外的權力體制中,旗人單設科舉,單有官缺。
總之,從社會組織方式角度看,八旗體制是中國帝制時代罕見的一種特殊制度。這種制度所包含的精神有民族區隔、貴賤分等、氏族化、軍事化等多種成分。其基本含義是增強社會成員的身份區分,強化社會分層和人對于人的統治關系。這種體制隨著清軍入關而覆蓋到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之上,造成社會結構的空前復雜化和社會分層的深化。
庶民社會分層體系與保甲制的推行
清代庶民大致分四類: “凡籍有四,曰軍,曰民,曰匠,曰灶。”軍戶是從明代沿襲下來的部分衛所人口,已經萎縮,但長期保持,主要進行屯田、漕運,家口編為軍籍,但不世襲,較明代軍戶的依附性為弱。匠籍從明代繼承而來,只存在很短時間,不久融入民戶。灶戶也從明代繼承而來,并保持世代相襲身份,不準脫籍,不可流徙。
順治五年(1648),清政府下令庶民三年一次編審里甲。其法仿照明朝舊制,110戶為里,推丁多者10人為里長,其余百戶分為10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各設里甲長。但里甲制度以編審男丁為主,要點在于賦役征收。自明后期開始,賦役體系中依照人丁征收的賦稅趨于向土地歸并,在這一過程中,里甲制度的實際功用愈來愈模糊。清經數次推動里甲編審,但都沒有能夠將之建成一個覆蓋全國的有效制度體系。隨著“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制度逐漸推出,對人丁的嚴格編審也就因失去意義而被放棄。在這種情況下,保甲法成為清朝實現對基層社會普遍控制的主要制度體系。清朝歷代皇帝都積極推動保甲制度建設,推行日廣。
清入關之后就開始推行保甲法。順治元年(1644)有條例頒布:“置各州縣甲長。總甲之役,各府州縣衛所屬鄉村,十家置一甲長,百家置一總甲。凡遇盜賊逃人奸宄竊發事件,鄰佑即報知甲長,甲長報知總甲,總甲報知府州縣衛,核實申解兵部。若一家隱匿,其鄰佑九家甲長總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顯然,這種保甲制度以社會控制和治安為核心目標,同時具有賦稅征收保障作用,并體現了國家對庶民社會的嚴格掌控。
清初旗人社會并不編入保甲體系。旗人地位高于民人,同時也是皇室特別加以嚴格控制的人群。保持旗人特殊地位和旗人編制體系本身的嚴密性使得清統治者并無必要將旗人編入保甲。所有旗人及其名下依附人口,皆別有專門檔案,持續稽查、統計。隨著旗下人口日眾,居住分散,旗民界限趨于模糊,清政府在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大規模整頓保甲時,開始將與民人雜居的旗人也編入保甲。這樣,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旗人的編制體系與日益普遍化的保甲體系形成了交叉。
保甲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政府對于基層社會最為嚴密的以對人的控制和社會治安為中心目標的體制,其覆蓋的地域范圍和社會人群達到空前廣大的程度。通過這個網絡,清朝基本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日常掌控。
結語:由明入清社會等級的深化
從前述研究看,明清兩代從主流而言,社會分層結構并沒有穩定地向平面化推演,反之,社會分層體系變得更為復雜。其中,人身依附關系大幅度地強化和普遍化,社會區隔也大幅度深化。突出體現出這種變化的八旗體系,是一種國家制度,而并非僅僅構成社會慣習或者地區化的民間風俗。這就使得清代的社會分層與帝制國家上層建筑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表現出清代政治專制與社會等級深化的一致性。與此相比,明代的良賤差別,雖然也得到國家立法的支持,但并非明朝所創立,也不是明朝著力建構的社會局面。在這種意義上,清代增強了體制內身份的社會意義,擴大了社會不平等。保甲是中國帝制時代歷史上覆蓋最為廣泛、最為精密的基層社會管理制度,保障社會治安與實現人身控制功能并行。其基本對象是庶民,但在清中后期已經擴展到八旗系統的外緣人群,顯示出八旗特權身份與普通庶民身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交融。這些情況在透視15世紀以降中國社會組織方式和演變趨勢分析時,是令人沮喪的。它實際上標示出,從社會結構角度來看,在這個世界大變動的時代,中國社會體系中發生著一系列與這場變動的基本取向并不相符的事情。就中國本身而言,前述社會領域的變化,顯示出明清兩個時代之間的錯位,而不是前后相繼的對接。這種錯位,在經濟領域并不同樣明顯。這是意味深長的。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教授;摘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1期;原題為《八旗、保甲與清前期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