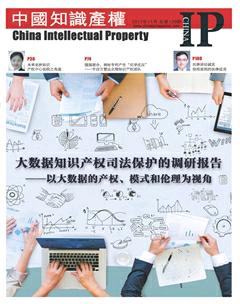淺議涉案商品真偽證明文件的證據效力
侯娟娟
關鍵詞
假冒注冊商標
被害人陳述
鑒定意見
在假冒注冊商標刑事犯罪案件的司法實踐中,通常由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機構對涉案商品是否為假冒其注冊商標的商品進行鑒定,并出具相應的證明文件。商標權利人出具的證明文件的證據屬性及證據效力在實踐中容易存在爭議和分歧。本文將結合筆者擔任被害人訴訟代理人的沈某等人假冒注冊商標罪案進行闡述。筆者認為,商標權利人對涉案商品真偽辨別而形成的相關證明文件,屬證據種類中的被害人陳述,不能以商標權利人與本案存在利害關系及不具有鑒定機構的法定鑒定資質為由,否定其證據效力。
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沈某、杜某某向周某購買假冒某知名運動品牌商標標識,組織工人生產假冒A商標的運動產品,沈某等人涉案非法經營數額共計近200萬元。2016年5月,一審法院判決沈某等四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等罪。沈某、杜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一審辯護意見以及上訴理由包括:出具鑒定意見的外國企業職工是權利人的代理人,有商業利害關系,且其不具有鑒定資質,出具的鑒定意見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應由具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鑒定涉案商品真偽。二審法院經審理后駁回沈某等人的上訴,維持了原判。
法院裁判
一審法院認為,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人對自己的注冊商標及商標標識最為熟悉,對產品的防偽秘密點最為了解,對自己的產品具有完備的鑒別能力,可以對涉案商品是否為本公司生產進行判斷。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人在證明商品真偽方面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且已提供了營業執照、商標注冊證等,加之被告人亦無相反證據予以推翻,綜合全案事實和其他證據,可以采納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人出具的被控侵權產品的鑒定意見。
筆者作為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在本案二審審理過程中提出,商標權利人就涉案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屬于被害人陳述而非鑒定意見,應采納為定案依據。二審法院最終采納了筆者的代理意見,駁回了被告人的上訴,維持了一審判決。二審法院認為,涉案商標系在中國境內依法注冊的商標,且在商標注冊有效期內。商標權利人出具的鑒定文本應屬于被害人陳述而非刑事訴訟證據中的鑒定意見,其內容為被害單位的辨認。除上述鑒定文本外,相關證人證言及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均能證實被告人生產、銷售假冒商品的事實。一審法院對涉案相關鑒定函予以采納正確,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對沈某等進行定罪處罰,定性準確。
評析
關于商標權利人就涉案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應被采納為定案證據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屢有爭議。本案一審和二審法院就相關證明文件的證據種類及其與案件的關聯性作出了分析和定性,對同類案件的處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現作如下具體分析:
一、商標權利人就涉案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屬于證據種類中的被害人陳述
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一般是指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對象。被害人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在我國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刑事犯罪罪名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及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等。該等罪名侵犯的客體為商標權利人合法的注冊商標專用權及國家商標管理秩序。商標權利人在侵犯商標權刑事犯罪案件中處于被害人地位。
在相關案件中,應公安機關的辦案要求,商標權利人需要對涉案商品進行鑒別,確實其是否為假冒其注冊商標的商品,并出具相關證明文件。這類證明文件沒有固定的稱謂。在商標侵權案件及侵犯商標權刑事犯罪案件中,出具文件的權利人或辦案單位將這類證明文件統稱為“鑒定結論”“鑒定證明”或者“鑒定意見”等。由于其稱謂上與刑訴法第48條規定的“鑒定意見”近似,因此司法實踐中存在一些混淆概念的情況。
刑事訴訟證據中的“鑒定意見”,是指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由國家認可的、有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對案件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檢驗、鑒別所形成的意見。所謂被害人陳述,是指被害人就其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事實以及有關犯罪分子的情況向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商標權利人出具的證明文件,無論其名稱如何,其內容為被害人對案件有關事實的說明,符合被害人陳述這一證據形式的特征,其并非法定鑒定機構就與案件有關的專業性問題提供的意見和結論,不符合鑒定意見這一證據的特征。因此,商標權利人出具的證明文件不存在不具備鑒定資質或因存在利害關系而影響證明力的問題。
二、商標權利人就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的證據效力有充分法律依據
首先,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人就涉案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刑法第213條關于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罪狀描述為“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行為”。行為人使用商標的行為是否經過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需要由商標權利人或其委托人作出判斷,其他任何鑒定機構均無法對其作出權威判斷。商標是區分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權利人對自己的注冊商標及商品具有不為他人所知悉的防偽技術或者特殊的鑒別方法,屬于權利人的商業秘密,其他任何司法鑒定機構無法悉數掌握商品真偽的鑒別方法,實踐中也沒有這類鑒定機構。因此,商標權利人就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最具有權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其次,相關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亦確認了商標權利人及其委托人就涉案商品真偽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具有證據效力。1997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于鑒定使用注冊商標的商品真偽問題的批復》明確,“使用注冊商標的商品真偽,應由該注冊商標的合法使用人或者法定檢驗機構鑒定。在雙方鑒定結論不一致的情況下,如果注冊商標合法使用人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其結論是真實合法的,則應以注冊商標合法使用人的鑒定結論為準”。2008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關于商標權利人授權他人鑒定注冊商標真偽問題的批復》提到,“商標注冊人依法委托他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投訴商標侵權案件,并且明確授權被授權人可對注冊商標是商品真偽進行鑒定的,商標注冊人和被授權人須對被授權人的書面鑒定意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被鑒定者對該鑒定意見沒有異議或雖有異議但無正當理由不提供其商品系真品的證據或者取得該證據的線索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將該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予以采信”。本案中商標權利人的代理人就涉案商品出具的真偽證明文件與該案其他證據能相互印證、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應予以采信。
有觀點認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的相關規定不應在刑事案件中適用,理由是該相關規定僅適用于認定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不能適用于認定假冒注冊商標的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此處并非主張適用商標局的相關規定認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僅針對涉案商品是否為假冒商品這一客觀事實的認定。無論是認定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認定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刑事責任,都首先要解決“涉案商品是否為假冒”的問題。如涉案商品被認定為假冒,即可發生行為人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如果假冒商品金額進一步達到法定標準,行為人即可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而認定“涉案商品是否假冒”的標準和依據,包括是否采納商標權利人的真偽證明文件,在商標民事責任、商標行政責任及侵犯商標權刑事犯罪的認定中,應當是一致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