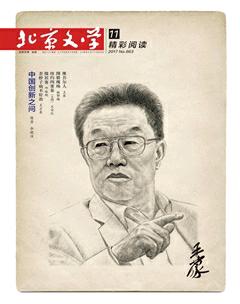誰是獵手?
劉瓊
我相信趣味有時是本能。比如,某年在上海開青創會,主辦方把上海作協簽約以及客居上海的青年作家那兩年出版的小說,滿滿當當地鋪陳了幾長桌。鬼使神差,我挑了一本姚鄂梅的《西門坡》。姚鄂梅那次有沒有到會完全不記得了,實際上此后也從未見過真人,但這個名字和她的文字在我的記憶里保留了清晰的痕跡。
一段時間以來,我都認為姚鄂梅是個狠角色,這當然指的是書寫狀態的她。不過,生活中的湖北姑娘通常也是狠角色,這是閑話,不敘。為什么會有這種印象?跟姚鄂梅的文字風格和美學趣味有關。姚鄂梅的文字從一開始,就顯得比同期作家成熟、老到和硬朗。支撐文字的成熟、老到和硬朗,是書寫者的閱歷、經驗和價值觀。我們的日常生命包括悲和喜,悲或喜有時袒露在眼前,有時被瑣碎的生活層層遮蔽。當大家還停留在抒情和幻想的表層,姚鄂梅已經把筆觸直接插向了眼前的生活現實,甚至插到了痛點。文字與現實之間有緊張感、有怒氣,甚至有殺氣,從概率看,這是姚鄂梅的趣味,也是她的異樣。這個痛點的觸及,通常讓我們不適、心顫、不快,乃至不忍卒讀。這部中篇小說《圍獵現場》同樣如此,或者更甚。
關于圍獵,想起了好萊塢電影《饑餓游戲》。這部電影是影中影,在收視率大棒指揮下,電視臺處心積慮招募了一群人參與到生存游戲中并進行現場直播:原本沒有利害關系的人群,封閉在生存資源有限的空間后,表現出其動物性的一面,為了獲得生存權利,爭搶、背叛、殺戮,等等,各種“動物潛質”被誘發和放大。觀眾直接看到的是電視臺制造的一個殘酷的圍獵現場,弱者和較弱者不斷被同類殺死,人性不自覺地被繳械、泯滅。由此引起人們對人性和動物性的界限、文明和生存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思考。間接看到的是另一幕,電視臺在收視率利益誘惑下,擅自踐踏他人的生命,無視文化倫理,貪婪、冷酷,令人厭惡。
文明的發展,到底是以人性的完善為追求,還是以各種數字為目標?這個問題恐怕是近年來包括好萊塢大片在內的一個問題焦點。
按照達爾文進化理論,人是比動物高級的高等動物,人性和動物性的差別很多,比如舐犢之情。“虎毒不食子”這句諺語甚至將舐犢之情由人性擴大到動物性。在《圍獵現場》里,面對蔓蔓這個智商檢測略低的女兒,父親與母親離婚后再無蹤影,母親再婚生子后將女兒寄養在鄉下老家,聯絡逐日減少,以致女兒被騙同居后生下孩子。這是父母。更有甚者,親舅舅為了多得回遷房,竟然做局誘導幼稚簡單的侄女與人同居、懷孕、生子,又瞞著侄女將孩子作為自己的養子申請要房,計謀得逞后不僅獨自霸占補償房屋,還將孩子遺棄。舐犢之情焉在?這些在利益誘惑下發生的行為,完全喪失了人倫常情,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也超出了小說中人物的承受力。姚鄂梅狠在哪里?狠在她看到了利欲熏心后人性的喪失,并用文字形象地表現出來。
看看這段結尾——
“直到半夜,舅舅推門進來,蔓蔓還站在那里,電視里重播著他白天看過的節目,不禁笑了一聲:你也喜歡看這節目了?
坐下之后,舅舅似乎覺得哪里不對勁,回頭一看,不禁一聲驚呼:你頭發怎么了?
蔓蔓頭上像被撒了一層白粉似的,從額頭和兩鬢開始,均勻地向后緩緩推進,只有后腦勺和發梢暫時還黑著。
舅舅站起來,摸了摸她新白的頭發,僵粗如鋼絲。摸到腦后時,蔓蔓猛地抬起手,擋開了舅舅。
我明白了!
什么?舅舅屏住呼吸,盯著她問。
合同,還有小慶。
話音剛落,舅舅看到她余下的黑發瞬間變白。”
知道親舅舅才是那個老謀深算的獵手的獵手,絕望和悲傷之極,蔓蔓瞬間白了頭。瞬間白頭雖然夸張,但我們能接受,因為情境真實。絕望在于無路可走,悲傷在于最后一點虛妄的親情也被粉粹。小說是一點一點地鋪出了這條絕望的路。小說沒有一句煽情的議論,而不是情緒自己跳出來演講——這也是我最欣賞的地方,完全用敘事作為動力推動情節發展,展現人物命運。小說在開頭甚至是暖調子,蔓蔓和母親在快餐店吃石鍋拌飯,談論學習和求職。蔓蔓原本是家境不錯、父母雙全、被疼愛的女孩,自從智商被測后,父母離異,被一點一點地離棄、一點一點地推到絕路。蔓蔓自以為抓住的男人安慶是舅舅設的人肉陷阱,自以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舅舅,是那個扣準扳機的獵手。這種殘酷無情的圍獵陷阱,即便是智商和情商正常的少女也很難逃脫,更何況“獵物”本身是一個稍顯弱智的女孩。小說邏輯嚴密可信,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描寫是真實的,中國社會城鎮化發展中的拆遷和居民的經濟關系、教育和職業發展的緊密關系,都獲得了充分的描寫。其中,前者是隱在背后對蔓蔓實行圍追堵截的動力,后者是活躍在前臺撕扯蔓蔓和母親行為的動機,它們都是獵手。
存在主義哲學的邏輯是“存在即合理”,但從人類學的邏輯看,存在在此不僅不合理,而且有罪。對于幼小生命的傷害,對于弱勢人群的歧視,這是我們這個社會迄今還存在的社會弊病。蔓蔓單純、幼稚、樂觀,對于自身困境一直在努力改善,這樣一個具有善意、對生活并無怨言的“雨人”,理應得到更多的體諒和幫助,但卻被身邊最親的人拋棄、最信任的人從身到心徹底地毀滅。反而是街頭的浪子,還流露出善意,并略施援手。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險惡,也看到了人性的復雜,同時也看到了文字背后的姚鄂梅的好惡。作為一個直面現實的女作家,姚鄂梅閱歷的不只是糖水,還有灰燼,還有糖水中的灰燼、灰燼中的糖水。當然,如果糖水再多一點,我會更喜歡。
責任編輯 師力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