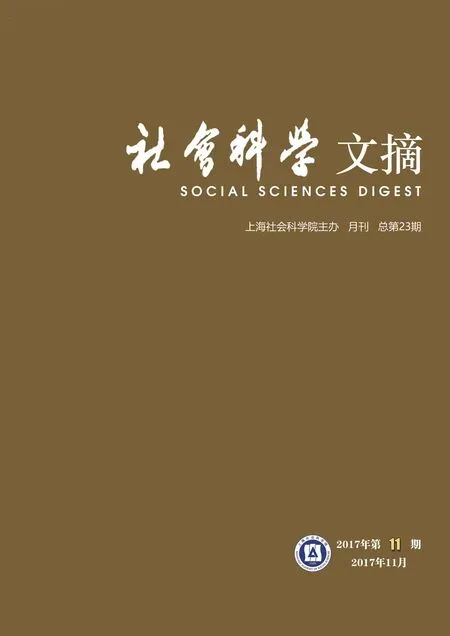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軸心時代”的概念與中國哲學的誕生
文/張汝倫
如何理解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概念?
雖然“軸心時代”的概念是雅斯貝爾斯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但相關的思想,即在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這段時間里,在歐亞大陸幾個主要的文明中心,平行發生了劇烈的思想和文化變革,可以追溯到18世紀。啟蒙時代法國伊朗學家Abraham-Hyacinth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早在1771年就看到,在瑣羅亞斯德、孔子、老子、佛陀、以色列的先知和希臘哲學家之間存在共時性,講到這個時代的普遍特征是:人類的一次大革命。而雅斯貝爾斯自己在著作中則提到拉索爾克斯和維克多·馮·施特勞斯是他的先驅(這兩人都是19世紀的德國學者),說他們已經討論了軸心時代的一些事實。雅斯貝爾斯也提到阿爾弗雷德·韋伯已“證明在歐亞大陸存在著真正的一致性”。其實,韋伯并未將歐亞大陸看作一個板塊,他注意的是不同的文化區。
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思想初看似乎與韋伯的論述頗為相似,實質很不一樣。與他的先驅相比,他對軸心時代的闡述不僅最為充分,而且也最具哲學意味。他是從歷史哲學,而不是從歷史學或歷史社會學的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軸心時代的特征是人自覺地從時間和宇宙論上反思他們自己之所在,試圖從這些反思的觀點形成自己的存在,在此意義上,軸心時代構成了歷史的起源。這無疑是一個思辨哲學的思想。
但“軸心時代”的概念之提出,卻是有明顯的時代背景的,即納粹德國的噩夢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歐洲文明的崩潰。建立在傳統歐洲人世界觀基礎上的世界歷史的統一不復存在。雅斯貝爾斯早年即已看到現代世界中人自身的分裂。在早期代表作《世界觀的心理學》中,他描述了隱藏在各種世界觀表現后面的種種靈魂沖動,它們一刻也不得安寧。
在寫《世界觀的心理學》時,雅斯貝爾斯關心的主要是現代世界個人的生存;但《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的命運。痛感于人類的分裂造成的不幸,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這樣的浩劫,雅斯貝爾斯希望通過證明“軸心時代”及其產生的普遍性真理來證明人類歷史的根本統一。但是,這種想法隱含一個極成問題的預設,即多樣性產生對立和分裂,只有普遍性(當然是多樣性的統一)才是人類永久和平的保證。我們在討論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概念時,這個預設以及雅斯貝爾斯提出此概念的政治歷史背景,是不能忽視的。
但是,當代討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之意義的學者,往往忽略他提出這個思想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語境,而抽象地把“軸心時代”或“軸心突破”的要義概括為人類達到較高層面的反思性,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主動性、歷史性和責任性。不過,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樣的轉變也可以在不同于原始軸心時代的語境和環境中發生。軸心時代的概念強調軸心時代才是歷史的開始,很容易被進化論意義上的進步敘事所接受。
此外,雖然雅斯貝爾斯聲稱軸心時代作為一個事實情況是可以在經驗上發現的,但他關于與軸心時代有關的一些經驗陳述根據現在我們已有的知識,不再站得住腳。實際上“軸心時代”并非一個純粹史學的概念,而是一個滲透著雅斯貝爾斯政治理想的歷史哲學概念,因此,如果有誰把它當作一個像“中古時代”或“啟蒙時代”這樣的客觀歷史概念來使用的話,其正當性是有問題的。正如史華慈后來所說的,“‘軸心時代’的觀念”充其量“應該被當作一個啟發性觀念來對待”。
內向超越是中國哲學突破的一個主要標志
從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至今,已近70年。西方人對自己歷史和歷史觀的反思,也有了很大發展,因而對雅斯貝爾斯本質上罔顧文化的多樣性而求人類文化的統一性的軸心時代概念有所批判。人們發現,雖然雅斯貝爾斯拒絕“歐洲的傲慢”,但他還是用一個統一的理性尺度來評價所有的文化與社會。他認為,在軸心時代,各個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反思階段。但今天的人們已經不能接受這樣犧牲多樣性而得來的普遍性,不能接受一個沒有多樣傳統的抽象人類。
雅斯貝爾斯之后,沃格林(他曾師從雅斯貝爾斯和阿爾弗雷德·韋伯)和艾森斯塔特進一步發展了有關軸心時代的假設。沃格林是哲學家,他基本還是從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的角度討論“軸心突破”,而艾森斯塔特則是一個歷史社會學家,他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重構了軸心時代的概念,用來進行比較文明史和比較世界史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軸心時代”的概念正是由于他的工作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假設多少還有西方中心論的痕跡;而艾森斯塔特卻是要用軸心時代的概念來批判主流的現代化理論,論證他的多元現代性構想。
艾森斯塔特對“軸心突破”的理解與雅斯貝爾斯的理解有明顯的不同,他是從社會秩序的維持與轉變的動力之間的互動關系來理解“軸心突破”的。在他看來,軸心突破是“超越秩序與世俗秩序之間基本緊張的出現、觀念化和制度化”。對于人類歷史經驗來說,秩序,而不是反思才是最要緊的。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只是秩序的兩個維度或兩個層面,并不相當于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區分。向某種超越的突破不一定意味著世界觀的完全改變,可以只是在社會的某個特殊維度上發生了部分變化。
無論是艾森斯塔特還是雅斯貝爾斯,不管他們各自的“軸心時代”的概念有多么不同,都只是理論假設,而不是事實性的概念。并且,他們的假設都是以希臘和猶太文明為軸心標準,艾森斯塔特的超越與世俗的區分也是與這個背景相關才得以提出,無法不證自明地用于其他文明的語境。軸心時代以這兩個文明的現象為基礎劃線,是成問題的。
然而,在許多華人學者那里,“軸心時代”幾乎成了一個事實性而不是解釋性的概念。“軸心時代”好像和新石器時代一樣,是一個人類文明普遍客觀存在的時代。一些華人學者在討論中國哲學的起源時,正是這樣來使用這個概念的,例如余英時在著作《論天人之際》中就是這么做的。雖然他承認“軸心說”是“歷史假設”,但是仍堅持認為中國也有軸心突破或哲學突破,他要“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即先秦諸子)的起源”。
當然,雖然余英時在上述著作中講“軸心文明”時也提到了艾森斯塔特,甚至還有聞一多,但我相信他有關“軸心突破”的思想應該直接來自史華慈,而不是雅斯貝爾斯或艾森斯塔特。1978年,美國學術雜志Daedalus出版了一期討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專號“智慧、啟示和懷疑:透視公元前1000年”(1978年春季號)。史華慈在這期專號上發表了《超越的時代》和《古代中國的超越》兩篇文章。
史華慈并不反對軸心突破的說法,但他寧可用“超越的時代”來替換“軸心時代”,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名稱替換,而是反映了他對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那個軸心時代(公元前七八百年)的理解。與雅斯貝爾斯相比,史華慈更注重各文明之間的差異,“但是,在所有這些‘軸心’運動中有某種共同的基礎性沖動的話,可把它稱為超越的傾向(the strain toward transcendence)”。這就是他寧可把“軸心時代”稱為“超越的時代”的理由。
史華慈說,他是在比較接近“ 超越”(transcendence)這個詞的詞源學意義使用這個詞的,即超越是一種“退后”和“看出去”(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是“一種對現實的批判與反思的質疑,以及對彼岸世界(what lies beyond)的一種新的看法”。史華慈對“超越”的這個定義十分精煉。在史華慈這里,超越并沒有特殊的宗教意義,它只是指較一般意義的脫離和超出現存的界限,看到“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它是質疑和超出自己的現實狀況,從而開啟了充分認識他者的可能性。
史華慈認為,孔子在內部尋求仁的根源,在外面尋求規范秩序;老子著作努力追求無名之道,就象征這種超越。史華慈用“超越的時代”來代替“軸心時代”,可能是他認為“軸心時代”的概念很難體現思想的延續。超越的時代雖然也是突破,但卻并非是與之前的傳統斷裂。他明確指出:“在中國和印度,超越的運動是在多少統一的共同文化的架構中發生的。”在《詩經》和《尚書》中已經有超越的因素了,孔子所做的是把他自己的某些東西帶進對道的理解中。這就是關注道德-精神生活內在方面的主體性。人能培養他們內在的道德成長的能力,能達到內在的道德完滿,這種道德完滿就叫做“仁”。歸根結底,社會的道德根源是人的主體。史華慈把這種轉向倫理的內在根源叫作“內向超越”(transcendence inward)。他認為正是在這點上,孔子堪比蘇格拉底。
然而,就像蘇格拉底從未否定過非人的神一樣,孔子也從未否認人之外超越的天。天不僅是自然與社會內在的道,而且也是一種超越的自覺意志。孔子講的道不僅是社會與宇宙的客觀結構,也是仁人“內在之道”。道家的哲學就超越而言遠比儒家激進。“道可道,非常道”,意味著道的終極本質是不可描狀、不可言喻的絕對,是人類語言范疇無法接近的。如果說道家哲學也是突破的話,那么它是突破到神秘主義。按照史華慈的上述解釋,孔子的突破是“內向”超越,即要在自身內在找到道德的根源;而道教的突破是“向外超越”,它是要超越向一個自身之外的道。也就是說,中國先秦時代的超越有兩個相反的方向,孔子向內,道家向外。
余英時更多是在史華慈講的超越意義上來用“超越”一詞的,即超越主要是指對現實世界有一種批判性、反思性的質疑,和對于彼岸世界(what lies beyond,余譯為“超乎現實世界以上的領域”)有一種新的看法。他論證儒家、墨家、道家的突破主要論據就是他們都對禮樂傳統有不滿和批評,乃至否定(道家)。然而,他又認為:“孔子時代中國哲學突破的一個主要面向,那就是現實世界與超越世界之間的關系在概念上的不斷變遷和流動。”可是,從現實世界和超越世界有了區分之后,這兩者的關系就一直在不斷變遷和流動。余英時在這里顯然要說的是孔子時代達到的“內向超越”。
如果這樣的話,那么“內向超越”就是中國哲學突破的一個主要標志。但問題是:突破是否就是開始?我們在此關心的不是“突破”,而是“開始”。余英時認為:“軸心突破的一個重要前提便是‘初次有了哲學家’。”“這是中國軸心突破的展現,也是中國哲學性思維的全面而有系統的發端。”這個說法能否成立,牽涉到對“哲學思維”本身的理解問題。
何為中國哲學的開端?
在我們日常與世界上的事物打交道時,總會發現,我們已經處于一個大的語境中,它決定我們與這些事物可能的關系方式。我們總是已經知道意義和目的,在我們研究世界的種種關系時,總是先受已接受的觀念的引導。靠著它們,我們才能確定遇到的種種可能性。連續性和整體性就是這樣的觀念。我們尋求連續和整體不是經驗的結果,因為經驗本身只有在連續和整體的意義上才可能。然而,如果我們試圖從理論上獲得所有可得到的經驗的一幅統一的畫面時,我們發現,現有的各種特殊知識辦不到。相反,新的經驗在任何時候都能證明理論是不完全的,因為作為我們探究之前提和經驗可能性之條件的連續性和整體性,是永遠無法在日常經驗中出現的。如果我們把可能經驗的全體叫“世界”,那么很顯然,這個世界不可能是經驗的對象,因而也不是我們科學研究的對象。它是主客體的統一,我們經驗的統一,因為我們自己也包括在這個世界中。這個世界,就是大全。
這并不意味著大全排斥知識,“因為我們可能取得的知識決不因我們體會了大全而被取消,相反,這種知識由于被相對化了就能被我們從一種新的深度出發來把握;因為它這個無邊無際的認識活動此時被我放進了這樣的一個空間,這個空間雖不能被認知,卻顯現為一種好像在透視著一切被認知的存在的東西”。哲學之所以是人類自由的產物,是自由的標志,因為它是一種超越,即超越我們的實存,而躍向我們的可能性。“超越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對一切實存的突破。”即超越我們的日常存在,而去思考和把握大全,或者自覺把自己置于大全中來思考。這時哲學就產生了,這才是起始意義上的哲學的突破。
對于大全的上述意義,中國古人也早有深切的認識。中國人把西人所謂“大全”稱為“道術”。《莊子·天下篇》開門見山,直指事物本質問道:“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答曰:“無乎不在。”“無乎不在”者,大全也。亂世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大全被一偏之見、一得之察所替代:“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天下篇》的作者因而悲嘆:“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看到,《天下篇》的作者是主張道術之整全,反對“道術為天下裂”的。然而,在余英時看來,剛好相反,莊子恰恰主張道術裂的。為什么?因為“‘breakthrough’和‘裂’好像是天造地設的兩個相對應的字。”因為他要證明:“中國古代的‘道術為天下裂’和西方現代的‘軸心突破’是兩個異名同實的概念,在比較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研究上恰好可以交互闡釋。”他并因此斷定:“莊子不但是中國軸心時代的開創者之一,參與了那場提升精神的大躍動,而且當時便抓住了軸心突破的歷史意義。”
不得不說,這是余英時的過度詮釋。《莊子》的問題語境和雅斯貝爾斯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是完全不同的,莊子根本反對“道術為天下裂”,《應帝王》中“中央之帝被日鑿一竅,七日而死”的寓言更是表明:對莊子來說,“道術為天下裂”的后果就是道術的死亡,就是天下無道。
退一步說,即便如此,也不能說莊子是中國軸心時代的開創者,因為“萬物為一”的思想,早在“軸心突破”的概念提出之前中國就有了,又何必要用“軸心突破”來為它正名呢?如果以明確思維大全(中國的叫法是“道”或“天地之道”)為哲學的開端的話,那么中國哲學顯然不是始于孔孟老莊。從現有流傳下來的古代文獻看,也許《尚書·洪范》和《周易》的出現就可以看作是中國哲學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