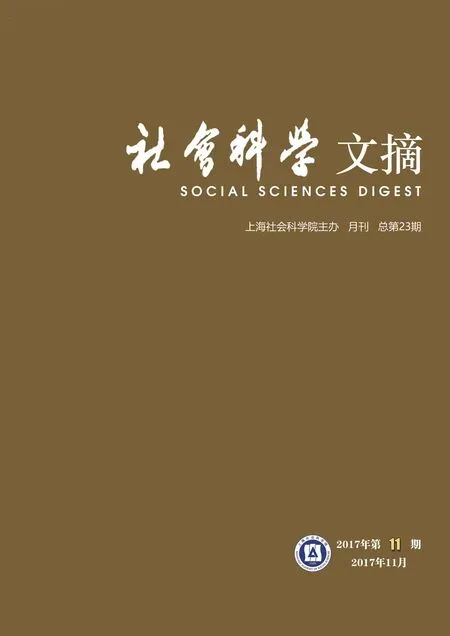論知識民主的進路
文/田甲樂
知識與民主的關系,一直以來是哲學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柏拉圖提出了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知識與意見的區分,認為知識是真理的王國,開啟了知識與民主互相分離的道路。近代科學革命的誕生,使得客觀話語修辭下的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成為知識的來源,加強了人們關于知識和民主無關的信念。但是,長期以來,知識往往和權力相伴隨。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應該成為國王。近代科學誕生之后,掌握科學知識的科學家開始獲得政府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學家在政府中任職的人數迅速增加。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知識滲透到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為公共決策的基礎。對知識生產和應用的掌握程度成為對權力掌握程度的基礎,知識民主成為哲學關注的新焦點之一。本文目的在于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角度闡明知識民主的發展進路。
從知識的客觀性到情境依賴性
知識的本質從客觀性走向情境依賴性,是知識民主在本體論上的發展進路。
知識起源于人類生存的需要和對確定性的追求。在生物進化過程中,人類一方面面臨生存壓力,需要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總結關于自然的知識,比如,如何生火和運輸、動植物的習性;另一方面面臨精神壓力,認為只有認識和理解的自然界才具有秩序和安全性。前者是知識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原因,各文明古國都出現該種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它的出現和進步速度與人類經驗的擴展是分不開的,與一個領域的復雜程度并沒有必然關系,而和該領域對人們生活影響的重要程度以及相關的經驗積累有關;后者是知識具有無用性、滿足人們好奇心的起源,各民族都出現了該種意義上的神話知識,它也是古希臘科學思辨和理性精神的起源,其目的在于認識世界的本源,為人類認識和理解自然提供解釋和辯護。
該時期的知識生產需要人們討論和磋商,是一個自由表達和討論、集體決策的民主過程。即使在古希臘,對理念世界和真理王國的追尋,也是一個允許和鼓勵辯論,不同觀點之間的磋商和說服的過程。古希臘一些思想家對知識生產中民主的反對,反對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而不是民主本身。古希臘的知識生產是一種崇尚和運用民主的過程。到中古世紀,基督教思想適應了人們需要,取代眾多的其他宗教而得到快速發展,基督教學者成為知識生產的主體。基督教思想雖然不允許懷疑上帝的意志,但是在對上帝和古典文獻的認知中,鼓勵理性討論,大大減少了很多宗教中的神秘主義。因此,基督教思想下的知識生產,是在上帝指導下的民主討論過程。
文藝復興給哲學、藝術、文學和科學領域帶來了思想大解放,人文主義逐漸代替基督教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實驗和理性完美結合,誕生了近代科學,科學方法代替哲學和神學方法,成為知識確定性的來源,科學知識開始被認為優于其他知識,逐漸成為知識和真理的代名詞。科學試圖建構一種超越繁瑣無效的理論爭論、憑借特定研究程序就能夠真實地反映大自然的研究方法,科學知識開始呈現客觀性的特征。科學和人文領域的界限逐漸明顯,民主開始被驅逐出科學知識生產領域。但是,科學仍然對公眾非常感興趣,科學家的私人收藏仍然對公眾開放,科學家仍然樂意通過公開實驗向公眾展示科學知識,同行和公眾的見證是科學知識權威性的來源。
啟蒙運動使科學精神開始成為社會中人們普遍承認和追尋的精神氣質,科學知識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有力工具,科學知識的實用性與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很快結合到一起,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得到凸顯和強調,科學知識生產模式成為知識生產的典范,科學方法逐漸侵占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科學知識逐漸被認為具有絕對客觀性特征,成為政府公共決策的主要依據,該時期科學知識向公眾的開放、公共決策中舉行的聽證會,是科學知識自信的表現,而不是讓公眾參與知識生產和決策,公眾磋商和民主討論完全被拒斥到科學知識生產和應用之外。
隨著科學知識對其他學科和社會領域的深入入侵,以及科學知識社會應用負面效果的出現,科學知識生產方法和方式的客觀性成為科學家和哲學家反思的對象。人們開始認為,分析命題與經驗命題之間不存在絕對的界限,觀察滲透理論,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并不能單獨決定科學,尤其在科學革命時期,相信不同范式的科學家之間的概念網絡、感官經驗和世界觀、對自然和以往成就的解釋是不同的,包括個人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內的常規科學之外的價值標準參與和決定了學派之間的競爭,成為隨后常規科學時期科學知識生產中的形而上學信念。科學知識生產的基礎(觀察經驗和范式)的絕對客觀性受到了挑戰,這為民主進入科學知識生產過程打開了大門。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不僅在科學革命時期,而且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知識也不是由科學經驗本身所決定的,而是由科學經驗和實驗者先前的信念所共同決定的;科學概念和術語的意義是開放的、動態的、不斷進行修正的、相互聯系的,人類的實踐活動、社會經驗和利益因素滲透到科學知識生產當中;科學知識生產中涉及到的所有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都是處于同一個網絡中的彼此具有能動關系的行動者,他們不僅承載一定的信息,而且轉換、轉譯、扭曲和修飾所承載的信息,使其所表示的涵義和發生的作用隨著時空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是信息的生成者和建構者,影響著網絡最終建構出的結果。科學知識生產過程和應用決策具有不確定性和情境依賴性,需要進行磋商討論,成為一種民主過程。
從知識的主客二分到主體間性
知識生產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從主客對立走向主體間性,是知識民主的認識論進路。
古代在對知識的研究過程中,世界被分為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上帝之城和塵世之城,對知識的研究主要是把握世界的本源和存在、尋找確定性,研究的重點在本體論。到了近代,人們發現,在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對人的認識進行研究,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主流,主要有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個進路,前者強調理性演繹是獲得知識的可靠途徑,后者認為經驗歸納是獲得知識的可靠途徑。兩者都有很多學者的追捧,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主體和客體二元分立正式確定下來,自然和人都成為一個可以被還原的機械的物理世界。從哥白尼天文學革命到牛頓力學,確立了自然存在和萬物運行的秩序,知識成為一種先天存在的等待人類發現的真理,主體和客體二元分立的知識生產方法受到推崇;達爾文進化論證明了人與動物的連續性、動物與自然的連續性,人的神圣性被去除,成為一種遵循自然規律進化而來的存在,人的認識能力成為一種通過適者生存進化而來的一種機械能力,主體和客體二元分立的觀念得到科學知識的支持。主客和客體二元分立的知識生產方法伴隨著機械論思維,主體遵循先驗理性或后驗經驗,通過科學方法,獲得先驗存在的客觀知識,在這個過程中,主體間的磋商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被認可的,民主被排除在知識生產之外。
主客二分的知識生產方法使得科學知識獲得了顯著進步,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物質財富,推動了社會快速發展。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納粹主義使得西方社會陷入科學危機、文化危機和人性危機當中,其根源看似是理性本質存在缺陷,但是起源于古希臘的理性本身對確定性和秩序的邏輯推理并沒有問題,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對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專注,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使得知識成為一種對客觀自然規律的鏡像式反應和表征,知識生產成為個體對自然的發現,然后在人群中進行傳播,知識生產具有了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這有悖于知識在古代起源時對人類生存需要和確定性的追求,人類的需要被個體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所代替。知識生產無法獲得公共性,排除了彼此之間的磋商和民主討論。在社會危機和學術反思的情況下,主客二分的思維的方式受到了質疑,主體之間的關系成為認識論中的重要問題,這為知識生產中的民主打開了大門。
在認識論意義上,康德在18世紀就提出了主體之間的關系,但是在知識生產意義上,康德關于主體之間關系的研究仍然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礎之上的,是要求個體進行知識生產時,做到知識的普遍化。這種主體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客觀性基礎之上和在個體主義掩蓋下的主體間性,是上述西方社會危機的根源,是被反思的對象。真正具有主體之間交互意義上的主體間性,首先是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意義上使用,指依循倫理道德在主體之間發生的主體間關系;胡塞爾在認識論意義上強調了在對世界認識過程中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海德格爾、許茨、梅洛-龐蒂、薩特、伽達默爾、哈貝馬斯都在主體交流意義上強調了主體之間的交互。個體的認知框架和能力是在相互交往活動中形成的,認知過程是在互相磋商中形成的,認識結果是磋商之后共同意識的產物。主體存在于主體間性之中,知識是主體間相互作用的產物。
科學知識生產,作為近代以來最強調發現優先性的研究活動,個體在知識生產中的地位得到了充分強調,但是20世紀中期以來也受到主體間性思潮的影響。隨著科學知識的絕對客觀性受到質疑,科學知識生產中充滿利益和權力等社會因素,主體間性成為科學知識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依據;隨著大科學的出現和國家創新系統的發展,個體科學家之間的知識不再像之前一樣能夠自動整合成完整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從個體轉向了集體,主體間性成為科學知識生產順利進行的保證。主體間性放棄了傳統認識論中的主體和客體二元分立的思維形式,轉向在主體間性中尋找知識生產的途徑,知識的觀念從對世界的表征走向對人與人、人與非人、自然與社會的建構,知識生產強調其過程中社會和主體交往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主體間性突出了對知識生產主體公共生活和共識的關注,共識是個體認識的組成要素,是不同個體的公共部分,隨著個體認知和知識的變化而變化。個體的主張表達、彼此之間的磋商和共識形成成為知識生產中的存在,民主成為知識生產中認識論發展的需要。
從知識的價值中立性到知識與秩序的共生
在知識生產和應用中,從知識的價值中立性到知識與秩序的共生,是知識民主的實踐論進路。
在近代科學的發展中,科學理性被認為是一種工具理性,科學知識被認為具有價值中立性,是關于客觀規律的發現,與知識生產主體的價值判斷無關,即使是與道德和價值判斷密切相關的倫理學也被認為具有價值中立性,知識生產者的價值和情感被排除到知識之外。由此導致的是專家治國論的觀念,強調社會治理和公共決策中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認為科學知識是中立的,只有掌握科學知識的專家才能做出合理的決策,并且這種決策因基于科學知識而具有中立性;如果決策導致了對人類有負面影響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那是由科學知識自身發展邏輯所無法避免的或者是一種意外。知識的生產和應用被認為是價值中立的,個體成員之間的磋商是多余的,甚至有害于客觀知識的生產和合理決策的制定,民主被排除在外。
隨著環境問題的凸顯和科技引起的災難的頻發,以科學知識為代表的價值中立觀念受到了質疑。事實上,知識的價值中立性有兩種含義:第一,對“人類”而言的價值中立,指科學知識對于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價值是等同的,撇開其他物種不談,它可以理解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能決定給人來帶來好處和壞處,對人類的不同發展方向是價值等同的;第二,對個人而言的價值中立,指科學知識是面對事物本身得出的研究結論,研究者不做評斷,它是大自然呈現給人類的,是由不依賴于個體研究者的客觀科學事實所構成的,對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等同的。20世紀的科學知識取得的巨大進步對人類發展方向有潛在的重要影響,科學知識不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對人類的發展具有指向性,第一種價值中立性含義已經不能成立。第二種價值中立性含義依賴于傳統科學體制下科學家的無私利性和有組織的懷疑精神,科學家在研究中能夠消除個人偏見、保持對科學經驗和科學方法的忠誠,面對研究客體本身進行客觀研究,實現科學知識的價值中立性。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知識生產與應用之間的關系逐漸由之前間接的不緊密的關系走向直接緊密的關系,知識生產者對資本和權力的支持與依賴日益增加,在研究中無法再保持置身于利益之外,第二種價值中立性也已經不能成立。知識價值中立性觀念的破滅表明知識負載著價值,是一個滲透著情感和利益的領域,需要通過民主才能達到具有公正價值的知識生產和應用。
以科學知識為代表的知識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與社會秩序共生,一方面社會秩序影響了科學知識的發展,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塑造了社會秩序。近代科學在英格蘭的誕生離不開清教倫理價值觀的支持,清教徒中很大一部分是社會地位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和商人,他們由于自己社會地位正在提高而持有一種科學也是進步的觀念,認為科學會增強自己的地位和勢力從而支持科學發展。清教徒和資產階級對科學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文化支持,把科學納入到他們反對既有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秩序、建立新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秩序的努力當中。現代科學知識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社會秩序的調整速度,沖擊和重構著倫理、法律和經濟等社會秩序。科學研究受到了倫理和法律等社會秩序的約束,同時也通過倫理和法律在重構著全球社會秩序。科學研究領域的擴大重新界定著專利的涵義和可申請專利的范圍、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發明之物和自然產品的界限,重塑著經濟法律和規則,重構了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及其競爭能力。知識與秩序的共生,使得知識成為社會秩序建構的基礎,平等公正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知識的平等,這使得知識生產和應用中需要不同主體的磋商。知識民主成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基礎,成為和諧社會秩序建構的關鍵。
結論
知識的情境依賴性揭示了知識的社會性和地方性特征,使得科學知識的權威性和神圣性降低,地方知識、人文學科知識和公眾日常經驗知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得到重視,需要通過民主來克服知識生產中利益的分歧和保證知識的可信性;知識的主體間性揭示了知識生產是一種建構而不是對自然的鏡像式的反應,有必要擴大知識生產的主體,通過民主來保證知識能夠代表多數人的利益;知識與秩序的共生使得知識生產和應用中蘊含的權力更加明確的暴露出來,需要通過民主來克服權力的濫用和保證公平社會秩序的建構。知識民主是知識自身邏輯演進的結果,是知識在適應社會中演進出的新的生產和應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