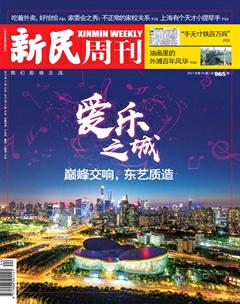讓老建筑“留”住歷史文脈
姜浩峰

城市發展過程中,對老建筑、老的城市空間加以改造,那是必然的。然而,這樣的改造不能破壞了城市的歷史記憶,更不能對建筑本身做出破壞性的“改造”。
上海九江路501號,現名“德必外灘”。1914年落成之際,它是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一百多年來,見證了九江路這一東方華爾街的興衰。如今,在這百年老建筑里,能看到的竟然是室內的“一絲絲垂楊線,一丟丟榆莢錢”的感覺。當然,這只是一種感覺,實際上,室內樓板、墻壁上種植的綠樹芳花中,并沒有楊樹、榆樹,都是設計師精心挑選的適合此地生長、修剪的植物。
這一設計,出自意大利建筑師斯坦法諾·博埃里的手筆。在改造九江路501號的時候,博埃里采用了米蘭“垂直的森林”項目的靈感。“‘垂直的森林與‘德必外灘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新造建筑,而后者,是對老建筑的改造。” 博埃里告訴《新民周刊》記者,“改造老建筑,首先就要尊重老建筑。”在不破壞九江路501號老建筑外形、外貌的情況下,對內在格局進行重新打造,讓老建筑的空間為今所用。
與九江路501號不同,這幾年,上海先后出現過幾起破壞老建筑的事件,若深究這些破壞者的根本心,其中有一部分人恰恰是出于保護,或者說使得建筑更美觀的目的。2015年6月,廣東路94號到102號原三菱洋行大樓曝出被人“刷臉”,花崗巖外墻被噴涂上水泥砂漿,即是典型案例。
保護好老建筑,能使城市街區更有活力,能讓城市文脈傳承接續。而一拆了之,或者只圖眼前“好看”的胡亂粉飾,最終的結果將是可怕的。
改造的前提是不破壞
由博埃里工作室打造的米蘭“垂直的森林”,被譽為“世界上最美且最具創造性的綠色建筑”,因其800多棵樹和1.4萬株植物而聞名于世。
九江路501號頗有博埃里垂直森林的理念。建筑內部充滿綠植,在空間設計上采用了多種中意文化交流的構想。這些構想營造了與建筑外觀截然不同的視覺感受。建筑的大堂被完全打開,而大堂內部采用了定制的玻璃柱,很漂亮地連接了中庭四周。光線透過這些玻璃豎柱,干凈地灑在中庭中,如同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師特拉尼(Terragni)希望為但丁紀念館設計的天堂玻璃柱一般。這種具有“透明建筑學”的處理方式,為整個建筑營造了一種的近乎“純凈”的體驗效果。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不變更原有遺跡外貌。走到室外看,九江路501號依然如故。
改造,是必須的。畢竟,九江路501號最初的建筑理念,是為了適應20世紀初的證券交易所。當年的這一帶,是遠東聞名的金融中心。如今,外灘附近盡管仍有不少金融機構,但金融中心肯定東移至浦江對岸的陸家嘴去了。此地老建筑的功能勢必會發生變化,由此必然會帶來老建筑改造的問題。
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鄭時齡說:“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上海城市空間和建筑的演變經歷了復雜的歷程,既有暫時的停滯,同時又蘊含著強烈的動力;既有疾風暴雨式的動蕩,也有平靜的變化。上海城市空間和建筑是復雜的,凝聚了近代文化的底蘊,歷經磨難和考驗,面對過封閉的社會環境,城市經歷了反復的轉型。今天的上海,已經認識到延續歷史的記憶的重要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豫園地區的改造,新天地、泰康路田子坊、8號橋、城市雕塑藝術中心、1933老場坊等一系列歷史建筑保護和創意中心的發展,說明了城市正在恢復歷史的記憶,并創造更光輝的明天。”
從鄭時齡所說中能夠看到,城市發展過程中,對老建筑、老的城市空間加以改造,那是必然的。然而,這樣的改造不能破壞了城市的歷史記憶,更不能對建筑本身做出破壞性的“改造”。
近幾年來,《新民周刊》曾經報道過諸如廣東路94號到102號原三菱洋行大樓被噴涂水泥砂漿事件。此事,簡直堪稱給香妃噴灑廉價地攤貨香水,或是昂貴的絲綢襯衫外穿一件低檔化纖西裝;亦曾報道過巨鹿路888號違反《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胡亂給老建筑裝修加層之事,即便未來“恢復”原貌外觀,也是一幢“假古董”,建筑的整體價值大打折扣——某種程度上說,這位業主此種行為類乎自殘、自損,而其尚不自知。悲夫!
上海城市記憶叢書主編、老建筑研究者婁承浩先生對《新民周刊》說:“我認為,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空間功能的改變,老建筑是可以區別對待的——不具有歷史價值、文物保護價值的,比如說二級以下舊里,當然可以拆;對于有價值的建筑,要保護。保護的前提,絕不是類似2015年外灘三菱洋行舊址那樣用噴槍進行的施工快餐,而是要修舊如舊。但另一方面,對老建筑也未必‘紋絲不動,比如三菱洋行大樓做過黃浦區中心醫院門診部,樓內模樣早就時過境遷,如今也找不到原貌照片。那么,對之內部裝修什么的,就可以在不破壞建筑結構的情況下,進行發揮。”
誠如鄭時齡所說:“城市永遠處于變化和更新發展的過程中,所變化的既有城市的建筑、街道和空間結構,也有城市的產業、基礎設施、交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遷。然而,無論城市如何變化,城市的核心價值、城市發展所追求的進步目標應當是一以貫之的。”
老建筑的新功用
“城市更新,不是城區簡單的推倒重建,而是對過去幾個世紀中積累下來的、已接近壽命極限的城市遺產進行改造,使其保留、激活、新生,一方面適應經濟發展和民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顧及人們的文化感受,延續歷史文脈,彰顯城市特色,這是為了避免千城一面。”華夏文化創意研究中心理事長、《城市的復活》一書主編蘇秉公說:“上海的城區更新,多年來遵循‘拆、改、留的原則,在大規模構建現代大都市的同時,努力保存老上海的文化特色,取得了一些成效。”
曾經做過盧灣區領導的蘇秉公認為,接下來,上海城區更新“拆、改、留”的原則可以稍作改動,順序調整為“留、改、拆”,在思想觀念上強調“留”的意義。
如今的上海,老城區任意一處但凡有些歷史價值的建筑,或者街區,有那么一點點變化,一定會引得一眾老建筑愛好者聞風而動,或背著相機拍下老建筑夕陽中最后的影像,或在博客或者朋友圈中發布懷念文章。“留”,已深入人心。endprint
11月3日下午,已是日落時分。已退休的中學高級教師樂見成先生來到靜安區72街坊。寶安坊、成德坊、武林邨、永順里、戈登新村,拆遷工地,夕陽的余暉給廢墟上橫七豎八的木桿剪影鍍上一抹亮色。“隔著弄堂,望到尚還健在的那幾幢頗具腔調的石庫門老宅,浮華的門楣、精致的地磚、講究的樓梯……”
樂見成眼里富有夕陽之美的老建筑,確實因為夾雜在靜安最后兩片成片二級舊里中,而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
比之72街坊,66、67、59街坊所在的斯文里,本是上海規模最大的石庫門建筑群。西斯文里始建于1914年,東斯文里建于1918年。根據最新上海的城市更新政策,通過保護百年的石庫門建筑,可以得到容積率上的優惠,由此,開發商將保留部分百年石庫門建筑。
在婁承浩看來,只要這些石庫門不消失,就應該找到更好的用途。作為老建筑研究者,婁承浩不僅對具有數百年、上百年歷史的老建筑有興趣,他還對年頭并不長的建筑感興趣。譬如上海民生碼頭上的8萬噸糧倉。
“上海的民生碼頭曾經是遠東第一碼頭,有著亞洲最大的糧倉。這座8萬噸容量的糧倉,因為圓圓的筒狀外形,被人們親切地稱為‘筒倉。雖然建成至今只有22年,但它在城市的糧食收運體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而且承載了工業時代的印記。”婁承浩說,“黃浦江功能轉換后,‘筒倉最終沒有被拆除,經過4年精心改造成為空間藝術展覽館。”
提及“筒倉”,婁承浩說,他在上海建筑設計研究院工作時的同事張明忠是其項目結構主要設計人。“當初建筑用途是散裝糧倉,選擇筒倉造型,是因為圓形體積容量最大,無死角。”婁承浩告訴《新民周刊》記者,“空間藝術展覽館項目,屬于舊建筑再利用,倉齡滿50年后可申請優秀歷史建筑或文物保護單位。”
盡管某種程度上,該“筒倉”還只能稱得上是一處較新的舊建筑,甚至比許多人家住的“新公房”還要新一些,但因為城市功能的轉化,這幢建筑也不得不別尋其他用途。但不是一拆了之,足見規劃部門在此地塊上的用心。
“從西方現代城市建設的歷程和建筑演進看,大體可以分為三種走向。一是工業化盛期,城市化加速及城市空間大規模擴張,大量興建基礎設施和新建筑,舊區改造興起;二是后工業初期,城市擴張因資源、效率及環境的頹勢而減緩,城市部分功能和消費從中心向邊緣轉移,擴建、新建與保留、改造并舉,出現‘逆城市化現象;第三,到了后工業盛期,資源循環利用和能量轉換機制受到重視,既有建筑的保留、改造和再生成為主導,提出‘再城市化理念。”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常青如此說,“與此進程和走向相對應,歐美城市舊建筑改造工程量已占建筑工程總量的70%到80%。”
就上海來說,常青認為,自20世紀晚期以來,此三種走向的演進周期和遞變速度極快,總的趨勢是——第一時期高潮正在過去,第二時期和第三時期的疊加過程已經到來。
在常青眼里,單以石庫門為例,“新天地”的創意在開發,而非保護,況且1990年代中期的時代背景與如今《物權法》出臺后的情況大相徑庭,此模式不可能復制;田子坊內,本身就有始建于1930年代的藝術工作室和作坊,其由政府出資改善基礎設施,引入藝術家入駐,形成興旺業態,但并不是所有老弄堂都有與田子坊一樣的藝術底蘊。“大量受到法規保護,但生活品質已經低下的里弄石庫門,又該如何在保存的前提下新生,確實比較尷尬。”常青說。
至于“筒倉”如今的新用場,此種保護模式,可以說是自南蘇州路、莫干山路、8號橋等工業遺存保護開始,一路有跡可循的成功方式。在常青看來,此種改造,主要是對廠房、倉儲的改造而出現的大量“創意園”。“從城市文明的歷史特征看,近現代的上海是中國工業文明的搖籃,上海的城市遺產無疑應包括工業歷史的空間遺產。”常青說,“工業空間殘骸的再生,搭載著上海在后工業時代延承近代工業建筑遺產的脈搏。”
此種保護模式,最早在于建筑師登琨艷。他于1998年對蘇州河畔杜月笙的舊糧倉進行的改造,有點兒類似紐約蘇荷街的翻版,使得本來頗為沉重的“工業遺產保護”話題,成為了當時媒體熱議的輕快惹眼的流行時尚。為日后上海世博會江南造船廠等工業遺存的改造,提供了靈感。
在婁承浩眼里,無論如何,保留下來的老建筑要為今所用。他舉了最近考察虹口區后所思為例:“虹口原來劇場眾多,疏理后應該重開,讓評彈、滑稽戲、滬劇、淮劇、越劇、話劇等百花齊放,這樣,虹口就火了。”虹口如斯,上海亦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