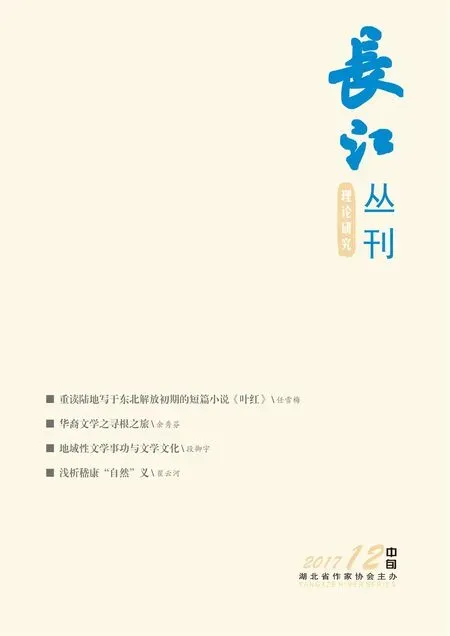“隱蔽”的中華文化在歐洲的“飛翔”
——以虹影《飛翔》為例分析歐華文學對“另一種中華文化”的彰顯
姚琬昱
“隱蔽”的中華文化在歐洲的“飛翔”
——以虹影《飛翔》為例分析歐華文學對“另一種中華文化”的彰顯
姚琬昱
中國流散文學雖作為居住國文學,但與中國文化以及現當代文學仍保持呼應。異域的寫作環境與移民生涯塑造了流散文學與國內主流寫作不同的文化特質,作為重要分支之一的歐洲華文文學,作家的域外書寫深受歐洲多語言多民族社會的影響。對文化多元的思考,逐漸從生存選擇到從中國傳統道家中提取思想根源,發展為群體性的精神認同—文化“第三元”。同時,這種文化發掘也使得長期被主流儒學話語所遮蔽的“三生萬物”的道家哲學觀在海外重獲顯現,而20世紀下半葉中國國內受戰爭文化影響而被割裂隱退的“五四”文化精神也隨之再次得到彰顯。本文以旅英作家虹影小說《飛翔》為例探討該文化現象在文學創作中的反映。
歐洲華文文學 三元理論 后殖民 “五四”文化
一、歐洲華文文學概況
海外華文文學是指中國大陸和臺灣省、港澳地區以外的海外各國的華僑、華人、外國人士,以華文為表達工具,以反映華僑、華人和其他人在居住國的社會生活,或中國大陸和臺灣、港澳地區社會生活為內容的文學作品。[1]中國海外華文文學大致形成了東南亞華文文學、美洲華文文學以及歐洲華文文學等主要流派。海外華文文學大致具有兩個特性:一是本土性,即文學表現內容集中于對當地人民、社會及民風民俗的描寫,且作品的藝術風格與主體選擇多帶有居住國的本土色彩,主要接受群體為本土讀者。二是中國性,即文學創作常與中國傳統或現代文學思潮相呼應。同時,由于海外環境受到中國國內政治形勢與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小,作家多保持了對中國文化自由選擇的創作態度,為在中國被割裂或遮蔽的文化思潮在海外顯現提供了可能。
歐洲華文文學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分支,代表作家主要有法國的高行健、程抱一,英國的虹影、趙毅衡,荷蘭的林湄,多多,邱彥明等。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80年構成歐洲華文文學的兩次創作高峰。同時,歐洲一體化使得歐華文學逐漸從分散走向凝聚,歐洲華文報刊也隨之紛紛出現。與其他地區的海外華文文學有所不同的是,旅歐傳統自近代社會以來一直游離于“民族救亡”的留學軌道之外,同時歐洲多語言多文化共生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文化包容性,及其長久以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神往,使得旅歐作家所攜帶的東方文明在歐洲得到較好的展開,同時與人文主義氛圍濃厚的歐洲文化相碰撞,形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長期被遮蔽的多元思想、個體主義、人文主義精神得到顯現的文化現象。①。
二、道文化的域外顯現和三元的精神歸屬
旅法作家程抱一基于自身的文化體驗提出三元理論,他將西方二元論的思想與中國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觀點相融合,主張異質文化和諧對話,相互包容的理想狀態。而歐華作家的寫作也逐漸從“早期對中式情調的宣揚轉為了對多元文化的思考和融合,力求跳出狹隘的民族文化觀,找尋一條世界性多元文化融合的道路”[2]。在虹影的《飛翔》中人物形象的建立本身蘊含著跨文化交流的特征,人物之“美”體現在“第三元”的顯現中,但作者并不止步于此,同時也將三元理論應用于后現代東方主義的思考中。
《飛翔》中寫東方文化是南京大學古板的校園和“溫柔纖秀而古典的她”,而法國文化則是鬧著風流韻事的法國男女和綠珍珠咖啡館。而阿爾丹在形象上則是中法二元文化下交融轉換的“三”。阿爾丹在南京大學教授法語,該設定本身提供了二元文化對話的可能,在東方環境下的阿爾丹,在法語課上朗誦法語詩《米拉波橋》,同時寫著《桃花扇》的論文和《扇舞》,《食蓮者》等富有東方意味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三山外的青天,白鷺洲畔,一個夢套另一個夢,是石頭都流成水,是水都流成石頭。可是我的喉嚨,嘶啞的喉嚨,能夠對你們,對那個陌生的東方,說出的唯一名字,仍然只有溫柔纖秀而古典的她。”[3]中式文化的傳統意象和法式的浪漫直白調和在阿爾丹的詩作中,而文學則成為阿爾丹精神上“二生三”的顯現。同時,具有東方韻味的柳小柳愛上帶著法式韻味的阿爾丹,愛情的產生正是三元文化下的和諧姿態和無限生機、生命力的表現。而后,阿爾丹與柳小柳以法式咖啡、《采薇》、書籍做著彼此相互交流的媒介,雙方在自由對話的“三”之環境中不斷向上發展。
程抱一反對靜態極端的二元對立,認為完全割裂的二元無法對話生出三。而虹影同樣也在《飛翔》中展現出極端二元下的封閉與毀滅。二戰后的中國文壇依舊延續戰爭文學時期的二元對立思維,而在文革時期發展到頂峰。對“資”對“外”的絕對清算使阿爾丹成為法國資產階級,柳小柳成為政治叛國的女鬼畫皮,文革的環境表述正是對二元對立的影射,而柳小柳的自殺和三十年后阿爾丹的落寞與衰老則是事物在缺乏交流下衰亡的結局。虹影在文本的潛在話語中展現的是對絕對二元的批判和對多元文化共存的理想追求。
而在“他”和蘇珊娜形象的建立上,虹影則表現了后現代環境下華人流散群體的生存現狀。賽義德認為東方被西方“命名”和“界說”了,不僅因為十九世紀歐洲人普遍認為東方具有“東方特征”,而且因為東方可以被制造和被俘虜為西方文化霸權體系中的一個“他者”形象。[4]文中的“他”與中國在法國文化圈一直處在“被看”的處境,國內同行譏諷“他”在國外教授比較文學是在賣野人頭,論及阿爾丹的書,“他”也承認“其中的中國恐怕是想象的創造,一如龐德筆下的神州古國。洋人寫中國的事,無論小說、詩歌或紀實哪一種形式,都極為無知,多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這點他最厭惡。”[5]。同時虹影構造出“他”對蘇珊娜論文和西方文壇中東方描寫的否定,潛在地表現出作者自身對西方文化霸權下對東方的誤讀與文化想象的對抗。但與賽義德等后殖民主義者不同的是,海外華人群體并沒有把東方與西方分割為絕對二元對立的屬性以號召革命式的顛覆,而是從中國古代的道學說中尋找出“第三元”的理論,主張二元文化間的平等交流,以產生包容、和諧的三元狀態,實現多元異質文化共通的可能性,以此來適應后殖民時代下的域外生存。故在此,在中國大陸被儒家一元中心所遮蔽數千年的道家思想在域外的特殊環境中得到強烈的顯現,成為海外華人的中華文化寄托與文化歸屬。
三、被新解的《桃花扇》與“五四”文化的重現
《桃花扇》一直與阿爾丹和柳小柳的愛情故事交織在一起,彼此形成呼應。但在虹影的處理下,《桃花扇》本身具有的傳統儒家的家國道德觀卻被政治背景下的個人命運感所超越,這使得在大陸被戰爭文化所斷裂的五四文化得以蘇醒。
傳統語境下的《桃花扇》的主旨探究多引用孔尚任所言——“借離合之悲,寫興亡之感”,是儒家“家國同構,君父一體”價值觀的體現。傳統文化下的理想人格的設定是以“社會理想”為主要評判標準,楊雄文學理論上的美學主張認為,“美”是倫理關系的完成、是善的普遍化,而“善”必須利于國家權力的穩定化。同時,“美”也是倫理修養的體現。[6]對于《飛翔》中出現侯李二人最后分別出家的悲劇,文學史解讀多引用張薇之語:“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里,家在哪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便是這點花月情根,割它不斷么?”以“國”、“家”、“君”、“父”的綱常名教弱化了男女私情的悲劇表達。故傳統文學批評中對《桃花扇》的關注遠不在于對侯李二人愛情及二人的命運的探究,而是更多著重于戲劇中政治道德的說教。
而《桃花扇》的人物理想在虹影的構架中卻得到轉換,阿爾丹參加法國的文化大革命,是錯以為柳小柳在國內也在造著資產階級的反,這樣或許他們就能團圓。而柳小柳面對對她政治錯誤和叛國的指責,也只是以沉默但不妥協的姿態予以反抗,直到誣陷的罪名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在學校,她憤然以自殺的形式維護個體的尊嚴。裹挾在政治變動時期的愛情在《飛翔》中不再是以意識形態性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出現,而是表現為在政治的選擇中追尋個人的理想與價值感。
小說結尾通過“他”之口寫到:“《桃花扇》那許多現代改編者,自以為得計。李香君該罵侯方域少氣節?侯方域該責備李香君無情理?孔尚任是對的:兩人理應分別出家,永不會面。男有男境,女有女界,大劫大難之后,國在哪里?家在哪里?”虹影否定了“少氣節”“無情理”的道德說教,而是承認在政治動蕩后人對家國的迷失感和漂泊感,把《桃花扇》和《飛翔》的愛情悲劇落腳在個人的情感體驗上,發揚了個體主義的人文關懷。
不可置否的是,虹影小說中的個體主義關懷很大程度上與她居住于西方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相關聯,但此書寫卻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表現。1937至1978年的中國大陸文壇的文藝創作主要受到戰爭文化的影響,高揚文學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強調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并運用戰時兩軍對陣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構思創作,使得“五四”啟蒙文化中所具有的人文主義思想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斷裂。而遠離國內政治的歐華文壇,則在人文氣息濃厚的歐洲使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和“平民的文學”等人道主義文學觀得到復蘇——即“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7]樸樸實實地記載世間普通男女悲歡離合的人生,表現“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8]。這使得中華文化傳統中“五四”精神在華文文學中再次得到彰顯,并在域外得到傳承。
四、結語
虹影《飛翔》通過“他”的視角,將“我”、柳小柳、阿爾丹三人的命運交織展開。同時引入《桃花扇》,構成了多重潛在話語。虹影在“他”的形象上構造出后殖民處境下華人流散群體的生存狀態,而在柳小柳和阿爾丹的形象上構筑起中法二元文化平等對話,相互融合的文化理想,同時又將這份理想毀滅在極端二元對立的政治環境中。在此“癥候”上可以解讀的是虹影的流散創作中對一元文化霸權和對東方主義想象的否定,對靜態二元對立的反對和對多元文化和諧共融的追求,這與程抱一的三元理論形成呼應,表現了歐洲歐文文學的共同訴求,一同使得被儒家一統遮蔽的道家哲學在海外得到浮現。同時,歐洲的人文主義氛圍使得歐華作家寫家國、寫人情更多地從人性關懷而非政治道德的角度思考問題,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國內被戰爭文化隔斷的五四人文主義文化傳統,使五四文化重新回歸到中華文化和華文文學創作中。
而在歐洲華文文學中,該文化現象得到較為普遍地展現。如法國華人高行健的“沒有主義”以及在文學創作中所展現的非儒家傳統的“另一種中國文化”。不僅歐洲,攜帶者中華文化基因的流散作家群體,如馬來西亞的黎紫書,美國的嚴歌苓,於梨華等,都在自己的移民生涯中完成了對中華文化與移民國文化的協商、融合與超越。這不僅以域外的視角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學中另一種被非文化因素所遮蔽的優良傳統進行改進、繼承,同時也為海外流散文學的經典化提供了獨特視角。
注釋:
①以上兩段參考自黃萬華《遠行而回歸的歐洲華文文學》。
[1]賴伯疆.海外華文文學概觀[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5.
[2]易凌沁.程抱一小說的三元特征及其文化定位[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3]虹影.飛翔[A].虹影,趙毅衡.沙漠與沙[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190.
[4]張京媛.彼與此——評介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J].文學評論,1990(01).
[5]虹影.飛翔[A].虹影,趙毅衡.沙漠與沙[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189.
[6]湯一介.中國儒學文化大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714~715.
[7]周作人.人的文學[J].新青年,1918,5(6)[A].任天石,等.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發展史[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8.
[8]任天石,宋吉述,等.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發展史[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8.
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