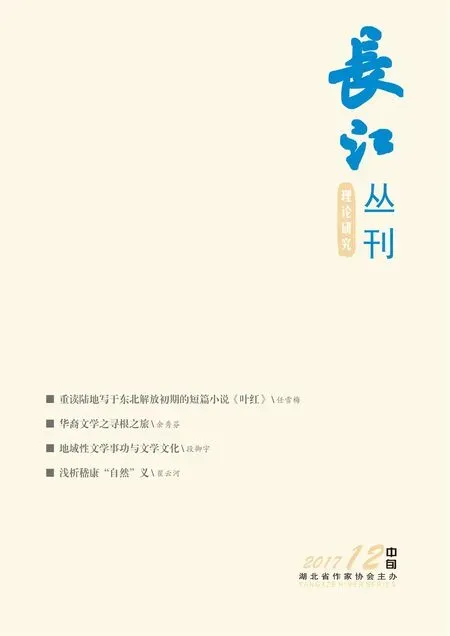時空視域下生態治理的哲學考量
靳利華
時空視域下生態治理的哲學考量
靳利華
當代生態治理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的新選擇,它的實施離不開一定的哲學思想。生態治理的實踐要修復生態系統的健康功能,營造所有生命體存在的生存環境,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定位。從時間維度講就是實現生物的自然時間和人類活動的社會時間的統一,從空間維度看就是實現存在物的自然狀態與人類社會實踐的社會空間的統一。
時空 生態治理 自然性 社會性 生存場域
世間萬物的存在都是發生在一定的時間,并占據一定空間的。換句話說,時空是是一切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的生存時空融入到宇宙、自然時空,“人的生存(的自我書寫和被書寫)的雙重性和(過去、現在、未來)之三維性,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實際生態場域:人是生存于時間和空間場態之中的,并且人的生存空間場態和時間場態又實際地融入了過去(已然的時空場態)、現在(實然的時空場態)、未來(未然的時空場態)之三維場域之中。”[1]生態治理是人類對被破壞的生物圈進行修復和保護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和存在需要在一定具體的區域內進行,也就是必然要在發生在一定的空間之中;同時生物圈的生態功能恢復和系統修復是需要一定時間的,在一定的時間長度中才能實現。因此,時空是生態系統自我恢復的必要維度,生態問題的化解必須在一定的時空中實現,生態治理的實施也必須在時空中考量。
一、生態治理的基本哲理
生態治理不是一種單純的實踐活動,它的實施需要依賴一定的理論思想,離不開一定的的哲學基理。首先,生態治理的實踐活動是生態系統組成的一部分,人類的社會活動要所在的生態系統保持均衡和健康。目前,學界基本形成共識,人類是生態系統構成的一部分,人類的存在與生態系統是息息相關的。“生態系統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允許他們保持功能的充分完整性以便繼續提供給人類和該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以食物、水、衣服和其他所需的資源。”[2]可見,人類社會系統的健康與均衡應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均衡健康保持一致。目前,生態治理的界域是人類社會系統存在的地球生態系統,目標是這一系統的健康均衡。簡而言之,人類的生態治理與生態系統就是一個局部與整體的邏輯關系。對此的論斷已經不需要論證。
其次,生態治理是為了所有生命體擁有適應的生存環境。人類與其他生命體是有別的,但不能唯人類利益而論。應當承認,人類從自然界衍化以來,就具有了自身獨特的屬性,使人類與其他物種有了差異。這種屬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必須同意利奧波德的觀點,征服生物界是太遲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找到適應的方式。”[3]這是人類應有的態度與立場,人類是不同于生物界的其他物種,但不是主宰者,而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人類在生物界應表現出對其他物種應有的尊重,但是這種尊重不是絕對的平等,而是一種物種之間平衡健康方式的選擇,“對生物、美好東西或者很好工作的東西的廣泛尊重,并不需要轉換成平等的尊重,它也不需要被轉換成普遍的尊重。我們作為道德主體責任的一部分,就是去對我們尊重的對象以及尊重的方式進行選擇。”[4]這種方式的選擇就是生態治理的目標之一。
再次,生態治理是為了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定位。人主宰自然的觀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已經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了。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哲學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確定的回答。這種哲理性的論斷在國家政策的具體實施中呈現出來,并非易事。如果每個國家都能認識到這種關系,就會大大減少產生生態問題的要素與誘因。理論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合理定位是多么的重要,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和主人,只是管理者和代理者。“從生物學和生態學的觀點看,把人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貶低人,而恰恰是還人以真實,防止社會以反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生物學特性。”[5]從這個角度講,生態治理就是要尊重自然生命,提高自然對人存在的生命價值。沒有自然生命,人的生命也將受到影響甚至是危害。因此,尊重自然生命也就是尊重人的第二生命。自然生命對于人的生命不僅在于它為人類提供的需求和服務上,而自然生命的過程與結果更重要。自然生命的生生不息和有機循環為人類生命帶來生活的福利。“自然為人類提供了生存空間、必需的生活資料、感官上的愉悅和精神上的資源”[6]。生態治理就是要再次調適人與自然、人類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合理健康關系。
二、時空維度上生態治理的蘊意
生態治理是人類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它是人類社會活動進步的體現,是重新審視人類與自然、生命體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理性選擇。這種活動是在特定的時空之中存在的。
一方面,一般意義上的時間包含兩個內涵,一是線性發展具有自然意義的時間,即自然性時間;二是人類社會實踐發展的具有社會意義的時間,即社會性時間。從自然性時間上看,不論人類如何活動,自然界的時間不以人類的主觀變化而發生改變的。宇宙、世界萬物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而生生滅滅。但是,自然性時間卻因為人類社會活動而具有了價值意義。“過去、現在、未來呈現了時間的單向發展特性,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時間又具有了價值的意義。”[7]正如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的,時間作為物質運動的一種狀態,具有經歷或長或短的一個持續性和先后的順序性。這說明,“時間的特點是一維性,即時間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向前發展,既不是循環,更不能倒退,即具有不可逆性。”[8]時間的這種特性在生態系統中表現的尤為明顯。生態特性表明一切生物的生存軌跡是有時間性,每一種生物都有自己的繁衍、生長、消亡的過程,一種生物與另一種生物之間的存在和發展變化始終呈現出一種不可逆的時間流。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在受損后經過修復不可能恢復到原先的樣態,只能是重新產生一個具有新功能和結構的新系統。生態治理是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的一部分,社會實踐構成的時間具有社會性。這種社會性的時間同樣表現出線性發展,人類的社會實踐是在不斷向前發展,甚至出現加速度。人類的生態治理實踐活動賦予世間萬物的自然性時間特殊的價值意義。
另一方面,一般意義上的空間具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的自然性空間,即一切物質存在的宇宙空間。這個空間狀態是一切存在物的自然狀態。在這個自然空間之中,人類與生物是具有同等重要的空間結構和布局的。人類與生物的空間活動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人類與生物的自然存在狀態維持了系統的動態平衡和健康功能。在這個自然空間之中,人類的空間與生物的空間是有界域的,這個界域是彼此安全存在的關鍵閥,一旦突破,人類與生物界都將受到損害。另一個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社會空間,這個空間是因人的活動而構建的。人類社會活動總是具體的,發生在一定的范圍內。空間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統一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之中。“自然空間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與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9]生物存在的生態系統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區域,生態系統的選取可大可小。生態系統的修復和生態功能的恢復也是發生具體的領域和范圍內,從這個意義上看,生態治理的自然性空間是自然存在的結構狀態。在這個空間結構中,人是空間活動的實施者,人類在生態治理的實踐活動中,改變著生物存在的自然存在狀態,同時也構建著人類與生物空間的結構狀態,形成動態的結構空間,空間的自然性經受著人類實踐活動的重構。在人類生態治理的實踐活動中,人類的活動將使得空間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出現統一。
三、結語
從時空統一的角度看,人的生態治理活動是人的一種生存狀態,是以場域的樣態呈現出來的。人的生態治理活動存在于生物圈的范疇內,呈現出生態場域的方式。人的生態治理活動是一個過程存在,是生態化活動的。作為生態活動的實施者,生態治理是就是人類要營造和重構生物存在的健康生態狀態。在人類實踐活動中,生態治理體現了實踐與時空,自然與社會的同一。正如黑格爾所說的,“空間的真理性是時間,因此空間就變為時間;并不是我們很主觀地過渡到時間,而是空間本身過渡到時間。”[10]生態治理是人類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歷史性選擇,也是人類在重新塑造與自身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的關鍵選擇。人類必選擇生態治理這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只有這樣才能扭轉生態危機的狀況,也才能使得人類的持續生存成為
可能。生態治理將成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一次理性選擇的轉折,將實現“自然、生命、人”三位一體的生態過程平衡。
[1]唐代興.生態理性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55.
[2][英]杰拉爾德·G.馬爾騰.人類生態學——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0.
[3][4][美]大衛·施密特.個人 國家 地球—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研究[M].李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08,305.
[5]陳根法,汪堂家.人生哲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18.
[6]賀麟.文化與人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118.
[7]袁偉華.時間與空間:新型國際關系中的時空觀[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3):27~28.
[8]趙家祥.歷史過程中的時空結構和時間向度——兼評西方歷史哲學的兩個命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39.
[9]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M].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21.
[10]黑格爾.自然哲學[M].梁志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7.
天津外國語大學涉外法政學院)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生態文明建設中生態治理中的國際合作與沖突研究”(項目編號:TJKS15-01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公民政治參與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3BKS036)。
靳利華(1971-),女,漢族,河北靈壽人,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博士后,天津外國語大學涉外法政學院,副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影響力研究協同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生態文明、中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