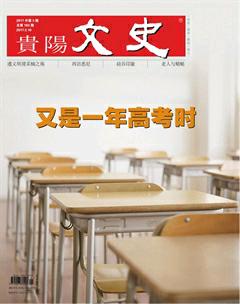貴陽新華書店、外文書店與內部書店
王六一
上世紀的城市建設規劃,新華書店和中國郵政都建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我自幼長大的貴陽也不例外,貴陽新華書店就位于市中心中華中路大十字左側的一幢樓房里,那時這幢樓可稱得上是城市的標志性建筑了。上世紀60年代初,社會文化生活有所松動,一批批國內外的優秀讀物開始出現在書架上,我父母擠出錢來,給我們購了彩色本的安徒生童話故事集《賣火柴的小女孩》、《國王的新衣》,連環畫《大鬧天宮》等。
稍及長,我對貴陽的書店還有點印象的是位于中華南路上的一家中外文古舊書店。我還模糊記得這家書店位于冠生園和越劇團之間,臨街狹長的書店里分中文與西文兩個區域,中文書架上擺有一些線裝書和書頁已黃的開明、商務書局出版的各種書籍;外文書則以英語書為主,大概是解放后50年代一邊倒的緣故,蘇聯小說的英譯本和俄文版混在一起,原版英文書卻很少。這家古舊書店有一五十開外的店員,英語講得很好,時常和購書的教授、老師講英語。“文化大革命”一來,這一書店消失了,后來連這條街上那些建筑全拆掉了。這家書店留給我的一個想法是:從今以后,在書店還能碰到與顧客用英語交談的店員嗎?
上世紀70年代,未讀完小學,幾乎沒在中學上過課的我,受到父母和朋友潛移默化的影響,開始自學中文和外語。學習得有課本和書籍,在貴陽人民會場右側的坡道上,有一兩層小樓被辟為貴陽新華書店業務部和外文部,成了我和朋友經常光顧的去處。非常幸運的是,我和貴陽新華書店業務員葉惠偉交上了朋友。小葉個子瘦高,精明能干,說話干脆利落,辦事認真負責。小葉的同事楊春當時就在外文部工作,楊姐一頭短發,雙眼明亮,很有精神,每次去她對我們都很熱情。那時,購外文書得憑單位介紹信,后來稍微松動,個人也可購買和預訂外文書刊了。這個門市部出售的外文版書刊和畫冊反映了社會的變化和開放程度,開始出售的是馬列、毛澤東著作英文、日文版書籍,接著出現了字典、辭典、語法書和一些科技書刊。那時我對外文書刊如饑似渴,只要經濟能力允許,什么字典和辭典都買。學英語,除了在大陸很流行的許國璋主編的英語教材外,港臺版《錢歌川英語》也很火,然而最受歡迎的是帶唱片和磁帶的《英語900句》和《靈格風英語》了。正是從楊姐的手中,我為自己和朋友們購了若干套這些英語教材。記憶猶新的是,我們幾位朋友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成立的英語自學小組開始是自已刻印油墨本的教材,后來大家都有了這些外語教材,還能聽唱片,學習就更方便了。
回憶起來,我們真是貴陽新華書店外文門市部的受益者。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葉惠偉所在的書店訂購了大量歐美文學、歷史原版名著印刷本,我們尚無全部購買所喜書籍的經濟能力,僅能考慮再三,挑選如吉本所著《羅馬盛衰原因論》等書。使人喜不自勝的是,當大批影印書出現后,我可以放開手購買這些價廉物美且中意的書籍了。影印書在那個年代真是偉大的創新。我和朋友們在外文門市部買到了精裝本《英語詩集》、《1500年來的世界史》、斯諾著的《紅星照耀中國》和近現代歐美作家歐亨利、馬拉默德等人的作品。我們購到了猶太作家艾爾薩斯·辛格的自傳體小說《肖莎》,由我和常錦譯成中文,因故未能出版。
我1980年代末從國外回來,這一門市部已擴大為外文書店,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到大十字的新華書店去拜訪小葉,遇到了楊姐,她已是書店黨支部書記了。得知我和常錦已出了譯作,她關心地問起當年一起到外文門市部購書的其余幾人的情況。我告訴他,何光滬已是著名學者,楊民生是英文學專家,陳明飛、王方鉅出國深造,成了教授和高級工程師。這位當年為我們輸送英文書籍的大姐臉上露出了微笑。
貴陽市新華書店內部書店同樣是我的向往之地。內部書店設在第五球場邊上的一幢兩層樓內,得經一背街進大門后左轉才到。直到現在,我閉著眼睛還能走到這里。這個書店專對黨政機關、大專院校、研究院所,不對外服務,名叫“機關圖書供應部”。我真是與葉惠偉有緣,陰差陽錯,他調到這兒來工作,對于我和朋友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我記得,9點上班時,書店樓下的門就打開,公開發行的書刊畫報全鋪在大桌上、插在旁邊的書架上供單位購書人員選擇,而樓上所售的內部書則憑票和證明,按所列書目和數目供應。單位派人來購書時,不一定完全取得到單子上的書,這就為工作人員預留了開后門的通道。那時,我跟皮煥昌先生學習古文,先生嗜書如命,我就甘愿充當他的書童,定期不定期來此購書。我為皮先生購每一期出版的《藝苑綴英》,10元一本,于我等算是價格不菲。當皮先生要我為他訂購《清史稿》時,我感到先生真是為了書而不惜代價了。我雖學點古文,但興趣最大的是國際外交和政治。說來有趣的是,我的好朋友溫佑銘在市蔬菜辦工作,作為市政府直屬機構,他們有購書證。老溫將購書證給我們使用,我們購到了丘吉爾全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杜魯門回憶錄》、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哈里曼回憶錄》等書籍。這些書在朋友們中傳閱,那時我們對外界的認識可以說全來自這些書本。我后來出國、遷居北京,每次搬家都會掉不少書。近40年后,在北京潘家園書攤上見到諸如《信使》、《第六次危機》等內部書籍,便將這些已發黃的書購下,即使不讀它們,但它們已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在貴陽近郊風景區花溪公園前面路邊和工礦區小河街上的兩家新華書店也是我喜愛光顧的地方。這兩家新華書店都不大,可各有特色。花溪新華書店距貴州大學、貴州農學院不遠,經常會有一些學術性和專業性的書籍。我和朋友騎自行車專程去這書店購書,曾在書店里購到過嚴復所譯《天演論》、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等書。我曾在位于小河的二十五中當教師,經常到小河街上的新華書店逛。小河是廠礦區,可這家書店卻經常進一些與機械設備無關的社科類書籍。我在1981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對在這家書店購到黑格爾的《小邏輯》有以下記載:“中午聽說小河書店有賀麟譯黑格爾的《小邏輯》,就趕緊去,運氣還好,還剩最后一本。據小楊說,一共到了五本,一天不到都買出去了。足見在我們這一地區對這種書有興趣的人還是有的。”
我還對另一家在貴陽郊區烏當的新華書店有著很深的記憶。那時我的好朋友楊朝清在這家書店當營業員,這可是我羨慕的職業。她母親與我母親是故交,我們都喜愛書,也成了知已。我有時也上這一書店購書,找他玩耍。朝清家有“海外關系”,在他秘而不宣將移民香港前,邀曠陽和我到烏當新華書店他宿舍一聚。我們喝酒為他餞行,在他那兒住了一晚,夜話的主要內容是書。楊朝清到了海外后,生活穩定,又開始了他收書、藏書之旅。他曾將收集到的十來本企鵝叢書英文版名著贈送給我,其中有勞倫斯《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喬伊斯《青年藝術家畫像》和弗洛依德的《釋夢》。
補遺:
本文發給陳常錦兄后,他又補充了以下幾段貴陽書店往事,特表謝意!
另外,在公園路上曾有兩家古舊書店,靠中山西路那家主營古書及書畫書,公園西路那家主營社科、文藝圖書,書價約七至八折,低的也才四至五折。看完后可又賣給書店,他們以稍低價格回收后又售,流通很快。這應是“文革”前的事。“文革”后未再恢復。王家巷那個店后賣外文及港臺版書,我去為單位買過《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臺版)。
80年代活躍的還有省新華書店下屬的古籍書店,有一門市設在正新街中段。機關服務部設在交際處對面貴州畫報社一樓,由一冉姓老人經營,我為單位購書常去。市新華書店的計劃發行部遷至遵義路展覽館旁,外面是營業門面,后面專為大學、機關及專業圖書部門服務,用各種書目訂貨,書到后打包通知去取。我那時每月去一次,付款提書。
還應該一提的有中華北路(噴水池附近)的貴陽作家書店,開始由省文聯的幾個作家發起,后他們退出。書店由市書店退休人員劉碧榮經營,一度很知名,特別是首次包發《山坳上的中國》很有影響。后門面拆遷,搬到都市路口后不久停辦。民營書店除西西弗外,西南風、文豪、達德等均各領風騷,現變化大,能堅持下來只剩西西弗、達德兩家了。
又想起一個店,大十字總店斜對面(正新街口)是市書店的科技門市部,曾經熱鬧過。只不過我們買得不多。門市部后面是批發部,我們去幾次買我們所譯的《喋血佳人》來送人。
后記:
今年是新華書店成立80周年,作為一名讀者,通過這篇回憶,與愛書人慶祝新華書店華誕!
(作者系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