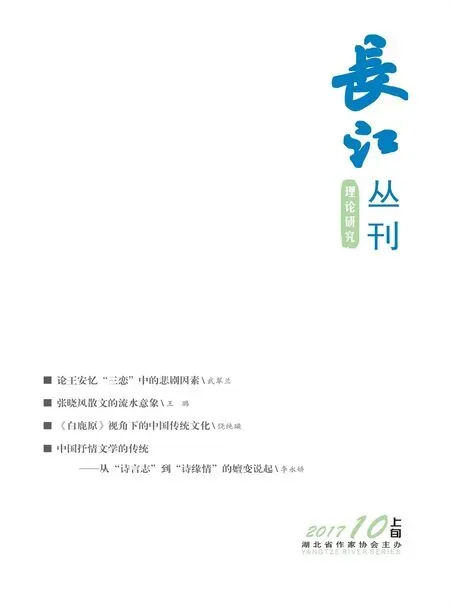答案在風中飄蕩
辜悅揚
答案在風中飄蕩
辜悅揚
冒著嚴寒,隊伍終于趕到了千余里外的北方,那是我別了二十一年的故鄉。落日緩緩騰著光芒。群山疊影,我們像皮影上的小紙人兒,在狹縫中喘著氣,背著疲憊,背著太陽。
作為雇傭兵,這是我的最后一場戰役。
時至今日,我仍在尋找阿丘。從我與他失散的那天起,已過去一條狗生命的二分之一。漂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我一直念念不忘。
二十一年前,敵人是在夜里來的,沖天的大火燒紅了半邊天。我和阿丘木在炕上,火光把我們黑油油的臉照得通紅。
父親背著我,赤著上身。我聽見阿丘不斷喊我的名字,聲音越來越遠。
“阿丘,阿丘。”我小聲回答他。
母親纏著小腳,跑不遠,不等父親折回家中,她把阿丘藏在了院子背后的那口枯井下。井不深,又隱蔽。他們最終死在了入侵者的刀下,逃出來的村民說,沒有留下一個活人。
我不信。
阿丘出生那年,槍聲越來越近,大旱,饑荒,餐餐都得省著吃。我常搶了他的小竹簍拿去賣錢,把娘繡給他的虎頭鞋偷偷送給村頭的姑娘,偷了隔壁家的雞飼也讓他頂罪。比起我的跋扈,他很少吭聲。我當他木訥愚笨。有時家里人心疼不過,把余下來的零嘴省給他,他卻悄悄藏回屋,踮著腳,放在我的木桌上。
村里的人把我帶到了附近的城鎮,逃亡者乘車去了更遠的北方,我選擇留下。
戰爭卷走了一切,斷絕了謀生的活路。滿街橫著停了蒼蠅的腐尸和伏在地上的餓殍。尋找阿丘成了度日如年的歲月里我唯一的念想,也成了我尋求一生答案的謎題。
“這日子不是人過的!”小石頭蹲在田坎兒上抬眼對我說。
小石頭是村長的小兒子,娘是偏房,年輕,被敵人擄了去,再沒音訊。剩下一家人到了縣城,大太太向來不待見他,無奈,他爹棄下他逃命。一去就是五六年,我倆留在城里,為了謀生,什么營生都做。一路往西走,探聽來一條財路:當雇傭兵。
“給誰當兵?”小石頭問。
“管他呢!這年頭,有口飯吃就不錯了!”那人穿著破爛布衫,挑著一籃蔫壞的野菜,瞄一眼冒冒失失的小石頭,搖搖頭走了。
部隊是什么來頭,沒人知道。我和小石頭四處打探,無從得知。
“走吧,當雇傭兵有啥不好,吃穿都齊全,俗話說,有奶便是娘,咱還能餓死不成?”小石頭三番五次地勸。我最終應了下來——部隊往北,沒準經過村子,還能找到阿丘。我倆匆忙弄了身衣裳,投了軍。
軍旅是艱苦的,幸得有小石頭。他會唱歌,會耍寶,還會講故事。
一路勝仗,一直打到關口。小石頭攢夠了盤纏,同我分了路。
“我要去南邊兒。”他說。那天夜里,凜冽的北風刮了一宿。“我爹躲在南方。趁那邊戰事不緊,我們父子還能聚聚。剛好有支隊伍南下,我明兒就走。”我驚愕,又啞然。這些年他走南闖北,原來并非無所掛念。
“得。你再給講個故事唄。”黑暗里,我語調故作輕松。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人。他不顧千難萬險,尋找他的親人。后來……”
還沒等到后來,天亮了。小石頭托我把他娘留給他的那根紅頭繩埋在他家墳上。
不知這一別,又是多少年。
隊伍剛入了山口,傳來消息,小石頭死了。
“石頭沒了……他讓我轉告你,這場仗,無論如何你都不能打。”
報信的是他的隊友,臨走前他把小石頭的紅頭繩交給我。頭繩躺在我黑黝黝的手掌上,像一道疤。
不遠處,槍聲從塹壕里往嶺頭高高低低地刺來。霎時間,鋪天蓋地的車輪聲和踏步聲震得吊橋上的鐵片嗡嗡震響。河岸上躥起半人高的火苗,煙霧貼在江面上,隨著風蕩遠。我匍匐著,搭住吊橋的鐵鏈。
只要攻破這座吊橋——
交鋒持續了兩個小時,腳底的土地不斷顫動著,伴隨巨大的爆裂聲,青山抹上了鐵蝕般銹紅,江水凝著濃血,緩緩向前。末尾的槍聲帶著永訣的意味,我殺死最后一個歪著頭半跪著的士兵,他看著我,瞪大了雙眼,仿佛驚愕的神情。我看不清他滿是污血的骯臟的臉,待我從草叢中爬起,他已倒伏在戰友滿是彈孔的尸體上。
“隊長。”我把武器和軍服退下來,捧在手上。“這仗打完,我也該回家了。承蒙大家多年照顧。”
他拍了拍袖子上的灰,笑了。“十多年出生入死,總有個頭,既然到了家,那就回吧。槍你留著,過了橋,就是另一個世界了。”他意味深長地望了一眼江水,方才觸目驚心的紅,已經浸沒在滾滾石沙之下了。
臨走前,隊長讓我把死傷敵軍的武器繳回,權當最后的任務。我利索地把槍支一個個搜羅起來。走到最后一個被我放倒的士兵前,我才發現他的食指緊緊地扣在扳機上,拽著機身,仿佛子彈出膛不過一秒的事。我一面心下疑惑他為何沒能在我之前先下手,一面將他的尸體翻轉過來。
那是一副熟悉的面孔,盡管已經被凝結的血痂覆滿整個常年被江風吹得通紅的臉頰上,那眉眼,卻仍是我夢中的樣子。我呆住,像一截木頭。
阿丘!我驚叫一聲。
“兄弟!繳完槍就趕緊回家吧,起風了,怪冷的!”風從北邊來,有摧枯拉朽之勢。染血的軍旗獵獵捕風,呼號著,死一般寂靜。
起風了,阿丘。我回來了。我們回家吧。
除了呼嘯刺骨的江風,沒有回答。槍上凝固的鮮血還有余溫,他的手卻冷得像塊冰。我合上眼,一片血紅。頭頂的陽光像一道又細又長的刀刃,刺穿了太陽穴。
倒下的時候,我聽見了耳畔的風聲。那聲音越來越小,仿佛他兒時的夢囈。
成都市實驗外國語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