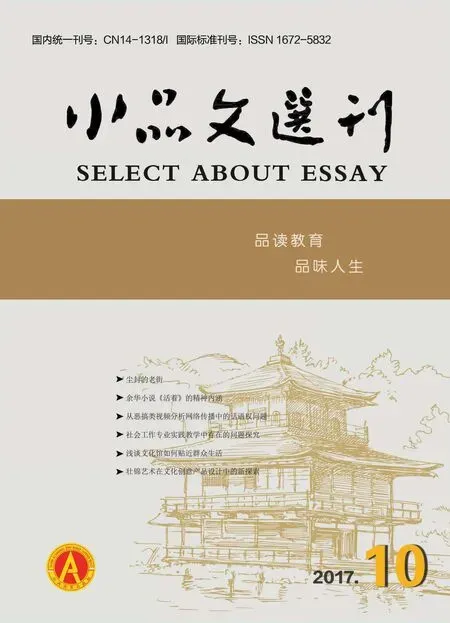史學三思
王 鑫
(暨南大學 廣東 廣州 510632)
史學三思
王 鑫
(暨南大學 廣東 廣州 510632)
當今社會的人們對物質的追求逐漸超出了對精神文化的追求,自近世以來的崇洋媚外的心態也仍舊大行其道,以致對本國的歷史和文化處處持以鄙薄的態度。實非良好的風氣。然而教科書中的歷史教育卻并未有對中國悠久的文化起到很好的宣傳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致使一些對中國古史的真實情況有部分的夸大和扭曲,讓本來就對本國歷史不甚了解的國人對歷史的誤解更深,導致抑中揚外逐漸加深的惡性循環。所以,我們應該用正確的史觀重新認識歷史,客觀的對待才是發揚和傳承中華悠久的歷史文化的正確方式。
中國歷史;馬克思主義史觀;神道設教
1 國史之思
我曾記得高中的時候一位和我玩的比較要好的同學跟我說過:“我總感覺中國的歷史十分落后,總是處處不如西方。”雖然我那位同學的言論可以理解,但是我聽后仍然不覺有幾分驚訝。雖說中國近世以來,由滿清上層統治的狂妄無知,迂腐不化,加之整體中國之制度的腐化,乃至貽誤中國近百年發展機遇,怠及中國從近代以來,節節落后于西方,以致屈辱條約,洋槍鐵炮,將中華數千年來“天朝上國”,“萬國來朝”的美夢轟的粉碎,中華睡獅待漸漸蘇醒之時,已是體無完膚。中華民族發展到幾乎遭外族顛覆的地步,中華之自信與自豪似乎被西方的機器揉捏與踐踏的一文不值。于是,近代向西方求學的呼聲日趨風尚,其當時之人亦也有全盤西化乃至全盤否定中國之傳統的狂妄論調。
然而,昧人不察,中國自古起碼有四千年發展之歷程,且傳續至今者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國家來,以近世百年之沒落,來否定歷來千年之恢宏,實屬妄自菲薄之庸徒。又有人反駁說,中國幾千年來處于封建社會毫無進步,有什么可值得說的。關于封建社會這一名詞,在下文中另有解釋說明,此不贅述。其實“通覽國史,我民族實乃一善變之民族。”①試看中國古時政府歷來推崇的儒學,又漢武時而定正統,然其實并非以儒為統,其中政治思想夾雜著道法陰陽五行之學,漢宣帝因太子“柔仁好儒”,而教訓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②由此可見奉為還圭臬的儒學治世之道并非“純任德教”,而是根據具體的現實社會狀況而加以融合變通。此后唐時的三教合流,宋明之理學心學,再到近代求變之中體西用,至民國時梁漱溟、錢賓四先生等開創之新儒學,都是其隨時代之變化而發展。又如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又周初的分封,到秦至唐前的州郡縣時期,唐至元前的道路時期,元后的行省時期,一直延續至今,這些制度,歷來總結前人之覆轍,而另辟后人之新路,地方政治的不斷演變,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國家的大一統,中國歷來以泱泱大國的姿態來傲世群雄,皆賴于全國之凝聚統一,而統一之策又汲取前人智慧精華而變通于今世。包括現在中國也要講統一,反對藏獨、疆獨、港獨、臺獨。你若一味的強調一成不變的傳統,何來如今統一之中國。正如錢賓四所說:
“國人每謂我立國于東亞之大平原,環而處者皆蠻夷,其文化力量遠不逮我,遂以養成我固步自封,自尊自傲的態度。而永不變進。其實任何一民族,一國家,其政治文化,并無歷數百年而不弊之理。若待其民族國家內部之文化政制等已臻腐敗。則如果熟魚爛,并不要外面再有他力,其一身生命即趨毀滅。”所謂我國一直落后不變的叫囂,實為愚蠢而又妄自菲薄的民族虛無主義者與文化自貶主義者。”③
錢賓四說一國之民應當知一國之史,且對本國之史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這里所說知一史當然不求人人都是歷史專家,而是要對本國歷史有一大概了解,對本國自古發展以來一脈相承之總趨勢有一形象認識。而如今且不說大部分人對我國歷史的盲然,那些難得對歷史感興趣者在網絡上貼吧里肆意的發表自以為獨樹一幟的高談闊論,而毫無確鑿的歷史依據,不知道他們是哪里看來的材料,或許是隨便搜索復制而得,或許看哪本比如《一周讀完××史》之類的快餐式讀物。更有甚者,如一幫喜歡清史的人和一幫喜歡明史的人拉幫結派的進行“論戰”,大都有互相詆毀之辭,弄一團烏煙瘴氣,無知!可笑!更不用說抱有“溫情”與“敬意”了。史學有爭論是好,可是肆意的褒貶那就是個人的愚昧了。或許大家可能會說這是網絡文化,可以暢所欲言,是非對錯都無關緊要,不必強求其言論的客觀性。然而,孰不知,現代社會網絡文化越來越融入我們的生活的同時,網絡文化也正在對我們人格個性的形成產生著不了低估的影響,當網上到處糜濫著偏離歷史常識的論調,到處充斥著自以為得意的言論,而實際上這些言論的得出并未真正經過仔細研究,僅僅是道聽途說或者隨便套用他人的觀點。如今社會上的這種蠢貨不少,務虛之風大行其道,這就不光是史學的悲哀,更是民族精神的墮落與靈魂的自毀。
史學的光輝在如今社會已經逐漸暗淡,當然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下的一種普遍現象。理工科類的知識對經濟的發展產生直接影響,隨之而來的經濟效益自然豐厚,因此經濟學等金融學科成為當下社會之顯學,人們對比趨之若鶩。雖然國家大力提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然而,這始終是一句空口號,傳統的東西逐漸不適應人們目前的日常生活,或者不認為是必須的了,接觸的少之又少,又何來弘揚發展之說。所以,一些人認為我們學習歷史學這種出來就業路子窄的專業,是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可是,當人們都不愿意踏上這條不歸路時,便是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絕路了。
2 育史之思
自古以來,中國史學家們向來崇尚史以真為貴,史憑實為信。歷史著述要客觀,褒貶得當不諱飾,不浮夸,這是史學評價的圭臬與準繩。然而,目前的大部分史學著作,就我個人我所見,并非書寫作者的真心聲,從事者多半有“為政治服務”的嫌疑,“唯恐揣摩圣意有誤”④。就拿我們從小學到大的教科書來說吧,可謂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總代表。其中張口閉口就是階級與階級對立,而且其中的評價也是毫無根據,莫名其妙,試舉一例,由朱紹侯、齊濤、王育濟主編的《中國古代史》里第七章第一節中論述漢武帝時期加強中央集權的法律措施中說:
“在漢武帝時期,法律更為嚴密繁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條文如此煩苛,表明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統治的殘酷性。”⑤
這么一小段文字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沒有什么爭議,按照一般傳統思路,古代封建政府做的一切都是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可是,當我仔細琢磨的時候,對這個所謂的煩苛的法律產生了質疑。由這些數據所看,這些法律規章確實繁多,可是光從這“三百五十九章”、“四百九十條”、“千八百二十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的法律就能斷定這就是對人民統治的殘酷嗎?試看今天的法律建設,根據中國2010年法律建設報告中統計,中國目前國家法律法規有1109部,國家的法律條文共4767條,加上地方的法律條文還有7830條,單憑數量上漢代的法律對比現在來說可謂是小巫見大巫,更“繁”,更“雜”,可是當今的法律并沒有體現出對“人民統治的殘酷性”,而是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不斷完善意味著以后還要增添更多的法律。如果舉出法律條文的內容說明統治者如何對人民敲詐勒索,敲骨吸髓,濫用酷刑等證明其殘暴無道,尚能使人信服,而光憑數量之多寡就斷言統治者的殘酷,這在邏輯上怎么也說不通,不知編寫這章的教授們是如何得出這種驚奇的結論的。
這種主觀臆斷的妄下定論實屬史學的大忌,然而書中確會一不留神的就碰出一些類似的奇妙言論,除了可笑還有惡心!
3 “圣”史之思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向來尊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雖說唯物史觀是我國的指導史學思想,處處研究皆從此著手,雖然,其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是若真的以此為中國史學的“圣旨”,還是需要仔細思考與討論。唯物史觀指出社會的發展形態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隨后即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我以一名才疏學淺的學生發出一個不入流的質疑,中國這個國家是一個獨特的國家,正如前文所說,歷經數千年滄桑而依舊延綿至今,世界上找不出像中國這樣的第二個國家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向來獨具一格,馬克思并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沒有通讀過中國歷代典籍,可以說對中國整個大歷史了解的并不透徹,而他的封建社會論的普遍性在中國的實行確在中國大陸廣泛的流行,而中國獨具一格的社會是否有必要為了印證馬克思的觀點而削足適履的加以封建社會這個標簽呢?這一點是值得質疑的,史學家們不是人云亦云的加以推崇肯定,我年紀輕輕,學問不深厚,這里無法做出我自己的解答,只能提出這么一個質疑。
中國的正統史學的尊貴地位一時無法撼動,上頭倍加推崇此理論的意義大家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不禁想起了清代的“神道設教”。“神道設教”這個詞出自《易·觀》:“觀天下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⑥此意思即是設以精神信仰使天下歸服,徐維錚先生談到清代的神道設教說:“也如中世紀列朝的‘神道設教’,滿清首先要求增強以愛新覺羅家族為核心,的征服族群的向心力。新滿洲自稱金朝女真族嫡系,卻害怕重蹈金朝漢化的覆轍。它在全國統治越穩定,君主專制越強化,而皇帝對于征服族群喪失權力的擔憂越增長。”
“神道設教”意義在于加上統治者的權威,雖然現在政府沒有如清朝那般迷信的設以神仙巫鬼的信仰,而思想與文化的教依然還陰魂不散,倘若中國只有這么一種史學體系,那么中國歷史形態基本被早已經作古的馬克思預定了,討論來討論去就是這些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總是這個階級與那個階級的對立與反抗,那么,這一路發展的體系脈絡被形式化的固定下來,那么整個大背景大環境的研究就毫無意義可言了。就如西方學者所可惜的那樣,中國擁有豐富的原始資料資源,可是近世中國史學的發展并不如人意。就中國目前狀況來說,史學在大眾眼中已經基本的淡出了生活,人們接觸歷史的知識大部分都在學校時所學習的課本中得來,而從小學至中學乃至大學的專業歷史課本的書都以階級的斗爭角度一脈相承下來,以致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給人的印象就是階級斗爭的不斷反復以及所體現的吃人與黑暗,難怪我的那位同學要說中國歷史給人的感覺總是落后的,處處不如西方。這等史學教育,何談史學復興,文化復興,一切都是無稽之談。
當然馬克思主義史學不能加以全盤否定,也不能作為“神道設教”般的禁錮國人的思想,其自有可取之處,亦有需要發展的地方。中國的真正的開明“百家爭鳴”時代不僅需要老一輩史學家不斷努力,更需要我輩青年放眼世界,以主動之責任感挑起民族文化的大梁。
注釋:
① 錢穆著,《中國史學發微》,第5頁。
② 班固著,《漢書·元帝本紀》,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錢穆著,《中國史學發微》,三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④ 朱維錚著,《重讀近代史》,上海文藝出版集團2010年版,第213頁。
⑤ 朱紹侯,齊濤,王育濟主編,《中國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5頁。
⑥ 蘇勇點校,《易經·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頁。
[1]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三聯書店2005年版。
[2]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三聯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4] 班固:《漢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 朱紹侯,齊濤,王育濟主編:《中國古代史》2010年5月版。
[6]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7] 蘇勇點校:《易經》,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8] 司馬遷著,張大可注釋:《史記》,華文出版社2000年1月版。
[9] 林華國,《近代史縱橫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0] 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5月版。
K01
A
1672-5832(2017)10-0253-02
王鑫(1994—),男,漢族,江西南昌人,暨南大學文學院碩士在讀研究生,專業方向:中國歷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