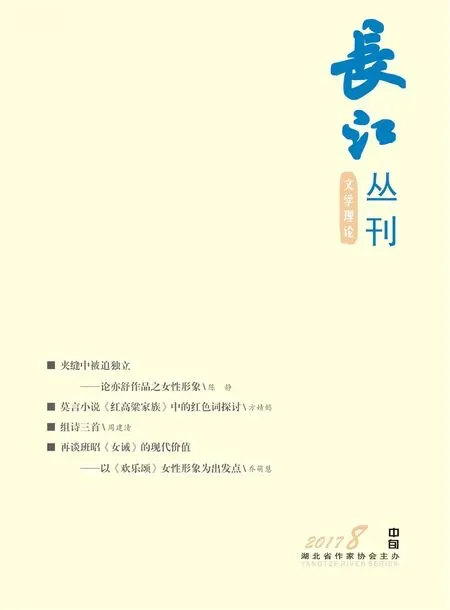理解“瘋話”
鄧翠蕓
理解“瘋話”
鄧翠蕓
本文從精神疾病的認識、理解精神癥狀的意義以及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癥的個體經驗幾個方面,強調工作中應重視對精神癥狀的理解,減少歸類和標簽化。
精神疾病 精神癥狀 理解
精神疾病是以心理(精神)活動(指感知覺、記憶、思維、情感、意志活動)異常為主要表現的一大類疾病。按照心理活動不同及心理過程的異常特征,應用醫學概念將它們概括為感知障礙、記憶障礙、思維障礙、情感障礙和意志障礙等類別。這些不同特點的各種障礙又分別有它特殊的具體臨床表現,即稱之為某種精神(心理)癥狀。而那些林林總總的精神癥狀,都是臨床上對精神疾病下診斷的重要指標。
國家心理咨詢師培訓教程及各類培訓教材中均明確說明了心理咨詢師的工作對象,即有心理問題的正常人,發病期的精神病患者并不屬其中,咨詢師在工作中必須對其進行轉介。而轉介到相關專科醫院之后,重者先是“五花大綁”強制住院,輕者也要各種藥物治療。“對癥下藥”完全照搬了臨床醫學的治療模式。精神病患者的各種“瘋語”只是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被害妄想”、“幻聽”、“詞語雜拌”、“思維奔逸”......或者成為茶余飯后的笑料罷了。沒有人會認真理會“瘋語”的背后到底是一種怎樣獨特的存在體驗。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精神癥狀呢?
一、精神疾病是一種最瘋狂的絕望形式
“絕望是一種試圖擺脫或否定自我現在所是的自我的疾病!然而,如何實現這種否定或擺脫現在所是的方式因人而異。絕望的最低形式是:在絕望中不要成為其自身;最瘋狂的和最強烈的絕望形式是:在絕望中要成為其自身。”“在絕望中拒絕成為其自身”,無法忍受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和矛盾,于是選擇了自殺;“在絕望中要成為其自身”,現實中無法實現理想的自我,只能在幻想中實現,于是成了臨床意義上的精神病。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美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阿道夫`麥爾(Adolf Meyer)認為,許多精神病都是一定的人格對某種社會處境的反應,導致一個人發病的最大問題是他的希望或抱負與他的現實狀況之間的不協調,而有些病人就是用白日夢來解決這一矛盾的。
二、當“瘋話”能夠被理解,還有精神病嗎
社會總喜歡用“正常”和“異常”對事物進行人為的分類,符合社會規范的正態范圍內稱之為“正常”,偏離正態分布區間的稱之為“異常”。所以弗洛伊德說:“文明是健康的大敵”。正因如此,精神病患者常被歸于“異常”的范圍內。何謂“異常”,就是不被社會大眾所理解的,不被社會所接納的。如果精神病患者的“瘋話”能被大眾理解了,也許精神病就不復存在了。
一位精神分裂患者說:“瘋狂是我們的噩夢,在夢中我們呼救,卻沒有回應。我們呼救,卻沒人聽見和理解我們。我們無法逃離噩夢,除非的確有人聽見我們,并幫助我們醒來。”如此說來,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真正地理解他,他就有可能醒來。
三、咨詢師應該重視對“瘋話”的理解
人需要在別人的理解中認識自己,人的自我價值、他的言語與行為的意義需要再別人那里得到解讀,尤其是需要得到他認為對于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人的理解。
臨床所見,不少精神分裂癥病人長期依賴藥物,長期臥床或脫離正常的社會生活,與其說是不能被治愈,還不如說是他們不愿意治愈。因為他們沒有面對苦難、面對痛苦和殘酷現實的勇氣,他們寧肯沉浸在脫離現實的夢的世界里。幫助精神病人康復的關鍵是站在當事人的處境,理解他所面臨的困境,鼓勵病人勇敢面對現實,杜絕產生妄想逃避現實的心理激活作用,而不是長期的維持用藥。
四、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癥的個體經驗
英國反精神病學派的代表人物R.D.萊恩說:“我們可能知道有關精神分裂癥病理學的全部知識,但是卻不能真正理解任何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那怎樣才能真正理解精神分裂癥個體的特殊經驗呢?只有“患過病的醫生才能治好病人”嗎?
首先在方法論上,我們不能把患者的行為看成“病癥”。萊恩曾說過精神分裂癥患者和當代精神病學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我們無法理解精神分裂患者對于自身的經驗之核心。只要我們依然正常而他還在發瘋,我們就始終無法理解。”“如果我們把患者的行為看成‘病癥’,那才是把我們的思想方式強加于患者,結果正與患者對待我們的態度相似;如果我們認為自己能夠‘解釋’患者的現在,把它看作一成不變之‘過去’”的機械結果,我們也就犯了同樣的錯誤。如果我們以這種錯誤的方式面對患者,那就幾乎無法理解患者希望告訴我們的東西。”我們不應該局限于自身世界之內,用我們自己的范疇對他加以判斷,以為這樣就能理解他。他不需要這樣的理解,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徹底承認他的獨特性和差異,承認他的獨立和孤獨以及絕望。
其實,應該把個體的特殊經驗至于他整個在世界的前后關系之內去理解。阿道夫·麥爾(Adolf Meyer)認為,精神癥狀是病人企圖用來治療自己的一種不適當的嘗試;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適應不良,它可以從病人的生活史中找到解釋。萊恩也認為,如果不理解精神分裂癥患者瘋狂言行的生存性關系,就無法理解這些言行本身。”
診斷是必要的,但只有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才需要診斷,咨詢師不能帶著癥狀和診斷去工作,更應該把所有的來訪者看成正常的,是人為的規則出了問題。一旦嘗試歸類、診斷,就會減少好奇和探索。咨詢師眼中應該只有事件沒有癥狀,盡量做到不判斷,不歸類,不貼標簽。只有理解,才能讓咨詢閃光。
[1]邱鴻鐘.醫學與語言[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單位:廣州工商學院)
鄧翠蕓(1988-),女,漢族,廣東韶關人,管理學碩士,廣州工商學院心理咨詢中心,中級社會工作師,研究方向:精神衛生與臨床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