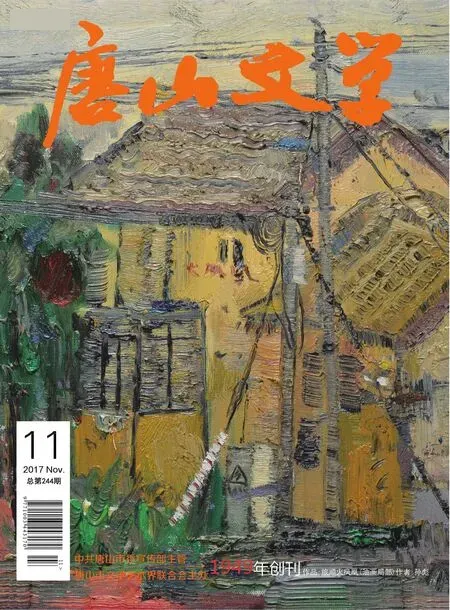在生存中尋找存在感
——析池莉《托爾斯泰圍巾》
金蘭芬
在生存中尋找存在感
——析池莉《托爾斯泰圍巾》
金蘭芬
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實(shí)用價(jià)值成了人們普遍信奉和推崇的價(jià)值理念。當(dāng)我們面對(duì)光怪陸離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生存的考驗(yàn)不斷沖擊著往昔純真干凈的愛情婚姻,越來越多的人迷失在物質(zhì)的誘惑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jīng)來不及認(rèn)識(shí)自己,來不及思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生活壓力的加大,使得人們?cè)谏钊χ邪缪葜煌纳鐣?huì)角色,屬于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在生活中不得不變換著不同的角色,這種角色常常處于一種難以言說的尷尬中。家庭、工作、房子、職稱……當(dāng)生存這個(gè)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的時(shí)候我們經(jīng)常會(huì)責(zé)問自己該如何生活。“生活就是這樣微妙,也就是這樣無情;無數(shù)的因素?zé)o時(shí)無刻離間人們;個(gè)人的命運(yùn),都埋藏在這無數(shù)因素之中,自己卻從無感知,何談去把握?”(池莉)
一、直面生存現(xiàn)實(shí)的逼仄
池莉筆下的人物往往是平平凡凡的小市民,帶有世俗氣的蕓蕓眾生,是遠(yuǎn)離英雄主義的凡夫俗子。她還原了某些特定階層市民生存的本真狀態(tài),把真實(shí)的你、我、他作為作品的主人公,他們就從我們的生活中走出來,一張張臉都似曾相識(shí),仿佛就是身邊的鄰居、同事、朋友或者親人。她的寫作充滿了對(duì)生活的思索,對(duì)生活現(xiàn)狀的思索,這種思索來自實(shí)實(shí)在在的現(xiàn)世生活,所以更接近現(xiàn)實(shí),貼近生活。池莉稱自己代表的是平民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她完全融入人物的立場(chǎng),與生活本身和老百姓的生活觀比較貼近。“對(duì)于一個(gè)幾乎在童年就選擇了文學(xué)的人來說,我很高興自己首先不是從書本和學(xué)理那里來認(rèn)識(shí)世界,換句話說,不是從人類社會(huì)已經(jīng)規(guī)整的、梳理的、邏輯的和理論的地面建筑來認(rèn)識(shí)這個(gè)社會(huì),而是從這幢建筑的最底層—地表之下,那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實(shí)的生命發(fā)端處體會(huì)和領(lǐng)教這個(gè)社會(huì),這種親身的體會(huì)和領(lǐng)教對(duì)于個(gè)人生活來說雖然充滿辛酸和苦澀,同時(shí)卻也充滿了文學(xué)因素和寫作動(dòng)力。”(《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
池莉的《煩惱人生》細(xì)致入微地展示了印家厚所承受的種種生存壓力、困頓和窘迫,“自我”被茍且的生活壓得喘不過起來。物質(zhì)匱乏狀態(tài)下衣食住行的煩惱,這些煩惱在旁人看來是那么的卑微,但對(duì)于為了生活而奔波的他們卻是那么實(shí)在,他們耗盡心力,在周而復(fù)始的生活循環(huán)中頑強(qiáng)地保持著自尊和韌性。生活永遠(yuǎn)不可能按你的想像進(jìn)行,我們只能咬著牙去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承受生活中的痛苦,然后積蓄力量,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整裝待發(fā)。《煩惱人生》作者融匯了現(xiàn)實(shí)人生的深切體驗(yàn),融入了女性作家體味到的獨(dú)特的“人生蒼涼”。我們都向往詩和遠(yuǎn)方,但現(xiàn)實(shí)只有茍且的生活。
《托爾斯泰圍巾》中“老扁擔(dān)”如同“阿Q”一樣無名無姓,一個(gè)社會(huì)最底層的人,“一個(gè)農(nóng)民工,專門做扁擔(dān),出苦力,搬運(yùn)重物上樓”,這就是“老扁擔(dān)”名稱的由來。從干苦力到收破爛,“老扁擔(dān)”在花苑橋人的心目中就是一個(gè)不愛說話的、很不起眼的可有可無的人物,他“從不主動(dòng)與任何人說話,不打攪任何人,眼神都是怔怔的,沒有光,也不閃動(dòng),萬物都不梢,不掠,一味只是老實(shí)和無害。”這樣的“小”到徹底的一個(gè)人,如此熟悉的一個(gè)形象,似乎一直生活在我們身邊,但似乎從來沒被太多的人關(guān)注,他似乎隨時(shí)都會(huì)消失,卻又隨時(shí)可以看見。貧窮、木訥、寡言的城市最底層的小人物,在城市里艱難地求生存,受到各方面的壓力和欺辱,什么吃苦的活都干,但收入甚微,用最大限度的節(jié)儉挑起養(yǎng)家糊口的重?fù)?dān),生活極其艱辛。
二、尋找存在感的詩意
在大的命運(yùn)已定的情況下,小人物在具體事物上的掙扎就顯得尤為珍貴。《托爾斯泰圍巾》中的“老扁擔(dān)”很是典型。“人的外在形狀,是命運(yùn)安排的,沒有地位,沒有錢財(cái),沒有事業(yè)成就,那都是由不得自己的;唯有人本身的內(nèi)容,可以自己決定。人的本身內(nèi)容,主要是志與氣……老扁擔(dān)不僅僅只為討一口飯吃,他還要表達(dá)他正直不茍的立身,要守護(hù)他作為人的自尊;他要向花苑橋人們證明,他是一個(gè)知錯(cuò)即改的人,是知道道德廉恥的人;如此,他也自然有了凜然不可侵犯的一面。”解決不了溫飽的“老扁擔(dān)”確是特別喜愛閱讀的人,非常喜歡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聽說老年的托爾斯泰離家出走時(shí)圍了一條他喜愛的長圍巾。因此“老扁擔(dān)”自己買了一條“托爾斯泰圍巾”,常年戴著,甚至死了以后還陪葬。
在《黑鴿子》中,莊嚴(yán)說起自己當(dāng)年的戀情“那些日子我最喜歡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當(dāng)然,這種書現(xiàn)在是沒人看了,太古典了,現(xiàn)代人誰還耐煩看它。” 甘于平庸、甘于膚淺,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壓力讓書籍在書架上享受擺設(shè)的地位,讓更多的現(xiàn)代人選擇輕松、詼諧的碎片化閱讀和簡(jiǎn)單的生活方式。
生命如此庸常,“老扁擔(dān)”的生活更是捉襟見肘,但他用詩意的方式擁有了人生的真趣,擁有生命的風(fēng)流。“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池莉通過“老扁擔(dān)”這個(gè)形象重建日常生活的詩性價(jià)值,讓人們重新領(lǐng)略了生存的意義。
生活再也不是簡(jiǎn)單的吃喝拉撒了,在無法回避的人的存在性面前,池莉的作品對(duì)于現(xiàn)代都市文化做了指向性的思考。“一邊活著一邊摸索,一邊參悟一邊改造自己”,現(xiàn)實(shí)人生的體驗(yàn),禪悟更趨于厚重和成熟了。
金蘭芬(1972-),女,江蘇無錫人,畢業(yè)于揚(yáng)州大學(xué)中文系,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育碩士,現(xiàn)任職于無錫旅游商貿(mào)高等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財(cái)會(huì)金融系,副教授,從事當(dāng)代女性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