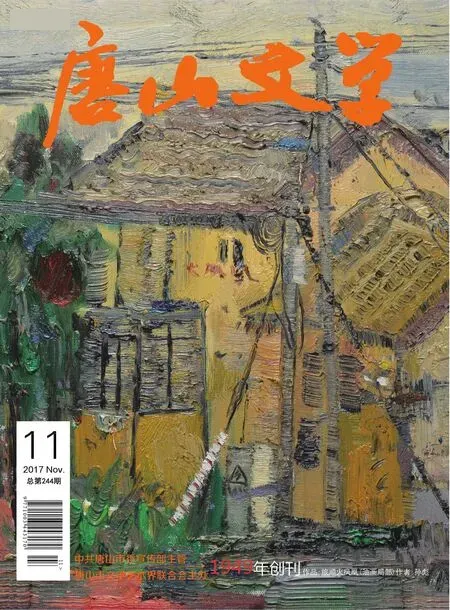《小說課》里的“小說”
金 峰
《小說課》里的“小說”
金 峰
看完畢飛宇的《小說課》,我忽然有一種感覺,畢飛宇的《小說課》不就是一本“小說”嗎。從2012年開始,畢飛宇在南京大學開設小說課,幾年來,小說課已經走出課堂,被登上了文學刊物和大眾媒體,畢飛宇似乎在向更加廣泛的讀者授課,他希望它在更廣闊的當代文學中,開創一點兒新的局面。
寫作30多年,得過魯迅文學獎、也得過茅盾文學獎,畢飛宇可以說是當代作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不僅是一個文學創作者,也是一個研究者。就作品而言,他認為:不是主題大作品就好。中國的當代文學研究,一開始是承襲俄國的研究方式,在宏大概念和歷史切入的方面比較擅長,但在深入文本和小說美學的方面比較薄弱。也就是說,關注作品的外圍越來越多,而對作品內部的關注比較少,似乎給人一種誤解,題材越宏大,作品就越好,但其實并非如此,寫小鎮的就比寫鄉村的好,寫國家的就比寫一個城市的好,寫世界的就比寫一個國家的好,文學不是這么粗暴的。
《小說課》是一堂小說審美的課程。深入文本,關注細節,成為他寫作的追求。幾年來畢飛宇在他的《小說課》中,秉持的是同樣的觀念,他講《促織》,講《布萊克·沃滋沃斯》,也講《故鄉》,他更善于深入到故事的細節中去,發現常人難以發現的東西。畢飛宇說:“其實這也是我一貫寫作的主張,更加注重文學的語言、結構、人物塑造、人物關系的處理等。而且,我也喜歡寫小題材,就小說而言,《三國演義》講的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而《紅樓夢》只是講一個家庭里小兒女們的是是非非,但這不影響《紅樓夢》比《三國演義》偉大的事實。”
畢飛宇愛聊小說,他說:“如果不講課,我還是喜歡跟人聊,但我就變成了一個話癆,現在話癆變成了職業,多好!”不過,畢飛宇講課,并不和別的老師相同,他說:“我講每一部小說,不是從讀者的角度去講,而是從作者的角度去講,去揣摩作者為什么這么寫,為什么這么寫就更好?從教學的角度而言,比如文學史、文藝美學等這些學生必須要學的專業課程,很多老師都教得比我好。我的課無法代替這些基本的課程,但可以做個補充,一個對提升文學審美能力的補充。”
講課多年,畢飛宇的課程很多都發表在公開的刊物上,廣為人知,附帶的效果是,他總是被人問道“寫作究竟可不可以教”?畢飛宇認為:如果想成為曹雪芹,自然不可能教出來,但如果想通過幾年的訓練,提升一下自己的寫作水平,當然可以教。寫作并不像常人認為的,要靠天分,要靠自己多寫。我們有時候太過看重天分這些東西了,但事實上,寫作本身還有很多基本的元素,是需要學習和練習的,從作品的思想性,到寫作的技巧,如人物的塑造、情感的處理、語言的雕琢等。確實有很多作家學歷并不高,但這不代表他們不學習。就如余華,他沒上過大學,但他非常愛看書,他讀的書特別多,和他聊天,古今中外各種流派的作品,他都很了解。盡管他經常說小說誰都可以寫,但實際上,沒有大量的閱讀和學習,怎能獲得現在的成就,所以我經常跟他說,不要說“小說誰都能寫”。寫一個故事確實容易,但想要把小說寫好,卻絕非易事。
本期《唐山文學》照例推出詩歌、散文、小說等作品,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說的創作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十八歲過去了,僅僅是開始》用生動的語言書寫過去,《歌者》以現代手法表現悲傷,做新的嘗試。無論怎樣的創作形式,都是對小說寫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