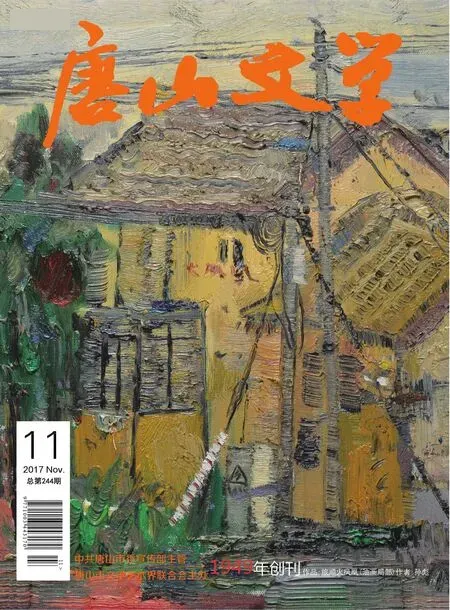論隆學(xué)義川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化”意識(shí)
——以川劇《金子》為例
蔣長朋
論隆學(xué)義川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化”意識(shí)
——以川劇《金子》為例
蔣長朋
劇作家隆學(xué)義在川劇、京劇、話劇、漢劇、黃梅戲、曲劇等多個(gè)戲劇藝術(shù)門類中創(chuàng)作了大量具有廣泛文化影響力和獨(dú)特人文個(gè)性的作品。其中,川劇作品10余個(gè)。其代表作川劇《金子》榮獲了包括曹禺劇本獎(jiǎng)、中國戲劇文學(xué)獎(jiǎng)金獎(jiǎng)、文華大獎(jiǎng)、中國藝術(shù)節(jié)大獎(jiǎng)在內(nèi)的各類大獎(jiǎng)34項(xiàng),至今已演出500余場(chǎng),成為當(dāng)代川劇藝術(shù)舞臺(tái)上一座耀眼的豐碑,被公認(rèn)為“20世紀(jì)末中國戲曲的代表作”。《金子》的脫穎而出,主要源于編劇隆學(xué)義在川劇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堅(jiān)持的“現(xiàn)代化”意識(shí),這也是現(xiàn)代戲曲區(qū)別于傳統(tǒng)戲曲最為核心的精神意蘊(yùn)。
一、人性的現(xiàn)代化
《金子》改編自曹禺名著《原野》。戲曲改編名著,尊重原著是基本原則。隆學(xué)義的《金子》尊重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曹禺原著話劇《原野》以仇虎為主角,寫他的苦難與復(fù)仇。隆學(xué)義改編的川劇《金子》,改換切入視角,將仇虎和金子的主次挪位,以金子的命運(yùn)軌跡展現(xiàn)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環(huán)境下婦女的磨難和掙扎。保留原著的兩條故事線索,把仇虎“復(fù)仇”的主題改為金子“寬容”的主題,將仇虎復(fù)仇、大星戀金、焦母恨媳等重要情節(jié)圍繞金子展開,突出了金子身處漩渦中復(fù)雜的內(nèi)心沖突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強(qiáng)烈愿望。重心轉(zhuǎn)移后,原著中強(qiáng)烈的悲劇色彩并沒有被削弱,反而更加豐富了原著的內(nèi)涵,金子內(nèi)心掙扎所展示的女性的苦難,從人性的角度,表現(xiàn)出更加深刻的反封建的人性呼喚,完成了金子從比較單一的個(gè)性到多側(cè)面、多層次的性格轉(zhuǎn)變。
二、程式的現(xiàn)代化
《金子》能夠取得巨大成功,除了隆學(xué)義在人性開掘上的“現(xiàn)代化”突圍,還有一個(gè)在川劇現(xiàn)代戲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成就——?jiǎng)?chuàng)造現(xiàn)代川劇程式。
戲曲中的程式是藝術(shù)家們通過生活體驗(yàn),并根據(jù)戲曲的美學(xué)特征而創(chuàng)作的,是我國傳統(tǒng)戲曲文化的寶貴財(cái)富。然而,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傳統(tǒng)的表演程式,在現(xiàn)代戲中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和塑造當(dāng)代人物時(shí),就顯得力不從心。例如傳統(tǒng)戲中,騎馬可以用一個(gè)“揚(yáng)鞭”的動(dòng)作展示,那么現(xiàn)代人開車,就沒有特定的程式來表現(xiàn)。這也是董健提到的“現(xiàn)代人思維模式下的話語系統(tǒng)”。川劇程式源自社會(huì)生活,是川劇藝術(shù)家根據(jù)舞臺(tái)藝術(shù)審美要求與規(guī)律,把生活中的自然狀態(tài)加工提煉為舞臺(tái)藝術(shù)形態(tài),與打擊樂、唱腔融為一體,用來塑造人物、表現(xiàn)生活形態(tài)的規(guī)范的、固定的表演方式。隆學(xué)義在《金子》的創(chuàng)作中,在深度挖掘人性的同時(shí),還兼顧了表演手法,以便演員二度創(chuàng)作。比如劇中仇虎醉后把焦大星看成焦閻王,演員變臉技藝便體現(xiàn)得恰到好處。《金子》中常五聽說虎子回來了,演員運(yùn)用踢褶子、矮子功把常五對(duì)仇虎的懼怕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文學(xué)性與動(dòng)作性自然契合。隆學(xué)義在《金子》中對(duì)川劇的現(xiàn)代程式創(chuàng)作,解決了現(xiàn)實(shí)題材與傳統(tǒng)藝術(shù)之間最為詬病的“話劇加唱”的矛盾,對(duì)川劇現(xiàn)代戲發(fā)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和重要的貢獻(xiàn)。
三、審美的現(xiàn)代化
《金子》聲名遠(yuǎn)播,其原因并非是隆學(xué)義復(fù)制了曹禺,而是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符合現(xiàn)代審美的“金子”。相同的題材,在當(dāng)下話劇形式的演出比戲曲更吸引年輕觀眾,在于年輕觀眾更喜歡藝術(shù)的真實(shí)性和快節(jié)奏。曹禺筆下的《原野》講述的是農(nóng)民復(fù)仇的故事,人物較多,情節(jié)復(fù)雜。隆學(xué)義在改編創(chuàng)作《金子》時(shí),在加快戲曲節(jié)奏、充實(shí)劇本容量和適當(dāng)追求真實(shí)性方面下了較多的功夫,對(duì)戲劇結(jié)構(gòu)與舞臺(tái)風(fēng)貌進(jìn)行了改進(jìn)。他選取金子為主線,簡化了人物,重新調(diào)整了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五幕戲中,除一頭一尾,其余三幕均固定在同一場(chǎng)景,在金子、仇虎、焦母及焦大星四個(gè)人物之間展開,將人物矛盾的沖突集中設(shè)置在金子與仇虎的愛情糾葛,升華了戲劇的主題——“金子阻止仇虎復(fù)仇而不能”。通過這樣的處理,使戲曲舞臺(tái)藝術(shù)更加契合現(xiàn)代人的審美需求,摒棄了傳統(tǒng)戲曲演出中節(jié)奏緩慢、情節(jié)拖沓的結(jié)構(gòu)形式,在情節(jié)結(jié)構(gòu)上做到嚴(yán)謹(jǐn)、出新、流暢、明快,準(zhǔn)確把握時(shí)代脈搏,吸納現(xiàn)代觀念及元素,成就了一個(gè)具有現(xiàn)代化審美意識(shí)的川劇作品。
戲曲需要改革,觀念需要革新。川劇文學(xué)生存、發(fā)展的重點(diǎn)也在于創(chuàng)新,如果不服從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規(guī)律和邏輯,拘泥于“三一律”的時(shí)空限制,停留在對(duì)“傳統(tǒng)折子戲”的盲目崇拜中,不敢如隆學(xué)義一般在人性、程式、審美方面注入現(xiàn)代化意識(shí),力求革新和突破,將不利于傳統(tǒng)川劇文學(xué)在當(dāng)下舞臺(tái)環(huán)境中找到合理的發(fā)展走向。在文化繁榮發(fā)展的長河中,只有拓展題材,表現(xiàn)形式多樣化,確立全新創(chuàng)作理念,既要堅(jiān)守傳統(tǒng),又要突破和發(fā)展傳統(tǒng),才能創(chuàng)作出符合現(xiàn)代觀眾審美情趣、貼近觀眾生活,藝術(shù)性、影響力、價(jià)值觀俱佳的川劇文學(xué)新品,使川劇的文學(xué)品格更加鮮明,讓三百年歷史的川劇富有更加長久的文學(xué)藝術(shù)魅力。
本文為2016年度重慶市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川劇藝術(shù)創(chuàng)新發(fā)展視閾下的隆學(xué)義川劇創(chuàng)作研究》(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2016YBYS147)成果之一。
重慶市文化藝術(shù)研究院 40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