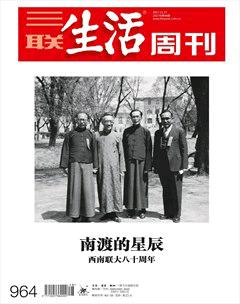錫安重生之路:從《貝爾福宣言》到巴以分治
2017-11-25 14:26:42劉怡
三聯生活周刊
2017年48期
劉怡
猶太民族國家的誕生史,并非一部簡單的熱血傳奇。陰謀與正義、勇氣與狡計、殘忍與犧牲,都可以從中窺見端倪。依靠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國際形勢劇變,消失1800年之久的以色列國終于在巴勒斯坦重生,整個中東世界的發展軌跡自此出現了決定性變化。
從來沒有任何一封政府要員寫給民間人士的信函,曾經引發過如此深遠的影響和層出不窮的爭議。以至于整整100年后,依舊會有人為之激動、憤怒和吶喊。
2017年11月2日,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發表滿100周年之際,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向全球巴裔人士發出倡議:在其所在國的英國使領館附近舉行抗議活動,譴責倫敦當局對巴勒斯坦人“長達百年的放逐”。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3000名抗議者聚集在英國領事館門口,焚燒特蕾莎·梅首相和阿瑟·貝爾福伯爵的紙質人偶。在伯利恒著名的圍墻酒店附近,抗議者頭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面具,向一群巴勒斯坦小難民表示“懺悔”。在耶路撒冷,一位女性示威者拉瓦達·烏達的發言引起了廣泛共鳴:“這片土地不屬于貝爾福。我們巴勒斯坦人將繼續常居于此,并抗爭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是的,在《貝爾福宣言》誕生的1917年11月,巴勒斯坦并不屬于英國或以色列,但阿拉伯人同樣無法以這片土地的主人自居。直到1918年10月底土耳其與協約國簽署《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為止,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巴勒斯坦地區一直是奧斯曼帝國所轄的自治旗。《貝爾福宣言》并沒有把巴勒斯坦的主權許諾給猶太人,甚至也沒有給猶太民族國家的誕生設定時間表。……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瘋狂英語·初中天地(2021年6期)2021-08-06 09:03:24
中國外匯(2019年21期)2019-05-21 03:04:06
作文與考試·初中版(2018年29期)2018-11-19 07:20:44
作文與考試·初中版(2018年32期)2018-10-25 11:44:48
少年漫畫(藝術創想)(2018年12期)2018-04-04 05:29:10
經濟社會史評論(2015年4期)2015-02-28 01:50:09
環球時報(2012-03-24)2012-03-24 14:15:07
探索財富(2009年3期)2009-06-18 03:19:24
探索財富(2009年3期)2009-06-18 03:19:24
英語學習·新銳空間(2008年10期)2008-12-31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