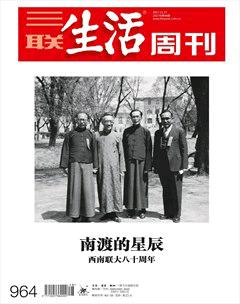《暴雪將至》:被一場兇殺案改變的命運
宋詩婷
年近不惑,導演董越完成了處女作《暴雪將至》。在剛剛結束的東京電影節上,這部電影拿到最佳藝術貢獻和最佳男主角兩項大獎。將90年代的社會背景融入一樁連環兇殺案,在一個小人物身上呈現一代人的命運,這是董越為犯罪類型片找到的新出口。
1997,一樁謀殺案
剛讀完《暴雪將至》的劇本,段奕宏就想起自己小時候的一段經歷。
小學時,學校鼓勵同學利用課余時間撿煤塊、煤渣,撿個一桶半桶,老師就在墻上給貼一兩枚小紅花。段奕宏的集體榮譽感就這樣被培養起來了。一開始,大家上學放學路上都低著頭,專心為集體做貢獻,但沒過多久,煤渣就都被撿光了。怎么辦呢?段奕宏渴望得到小紅花,于是做了弊。他開始從家里的煤庫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偷煤,再假裝是撿來的,上交給學校。“余國偉對榮譽、對體制的追求一下子讓我想起來小時候的這段經歷,我們在追求什么?怎么就走擰了呢?”段奕宏問大家,也問他自己。
段奕宏口中的“余國偉”就是他飾演的電影男主角,一個國有工廠的保衛科科長,一個被時代遺留在過去的小人物。
2013年,導演、編劇董越開始構思《暴雪將至》的劇本大綱。他想寫一個以上世紀90年代為背景的小人物故事。因為對犯罪類型片感興趣,一開始他想以警察的視角來寫,以一個處于灰色地帶的警察為主角,“但把握起來難度太大”。董越曾再三權衡,“首先,我對警察這個職業沒那么了解;其二,寫這樣一個灰色狀態的警察,對整個項目來說,風險太大了,搞不好電影就夭折了,不能冒這個險”。放棄警察后,董越開始尋找一個能與刑事案件相關聯,又不是警察身份的人。找來找去,就想到了保衛科。
保衛科科長,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職業幾乎是第一次以主角面貌出現在華語電影里。“這是一個尷尬的職業,有些小權力,但又不是真正的權力擁有者和執法者。”作為電影的導演和編劇,董越捕捉到了這個職業所能賦予角色的獨特性。

?段奕宏憑男主角余國偉一角,得到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
有了核心人物,故事便徐徐展開。湖南小城,人稱“余神探”的保衛科科長余國偉有個秘密——想擠進體制內,成為真正的警察。一起連環兇殺案讓他看到了機會。他所在的工廠附近,四名女性接連被殺,作案手法一致,兇手指向同一個人。余國偉積極幫警察破案,他用自己的野路子,一度揪出兇手。隨著離真相越來越近,余國偉心中“轉正”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欲望讓他動了歪腦筋,他想利用與自己相好的風塵女子燕子做誘餌,引兇手露面。可惜計劃敗露,燕子含恨而去,余國偉也將憤怒發泄在他心中的疑兇身上。最終,命運與余國偉開了個玩笑,他終于走進了夢想中的警察局,卻是以嫌疑犯的身份。
《暴雪將至》的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兇殺案本身,另一個是大的時代背景。寫一個犯罪故事,這是董越擅長的。在主線故事上,他用犯罪類型片的方式展開情節,參考了很多真實案件,再將它們糅合在一起。
但真正賦予這個故事新意的卻是劇本中關于時代背景的描摹。1997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波及的工廠越來越多。一個個“以廠為家”的普通工人被擋在了工廠大門外。工廠機器被變賣,廠里發不出工資,用物資和產品抵債。曾經打算抱著“鐵飯碗”吃一輩子的工人失去了收入來源,也失去了生活保障。焦慮和空虛默不作聲,卻在每個失去支撐的個體和家庭中蔓延。
《暴雪將至》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為了呈現這一背景,董越不僅營造了真實的工廠環境和生活氛圍,還在主線故事之外安插了一些突顯時代特質的故事和元素。除了連環兇殺案,電影還用兩場戲呈現了另一場兇殺案,男人錯手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并非有深仇大恨,只是男人失業后郁郁不得志,夫妻倆常年爭吵,一怒之下動了刀子。在當年,這類事件并不稀奇。那場余國偉和同事一起被工廠棄之門外的戲也很真實。大門里,領導在點名,門外,全廠職工安靜等待。名字念了十來個,開門迎人,除了點到的,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在這些失去工作的人中,余國偉的故事也顯得沒那么特別了。如果出現在社會新聞里,他的行為和結局與殺妻的男人無異,而他們內心的理想與情感理所當然地將被時代遺忘。這兩場兇殺案,一主一次,恰好能彼此映射。
陰郁的兇殺案,心惶惶的年月,董越用陰暗的影調和下個不停的大雨來制造氛圍和渲染情緒。他是攝影師出身的導演,卻一直警惕一種傾向——形式先行。“沒有具體空間,沒有環境描寫,沒有氛圍,只有故事構架,一個一萬多字的詳細故事大綱。”董越說,《暴雪將至》的劇本是在勘景之后才完成的,影像上的風格和調性也是根據拍攝地的特質建立起來的。
他為電影選擇的拍攝地是湖南省衡陽市,那里也是《暴雪將至》的制片人肖乾操的老家。肖乾操告訴董越,老家或許有可用的工廠場景。一到工廠,董越就果斷確定了拍攝地:“一看就覺得可以用,沒有明顯地被當代元素干擾過,基本設施還停留在90年代,還是當年的風貌。”
勘景的過程中,董越和當地人聊了很多,希望從他們那得到些本地信息。“我們去時還是10月份,秋天,但當地人說,衡陽冬天很濕冷,雨水多。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條件很好,《暴雪將至》故事本身氣質就比較冷,如果影像上可以強化它,那就更好了。寒冷的氛圍也會給人不安全感,人在那種環境里,心理動機就變得更合理了。”董越說,看完景他就決定,把電影的開機時間定在冬天。
雖然,最終電影沒有在冬天開機,但董越還是制造了冬天的環境,用“濕冷”來渲染氛圍。雨幾乎貫穿整部電影,暴雪作為聲音元素,一直出現在電影里的各類廣播中,暗示著危險。

導演董越工作照
作為最重要的隱喻,“雪”只在電影中出現過兩次。一次是余國偉作為勞模上臺領獎,舞臺道具故障,下了一場假雪。另一次是10年之后,余國偉出獄,坐在公共汽車上準備遠走他鄉,遲到10年的大雪終于來了。
片名《暴雪將至》在影像上找到了對應,它不僅指向現實層面的一場大雪,也暗示著急轉直下的人物命運。董越說:“我希望呈現一種荒誕感,荒誕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出現在了不該出現的地方。”
新導演與大演員
《暴雪將至》是董越作為導演的處女作。在剛剛結束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上,這部電影得到最佳藝術貢獻獎,男主角段奕宏也憑余國偉這個角色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
與一位處女作導演合作,對于經驗豐富的段奕宏來說是個冒險的事,相應的,與一位大演員合作,對導演董越來說,也是把雙刃劍。
“初出茅廬的導演沒有保險系數。”段奕宏當然知道,在今天的電影環境下,決定一部電影品質的因素很多,導演的技術和審美是一方面,他的判斷、控制力甚至是情商都能影響電影最終的效果。雖然一拿到劇本,他就從余國偉身上找到了共鳴,但在決定接下這個角色之前,他還是與導演見了兩次,長談幾個小時。“我感受到年輕導演身上那種掙扎感,那種不是很篤定的感覺。創作上的不安全感能帶來更多可能性。當然,即便如此,這個選擇依然是冒了很大風險。”段奕宏回憶自己當初的判斷。
第一部作品就有段奕宏這樣的演員挑大梁,董越當然很興奮。但演員名氣大、資歷深,可控性就不太好估計,很多年輕導演都栽在與演員的溝通上。董越清楚其中的利害關系,所以,兩次與段奕宏見面,也是他對對方的評估:“好演員能帶給你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這非常難得,是個好機會。表演和創作上的分歧不會困擾我,我唯一要把握的就是確定這個人的人格,如果真不是一路人,再有名氣也要換掉,這點上,我還是有堅持的態度。但接觸后我發現,段奕宏很純粹,有了這個基礎,其他創作上的探討就不是問題了。”
董越的判斷沒錯,段奕宏的確是賦予這部電影靈魂的演員。他把余國偉的復雜性詮釋得精準到位。作為保衛科的大人物,作為勞模,余國偉有正義和睿智的一面,作為一個想擠進體制內的小人物,他又有卑微的一面。面對感情和欲望,他掙扎前行,這些他拼命遮掩的掙扎都體現在細微的動作和表情里。
“對于演員來說,如何建立信念很重要,你要相信你演的角色,這樣表演上才能有代入感。”段奕宏說,雖然自己沒在大廠里生活或工作過,但小時候,家附近有個紡織廠,幾萬人,就像一個小城市,外面的人都想進去,那種榮譽感他能理解和捕捉到。
有了信念,還需要抓住細節,這樣才能讓觀眾也相信。和演《白鹿原》《烈日灼心》時一樣,進組前,段奕宏依然去體驗了生活。熱心的保衛科干事帶他在工廠里走一走,還原了很多破案場景。“通過他們,我能去感受一個大廠工人的精神狀態。對于余國偉這個角色來說,把握住那個精神狀態和90年代的時代氣質,這個是最重要的。”段奕宏說。
《暴雪將至》在東京電影節首映后,有當時的群眾演員在網上寫影評,回憶了他參與拍攝的一場餐館戲。那是余國偉第一次與他心中的嫌疑犯面對面,他拿出雨中追兇時對方留下的一只膠鞋,讓眼前的嫌疑犯試穿。董越和段奕宏對這場戲的拍法有分歧,按照兩人不同的理解,這場戲拍了四五種呈現方式。一場幾分鐘的戲,拍了大半天。
“現場的交流和調整太多了,隨時都在變。”董越說,他尊重段奕宏的想法,也堅持自己的理念,他需要在這中間找到平衡。導演和演員,一個從整體上把握故事和視覺,一個從人物出發,兩人出發點不同,但可以互為補充。
剛看劇本時,段奕宏有種擔憂,怕電影最終的呈現更像一個高級的電視劇。“一開始劇本里有很多解釋性的臺詞和表達,很怕觀眾看不明白余國偉和真正的警察之間那種身份的差別,但其實不需要,這些可以用視覺化的東西,靠表演去體現。”段奕宏提到了一場戲,電影一開始,余國偉在案發現場掏出相機拍照,一個警察走上來,沖他屁股踢了一腳,讓他該干嗎干嗎去。“這么早就直接體現這種地位的差別,太外露了。”他更傾向內斂的表演,用余國偉戰戰兢兢要給老警察點煙,警察局里一邊自我表現一邊討好的姿態來體現這種差別。
“拍還是拍了,而且要拍好,最終決定權當然在導演。”讓段奕宏欣慰的是,后來在東京看電影首映時,他發現,導演把那場戲剪掉了,“這說明大家的審美還是一致的。”
董越也是個敏感的人,他知道,段奕宏一度對他持懷疑態度,但這種對新導演的謹慎也是他能理解的。“電影的氣質取決于什么?導演的品位和審美,但在這方面,段老師沒有辦法判斷我。我知道,直到電影拍攝結束,他也是抱著不知道最終會怎樣的心態離開的。直到看完電影首映,他大概才覺得,坐在他邊上的這個菜鳥,電影品位不差。那時起,他可能對我有一些新的認識。”董越說。
年近不惑才完成自己的導演處女作,董越等待了很多年。事實證明,他多年的攝影師和廣告拍攝經歷并非荒廢時間,那些經驗讓他比大多數處女作導演更有控制力和執行力,這些優勢都體現在《暴雪將至》的影像呈現上。
在電影籌備階段,制片人曾幫忙把《暴雪將至》的劇本遞給很多業內人士看。香港一位很出名的制作人看了劇本,約董越聊一聊。“一見面他就和我說,這個劇本很多地方可以刪掉,沒有意義,提到的第一場戲就是10年后余國偉重返領獎禮堂的那場戲。”董越很意外,那場戲他自己很喜歡,那種介于真實與虛幻之間的感覺,暗示著人與真相之間的距離,也有種人走茶涼的滄桑感。“第一反應是郁悶,回家后想了很久,突然興奮起來,因為,這個例子恰巧證明,我與香港電影人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獨特性就來源于這里。這是寶貴的東西,我自己必須珍惜。”
處女作沒有遺憾是不可能的。采訪時,董越不止一次提到,電影里三廠交匯處的小街戲份可以拍得更好,但時間和物力都有限,感情戲也可以拍得更從容一些,作為新導演,有些創作之外的事他還需要積累經驗。
如今,《暴雪將至》為董越帶來的贊美與批評都將成為過去,他唯一看重的是,這部電影之后,他再也不用擔心沒有電影可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