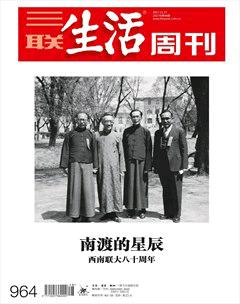“藝術(shù)至少為終極自由提供了一種錯覺”
虔凡
2017年11月,戰(zhàn)后抽象藝術(shù)代表人物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新展“試驗(yàn)與變化”在美國佛州NSU藝術(shù)博物館開幕。橫跨其職業(yè)生涯60年的近300件繪畫和雕塑,“其中有很多作品此前沒有展過此后也不會再展,因?yàn)樗鼈兪俏易约旱氖詹亍缓靡馑迹鼈兪俏姨氖詹亍薄K固乩诮邮鼙究瘜TL時說。
弗蘭克·斯特拉今年81歲。在美國幾乎任何一座重要藝術(shù)博物館的現(xiàn)當(dāng)代收藏中,都會和他的畫作迎面相見。在上世紀(jì)60年代的極簡主義運(yùn)動中,斯特拉開拓性地以“黑色繪畫”(Black Paintings)先聲奪人,之后從立體畫布到拼貼與浮雕畫的結(jié)合,從極簡跨向極繁(Maximalism)……他近60年來的探索實(shí)踐,正是藝術(shù)在時代變遷中的一個縮影。
斯特拉成名很早。1959年,剛剛從普林斯頓大學(xué)歷史系畢業(yè)一年,他就憑借作品“理性與污穢的聯(lián)姻II”(The Marriage of Reason and Squalor II)入選了紐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MOMA)的群展“十六個美國人”。這個展被視為60年代美國極簡運(yùn)動的開端之一,大膽的創(chuàng)作在受到爭議的同時也收獲了很多藝術(shù)評論人的肯定:“毫無疑問他們在‘進(jìn)行創(chuàng)新,舊的形式已經(jīng)不再能夠承載他們的想法”。
斯特拉的畫作在展覽結(jié)束后就被納入了MOMA永久館藏,他的創(chuàng)舉鮮明有力:在對稱構(gòu)圖的大尺幅油畫布上,使用普通家居涂飾的刷子和瓷漆,與筆刷等寬的黑色在背景上平行鋪展而開留出畫布原色細(xì)線的間隔。他拒絕筆觸的表現(xiàn)力,而強(qiáng)調(diào)將畫布識別為一種二維平面融合于三維物體之中的整體結(jié)構(gòu),這種技法以返璞歸真之感讓人聯(lián)想到工廠勞作的方式——用純?nèi)坏慕Y(jié)構(gòu)和抽象的視覺表現(xiàn)繪畫行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