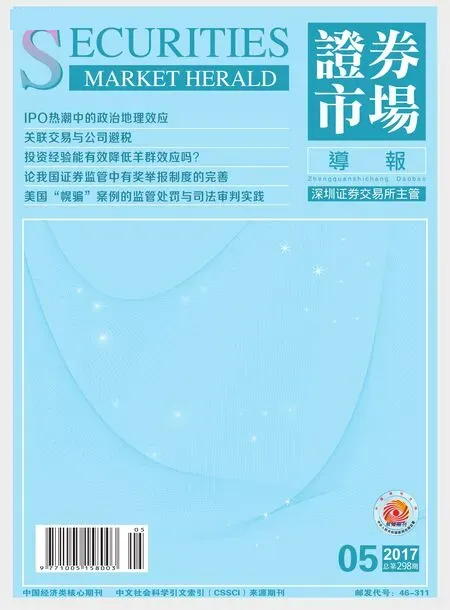投資經驗能有效降低羊群效應嗎?
——以開放式基金的個體為例
(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天津 300350)
引言
在金融學領域,羊群行為是指投資者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的決策,或者過度依賴于輿論,而忽略自己的有價值的私有信息,進而跟從市場中其他人的行為。一般而言,行為金融學家們將其產生原因歸為三類:Scharfstein and Stein(1990)[1]提出的基于聲譽的羊群效應1;Maug and Naik(1995)[2]提出的基于薪酬條款的羊群效應2以及Banerjee(1992)[3]提出的信息不對稱(或信息流模型)羊群效應3。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羊群效應的產生難以完全用上述三種類型進行解釋。Falkenstein(1996)[4]即指出當投資人并非基于委托代理原因、也不受聲譽效應和相應的薪酬激勵政策的影響、且信息也相對透明時,羊群效應仍然存在于資本市場,他認為還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影響著羊群效應的產生。
自Lakonishok et al.(1992)[5]的經典性研究面世以來,目前理論界所形成的一個共識是,缺乏經驗的個人投資者往往容易放棄自己的私人信息而模仿或追隨經驗豐富的投資者,從而產生羊群效應。然而迄今為止的文獻大多直接或隱含地假定投資者的投資經驗與其羊群效應之間的關系大致呈負向的線性關系,即投資經驗的缺乏會導致更高的羊群效應,而投資經驗的豐富會使得羊群效應下降。這顯然忽視了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進一步,已有研究基本是對某類投資者整體羊群效應與其投資經驗關系的考察,而忽視了對投資者個體羊群效應與其投資經驗的分析。此外,已有的文獻都相對忽視了羊群效應的“路徑依賴”特征,而且對于投資者個體羊群效應的衡量方法以及投資者經驗指標的選取上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本文以我國開放式基金為例,對投資者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已有的研究大多認為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是線性關系,投資經驗越多,羊群效應越小,但我們受到Gervais and Odean(2001)[6]所證明的非線性倒U型曲線關系的啟發4,在本文的研究中提出了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可能呈倒U型、U型、N型或倒N型的非線性關系三個假設,并分別給以了詳細的實證檢驗,從而更為科學、嚴謹地揭示了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的內在關系。第二,本文首次從基金個體(而不是現有研究中某類投資者整體)的角度對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從而更為精確地描述出投資經驗的變化對羊群效應的影響過程。第三,本文的研究考慮了行為人與組織的慣性特征,較好地捕捉了羊群行為“路徑依賴”的特征,這是以往研究所忽視的。此外,在具體的投資者經驗指標的選取5和個體羊群行為指標的計算上本研究都給出了一定程度的豐富和改進,從實證角度深化了行為金融的相關研究。
文獻綜述
學界在投資者經驗對投資者行為偏差修正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Smith(1998)[7]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理性經濟人”的假說,認為經濟人可以從過去經驗中學習,更正原有非理性行為的錯誤。沿著這種思路,國內外學者就過往經驗對處置效應(Feng and Seasholes, 2005; Costa et al., 2013)[8][9]和過度自信(Menkhoff et al., 2010)[10]等非理性行為的影響分別做了理論與實證上的研究。
而對于本文所關注的投資者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關系這一視角,目前學界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研究。Gloede and Menkhoff(2014)[11]發現投資經驗不僅能有效降低處置效應與過度自信水平,還能抑制投資者的羊群行為。Chevalier and Ellison(1999)[12]通過理論推導得到了基金經理越缺乏經驗,羊群行為越嚴重;Menkhoff et al.(2004)[13]則發現,隨著投資者投資經驗的增長,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會顯著降低;Venezia et al.(2011)[14]更進一步發現,富有經驗的投資者羊群效應往往較低,缺少經驗的業余投資人則羊群效應較高,而且這種現象是持續性存在的。國內學者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且多為定性描述(如蔡慶豐等人,2011;饒育蕾等人,2012)[24][29],缺乏實證上的證據。
以上從處置效應、過度自信和羊群效應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文獻,其研究結果都表明投資經驗的增長能有效地降低投資者的行為偏差,換言之投資經驗與非理性行為之間是一種負向的線性關系。但也有學者對兩者的關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Gervais and Odean(2001)[6]的模型表明隨著經驗的增多,投資者的過度自信水平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Locke and Mann(2001)[15]進一步通過實證檢驗支持了Gervais and Odeans的理論。譚松濤(2013)[32]發現在控制了歷史投資表現之后,股民的投資經驗對其過度交易的影響并不顯著,過度交易或者過度自信并沒有隨著股民投資經驗的積累而得到減弱。
總結以上文獻,一方面,國外現有的文獻雖然在投資經驗對過度自信、處置效應或某類投資者整體羊群效應影響的研究上較為豐富,但對投資者個體羊群效應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的研究較為缺乏,這導致在研究中缺少了對個體研究對象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欠缺完整性的;另一方面,現有文獻對于投資經驗與非理性行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存在分歧的,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們是以線性視角還是以非線性視角看待投資經驗對非理性行為的影響——至今為止的大多數研究都采取了簡單的線性視角,這無疑限制了研究結論的準確性。進一步來看,目前國內相關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缺乏實證考察我國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關系的研究,制約了對我國市場中羊群效應產生原因的進一步認識,從而導致當前我國仍然缺乏具有針對性的治理對策。
受到Gervais and Odean(2001)[6]投資經驗與非理性行為(過度自信)存在非線性關系研究以及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26]對個體羊群效應衡量方法的啟示6,本文以我國開放式基金為例,利用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偏股型開放式基金的季度數據對投資者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非線性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期拓展和深化對羊群行為產生的原因與機制的討論。
研究設計
基于已有的對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的研究,本文參考了Chen et al.(2007)[16],Nicolosi et al.(2009)[17]以及Greenwood and Nagel(2009)[18]對投資者經驗的研究成果,改進和發展了一些新的衡量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的指標。在衡量羊群效應時參考了Lakonishok et al.(1992)[5]的LSV模型對羊群效應程度衡量的思路,并結合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26]對個體羊群效應的衡量方法,建立了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的計量模型。
一、投資經驗的定義和測度
綜合已有的文獻,我們認為所謂投資經驗,是指投資者親自參與,從多次的投資實踐中不斷學習和積累所得的投資知識或者技能。一般而言投資者投資股票種類越豐富,交易次數越多,獲得的經驗則越多;同時投資者從事投資研究與實踐的時間越長,其投資經驗也會越豐富。據此本文提出如下與投資經驗相關的指標:
1.股票種類累計(SS)
股票種類即為投資者購買股票的種類數目累計。Nicolosi et al.(2009)[17]認為投資者投資股票種類越豐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在股票市場獲得經驗越多。本文結合機構投資者的特征,以機構投資者持有過的前十大重倉股的累計值7來作為股票種類的衡量指標。
2.交易次數累計(TT)
Chen et al.(2007)[16]認為一個投資者交易越頻繁,交易次數越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獲得的經驗則越多。本文以前十大重倉股的交易次數累計作為代表。
3.基金成立時間(FT)
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實踐中會形成自己的文化、管理制度以及數據積累等,這些將對投資經驗的形成產生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基金的成立時間代表。
4.基金經理的從業時間8(MT)
基金經理經驗將融入于整個機構的投資經驗,對機構的投資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使用Resset數據庫的基金經理從業時間作為其經驗的一個衡量指標。對于有多個基金經理的季度,本文采用了加權算術平均數。
進一步的,本文綜合上述股票種類累計、交易次數累計、基金成立時間以及基金經理從業時間等因素,采用因子分析構造表示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的綜合指標EX。因子分析是變量降維的一種方法,主要用于從具有大量數據的多個原始變量中提取綜合處較少的新變量,本文使用因子分析的目的在于將四類經驗指標合并濃縮為單個具有解釋力度的綜合指標。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變量標準化。由于交易次數、基金成立時間等指標值均是客觀數值,因此為避免量綱造成的不利影響,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我們先將四類經驗指標進行標準化(采取正態分布標準化法),將其轉為標準變量。
第二,提取公共因子。利用Stata,我們將四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來判斷所需提取的公共因子的數量。從Stata報告的結果來看(見表1),前兩個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其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7.35%,表明前兩個公共因子反映了87.35%的原始信息,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度。因此綜合來看,兩個公共因子是較為合適的選擇,假設分別為F1與F2。
第三,確定因子載荷矩陣與因子得分。在上述基礎上,我們再利用方差極大正交法對因子進行旋轉,從而得到了因子載荷矩陣(表2)。從因子載荷矩陣來看,F1在交易次數(TT)、股票累計值(SS)、基金成立時間(FT)上具有較高的載荷,而F2僅在基金經理從業時間(MT)上有較高的載荷。前一個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從基金主體出發顯示的投資經驗,后一個因子則反映的是從基金經理個體出發顯示的投資經驗。依據表2所示的因子載荷矩陣,可得兩大公共因子F1及F2與四個經驗指標之間的關系,具體可表達為:



表1 累計方差貢獻率與特征值

表2 因子載荷矩陣
二、羊群效應指標(HM)
目前對羊群效應的衡量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基于LSV模型,該模型由Lakonishok et al.(1992)[5]提出,以某只股票的買家占交易總數的比值為計算對象;另一種是基于Christie and Huang(1995)[19]使用的CH模型,該模型運用股票收益的橫截面離散度(CSSD)來計算羊群效應值。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羊群效應的存在性以及羊群效應的計算方法進行改進完善,取得了諸多成果(如孫培源和施東暉,2002;董志勇和韓旭,2007;田存志和趙萌,2011)[31][25][33]。但上述研究和方法都無法精確的描述交易者個體的羊群效應,導致無法計算出每一階段羊群效應的變換值。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26]利用分割聚類的矩陣化方法對羊群效應進行測算,使衡量投資者的個體羊群效應成為了可能。本文借鑒LSV模型衡量羊群效應的思路,參考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26]分割聚類的矩陣化方法9,設計出如下的計算方法:
1.建立持倉矩陣HSt
投資者j第t期持有股票i的數量作為持倉矩陣的基礎,持倉矩陣HSt構造如下:

其中,m為投資者個數,n為股票只數,bj,t,i為投資者j第t期持有股票i的股數。
2.在(3)式基礎上進一步構建動態矩陣
即第t期和t-1期持倉矩陣的差作為變動矩陣:

為了進一步衡量投資者買入方向的羊群行為(以下簡稱“買入羊群”)和賣出方向的羊群行為(以下簡稱“賣出羊群”)的情況,構建增倉矩陣和減倉矩陣:

如此便形成了增倉矩陣和減倉矩陣的線性可加等式,即DHSt=BDHSt+SDHTt。
3.構建衡量羊群效應的矩陣


其中Mt=(bmj,t,i),SMt=(smj,t,i),分別表示買入羊群效應和賣出羊群效應,從而羊群行為以集中交易的方式得到衡量,越集中羊群效應值越大。
4.個體羊群效應的衡量
假設個體羊群效應的表達式為HMt,j,則個體羊群效應的值為當期具有買入與賣出羊群行為傾向的股票數與當期總交易股票數,表達公式如下:

其中,numt,j表示投資者j在第t期持有的具有羊群行為傾向的股票數量,numt,j表示投資者j第t期的總交易股票數。
三、控制變量的選擇
參考潘越,戴亦一和陳梅婷(2011)[28]、蔡慶豐、楊侃和林劍波(2011)[24]、胡赫男和吳世農(2006)[27]等人的研究,本文控制變量的選擇如表3所示。
四、研究假設與檢驗模型
以往的研究表明,投資經驗越豐富,羊群效應越低,但是根據Gervais and Odean(2001)[6]的理論研究與Locke and Mann(2001)[15]的實證檢驗,投資經驗與投資者過度自信程度呈現倒U型的關系。那么同樣作為投資者行為偏差的羊群效應,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是否也呈現倒U型關系呢?換言之,機構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是否也會如過度自信這一非理性行為一樣隨著經驗的積累而先升后降呢?進一步來看,如果上述倒U型關系不成立,又是否意味著機構投資者的羊群效應與其投資經驗之間是正U型關系——隨著投資經驗的積累其羊群效應先下降后上升呢?為解答以上的疑問,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假設。

表3 控制變量
假設1: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呈倒U型曲線關系;
假設2: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呈U型曲線關系。
為驗證以上假設,我們設計了以下模型來檢驗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其中,HMt,j為機構投資者個體羊群效應的表達式,EXt,j表示投資者投資經驗,Sizet,j表示基金的規模,Ratet,j表示基金的績效水平,Sext,j表示基金經理的性別,Stylet,j表示基金的投資風格,Edut,j為基金經理的學歷水平,Modet,j表示基金的管理模式。在模型(7)式中,若系數β2與β1顯著不為零,則依據β2的符號可以對投資者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的關系做如下判斷:(1)β2<0,則說明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即在投資經驗小于某一拐點時,投資經驗會助長機構投資者的羊群行為,但隨著經驗的進一步提高超過門閥值后,投資經驗會有效的降低羊群效應;(2)β2>0,則說明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呈現正U型關系,即投資經驗會在拐點前抑制投資者的羊群行為,超過拐點后,投資經驗會提高羊群效應。
在模型(7)式中,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值使用的均是當期值,這意味著機構投資者的羊群行為會受到當期投資經驗的瞬時影響,不存在滯后效應。但是現實情況并非如此理想。一方面人的行為具有行為慣性,人在一段時間內的行為具有穩定性與一致性;另一方面組織也存在行為慣性,在面對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時,組織往往不能及時的改變傳統的行為以適應市場的變化。即無論是從基金經理還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角度,他們的投資行為均會表現出“路徑依賴”特征,前幾期的羊群行為會對當前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羊群效應變化的滯后效應進行考察。具體方法上,本文計劃利用局部調整模型的思想對上述滯后效應進行闡述。
考慮如下的局部調整模型10:

其中,HM*t,j表示羊群效應的期望水平,即我們所預期投資經驗對羊群效應所達到的作用水平,θ是常數項,Xt,j為(8)式各解釋變量所組成的向量,s是其系數向量,δ為擾動項。(8)式表明各變量的當期水平影響著機構投資者羊群效應的期望水平。由于投資者存在行為慣性,我們所預期的羊群效應值不會在短期內實現,而是需要一定時間讓投資者逐步調整,使當期水平向期望水平靠攏。這正是局部調整模型的假設:因變量的實際變化只是預期變化的一部分。用公式表達如下:

其中,λ1與λ2為調整系數,表示實際羊群效應向期望羊群效應調整的速度。本文采用了二階局部調整模型,即當期羊群效應的實際值是期望羊群效應與前兩期羊群效應的加權和。與傳統的一階局部調整相比,該模型能更好地捕捉機構投資者羊群行為的慣性,消除擾動項的序列相關問題,保證后面動態面板模型的設定準確。
結合(8)式和(9)式可得:

其中θ*=λ1θ,s*=λ1s,δt,j*=λ1δt,j。s*為短期乘數,反映解釋變量對羊群效應的短期影響,s為長期乘數,反映解釋變量對羊群效應的長期影響,λ2與(1-λ1-λ2)為滯后乘數,反映前兩期羊群效應對當期的影響,即表示滯后效應的大小。(10)式所表示的動態面板模型即本文進行實證檢驗將要采用的基本模型形式,具體表述為:

另外,盡管我們依據前人的文獻提出倒U型與U型假設,但如果這兩種假設都不能通過檢驗,也不意味著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必然呈線性關系,因為機構投資者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仍然有可能存在“N”型11或倒“N”型12的三次曲線關系。為保證本文前兩個假設的穩健性與嚴謹性,就需要通過多種計量分析方法與檢驗方法對其他曲線關系存在的可能性進行驗證。為此,我們提出第三個待檢驗假設。
假設3: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呈現三次曲線關系。
為對假設3進行檢驗,我們在(11)式中加入三次項形成(12)式:

在(12)式中,若β4顯著不為0,則說明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確實存在三次曲線關系,然后我們可以再根據β2、β3與β4的具體情況來做進一步的判斷。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介紹
本文樣本選取時間為2010年1季度到2015年4季度,按季度劃分為24個子觀察期13。期間,我國股市經歷過完整的熊市和牛市階段,為我們研究羊群效應提供了絕佳的市場背景。數據選取了這段時期我國A股市場所有的偏股型開放式基金為研究樣本,剔除了每期累計交易次數為0的樣本,另外還剔除了部分缺失數據樣本。在投資組合的股票樣本選取中以機構投資者的前十大重倉股為研究對象。最后共獲得了166只基金24個季度共3984個研究樣本。本文所有的數據均來自Resset和Wind數據庫。

表4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4給出了本文實證模型所涉及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的統計性分析
為直觀的展現機構投資者羊群效應與投資經驗之間的關系,表明基金個體羊群效應與投資經驗之間的U型曲線關系,我們先對其進行統計性分析。考慮到單只基金不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我們在每個季度對166只基金的羊群效應及投資經驗取均值,得到一組共24個季度的羊群效應與投資經驗組合值,我們可以把其看作市場中偏股型基金的典型代表。然后我們將羊群效應與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置于同一張圖中(圖1),縱軸代表羊群效應,橫軸代表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
從圖1看,投資者的羊群效應與其投資經驗呈現較為明顯的U型關系。羊群效應在投資經驗較為缺乏時處于高位,隨著投資經驗的積累,羊群效應逐步降低,并曾一度低于0.1,但當投資者投資經驗進一步增強時,羊群效應開始逐漸回升,但低于缺乏投資經驗時的羊群效應值。這說明投資經驗對羊群效應的影響是有限且復雜的,尤其是在U型曲線的后半段,羊群效應逐漸回升至低于缺乏投資經驗的水平,很有可能是因為投資經驗對羊群效應的邊際效果在逐步遞減,使得其他增強羊群效應的因素在與投資經驗的博弈中占了上風。
三、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的回歸分析
在(11)式與(12)式中,解釋變量中含有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而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與殘差項有可能存在相關性,采用傳統的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時,容易產生內生性問題,因此,我們主要采用Windmeijer(2015)[20]所提出的改進后的兩步系統GMM14對各模型進行估計,此外,為保證檢驗的穩健性與嚴謹性,我們需要采用多種不同的計量方法對可能出現的曲線關系進行檢驗。因此,除了采用能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系統GMM外,我們還利用靜態15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LS)、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固定效應(FE)、隨機效應(RE)等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力求從多種實證角度對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的關系進行刻畫分析。表5是各實證檢驗方法回歸結果。

圖1 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U型關系圖
針對表5所示的實證結果我們做如下分析。首先我們對假設3進行檢驗。在模型1中,我們采用基于動態面板模型并能有效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系統GMM16,對引入投資經驗三次項的(12)式進行參數估計,結果顯示,投資經驗的三次項系數并不顯著,而一次項與二次項系數均顯著為正。因此我們排除了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呈現“N”型或倒“N”型關系的假設3。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專注于對“U型”與“倒U型”關系進行多種計量角度的檢驗。
與檢驗假設3相似,我們首先也分別利用靜態NLS與系統GMM對假設1與2進行驗證。模型2的回歸結果表明,投資經驗一次項與二次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表現出正U型曲線關系。而在模型3中,我們報告了能考慮變量動量效應且能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系統GMM法的參數估計結果17。從參數估計結果來看,投資經驗一次項與二次項的系數同樣均顯著為正,正U型曲線關系仍然存在。以上分析結果清楚地表明,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確實存在U型曲線關系,且估計結果十分穩健,很好地驗證了假設2,即隨著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驗的增長,羊群效應會逐漸降低,當投資經驗增長至某一閥值時,羊群效應達到最低,此后經驗的繼續增長并不能減輕羊群行為,反而會助長羊群行為。

表5 羊群效應對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回歸估計結果
其次,為進一步檢驗內生性問題在羊群效應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們還分別報告了靜態POLS,靜態FE,靜態RE三種被各類文獻廣泛使用的估計方法,將估計結果與系統GMM估計結果進行對比,從而對內生性問題的影響程度以及GMM估計方法的穩健性程度進行考察18。通過比較分析可知,除模型4外,模型5與模型6的有更多的控制變量呈不顯著狀態,特別是最為重要的投資檢驗的二次項系數,模型4與模型5中僅在5%的顯著水平上顯著,t值也小于模型3所報告的2.78,而與模型3相比,模型6中投資經驗的二次項系數雖也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但其t值要略小于模型3,且有部分變量系數符號與模型3、4、5也存在差異,說明采用系統GMM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內生性問題,獲得最優最有效的參數估計結果。
最后,我們再看羊群效應與各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表5可以看出,在6個模型中,基金的規模與羊群效應成負相關關系,基金規模越大,羊群效應越低。一方面是因為規模更大的基金一般具有更強的投研能力,往往能在市場中發現小規模基金所不能挖掘的新的優質股票,另一方面是因為較大的規模給基金經理提供了更多的配置資金,使資產更為分散化。而基金的業績與羊群效應成正相關關系,基金業績越好,羊群效應越高。這可能是由于基金以往較高的業績使基金經理在進行資產配置時產生了“路徑依賴”,將資金集中于某些股票。從6個模型綜合來看,基金經理的性別、以及基金的管理模式并不能對羊群效應造成影響,多個基金經理共同管理一支基金并不能減輕基金的羊群行為。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本文使用多種檢驗進行輔助19,其基本結果均表明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之間存在顯著的正U型曲線關系,即羊群效應會先隨著投資經驗的增長而降低,然后在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達到某一臨界值后,羊群效應會隨著投資經驗的增長而提高。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曲線關系,我們認為存在以下原因:
在臨界值前,投資經驗的增長抑制了機構投資者的羊群行為。這是因為一方面,機構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伴隨著投資經驗的不斷增長,對資本市場的了解也會更加深入。通過對過去投資經驗的學習不斷吸取教訓和積累經驗,投資者可能會對自身擁有的有價值的私有信息更為重視而不容易被他人的決策或者輿論所左右,從而減少了非理性的羊群行為,這也從本文的角度驗證或支持了Gervais and Odean(2001)[6]的結論:投資者的投資經驗與其過度自信程度之間是倒U型的關系——正是由于在經驗不斷積累的初期投資者過度自信程度不斷上升,才使得投資者越來越相信自己所擁有的信息和能力,從而追隨他人的羊群效應逐漸降低。另一方面,交易經驗的累積伴隨著投資者的預測能力的提升(Hartzmark,1991)[23],或選股能力和擇機能力的提升(Nicolosi and Peng, 2009)[17],或三者同時得到提升,這些投資能力的提升也會使得羊群效應出現下降,從而使具備上述能力的投資者可以戰勝其他投資者獲得更好的投資表現。
然而學習效應所帶來的好處并不能持續。隨著投資經驗的進一步積累,投資者的羊群效應程度開始上升,投資者由最初的“初生牛犢不怕虎”和逐漸的過度自信,而變得日益謙和甚至“自卑”——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信息和經驗轉而去追隨他人的投資行為。究其原因,行為金融給出的產生羊群行為的三大經典原因——聲譽效應、薪酬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效應,恐怕是在此階段之后才開始發揮作用。
結論與啟示
隨著行為金融學的發展,解釋羊群效應成因的傳統的三種模型越來越難以令人們完全信服,特別是有關文獻所揭示的投資者經驗與非理性行為之間會呈現非線性關系的結論,讓我們有理由猜想:羊群行為會受到投資者經驗的影響,且這一影響可能也并非是已有研究所(隱含)假設的線性關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從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與羊群效應的關系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資本市場進行了一次實證檢驗。我們發現:投資者的羊群效應確實受到投資經驗的非線性影響,即:隨著機構投資者投資經驗的增加,機構投資者的羊群效應會先降低后提高,羊群效應與投資經驗兩者呈現出正U型曲線關系。
本文的研究和結論帶給了我們如下的理論啟示。第一,支持了已有文獻關于經驗會影響投資者羊群行為的結論,特別是以實證證據拓展了Gervais and Odean(2001)[6]的理論結論——投資經驗不僅僅如Gervais and Odean(2001)[6]所證明的對過度自信產生倒U型的非線性影響,也會如本文所揭示的對羊群效應產生U型的非線性影響。第二,已有研究發現投資經驗的增加會導致羊群效應的下降是有條件正確的,該條件即是當投資經驗的積累還沒有超過閥值之前,而一旦投資經驗的積累超越了閥值,經典的三大效應對投資者采取羊群行為的激勵可能更大。換言之,經典的三大效應對投資者羊群行為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度,而諸如投資者經驗或學習效應的因素也并不完全。因此,任何非理性行為可能都是各種因素綜合或先后發生作用而導致的,要想更為全面地揭示這些因素,就需要我們更多地采取非線性的視角而對線性思維更為謹慎。
此外,基于本文所得結論,我們應該意識到,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具有不同程度上的羊群行為,他們羊群效應的大小既與投資經驗、基金規模、基金業績等因素息息相關,也與委托-代理關系、聲譽、信息流等三大效應有緊密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我國資本市場羊群效應偏高這一事實歸咎于市場投資者投資經驗的缺乏,任何一個市場都隨時有新的即欠缺經驗的投資者入市,這就導致即便在一個較為成熟的市場(如美國)中,羊群效應等非理性行為也會一定程度地存在(Lakonishok et al., 1992)[5]。并且即使市場中富有經驗的投資者占大多數,羊群效應仍可能處于較高的水平。因此,一方面我們永遠不要奢望在一個市場中完全地消除非理性行為——羊群效應恐怕就如投機因素一樣,是與一個正常運轉的市場相伴而生的;另一方面我們既要不斷提高投資者的投資經驗,如加強對基金經理的在職培訓、改善機構投資者的結構與質量(如培育一大批有著自己獨立的投資風格、定位長期投資、立足長遠發展的機構投資者)等,又要加強制度建設。特別是考慮到本文所發現的投資經驗到達某一臨界值后反而會助長羊群行為這一現象,更需要我們著力于制度建設,如通過約束-激勵機制改善委托-代理問題、通過強化機構投資者監管降低信息不對稱,以及改革目前的契約型基金使其轉變為公司型基金,以便通過引入股權、期權完善基金經理的薪酬制度等。
最后,考慮到中國資本市場優質的投資對象依然過于稀缺這一現實,投資者不得不采取“扎堆取暖”的策略。因此,完善證券公開發行制度與退市制度,提高發行人信息披露質量,培育更多優質的上市企業,以供投資者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多樣化投資,無疑將對中國證券市場羊群效應的減少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釋
1.市場上存在聰明的基金經理與平庸的基金經理,聰明的基金經理比平庸的基金經理有更強的能力與更好的業績,平庸的基金經理為維持其聲譽,會選擇模仿聰明的基金經理的投資行為,從而產生羊群效應。
2.Maug and Naik(1995)[2]的模型假設一個風險厭惡的基金經理,他的報酬與基準經理人的業績表現有關,若他的業績表現低于基準經理人的業績表現,則薪酬水平較低,反之則高,所以與聲譽模型類似,基金經理有動力去模仿基準經理人的投資行為,從而產生羊群效應。
3.Banerjee建立了一個序貫決策模型,在模型中,先驗看法相同且風險中性的投資者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投資,在投資前,所有投資者都獲得了關于資產的信息。若前幾個投資者投資選擇相同時,后面的投資者會忽略自己收到的信息,而選擇跟隨前面的投資者,因為前面幾個投資者收到相同錯誤信息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如此便產生了羊群效應。
4.Gervais and Odean(2001)[6]研究了學習偏差對過度自信的影響,并從理論上證明了過度自信與投資經驗之間大致呈現一種倒U型曲線的關系的,即初期經驗少時投資者過度自信的程度較高,之后隨著經驗的增加其過度自信的程度逐漸降低。
5.已有文獻大都只采用了一個或兩個經驗指標,而本文基于全面性考慮,對各文獻所用指標進行了總結,選出了四個主要指標,并利用因子分析構造出一個綜合指標來衡量投資經驗。
6.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26]較早提出了基于分割聚類的矩陣化方法研究投資者個體的羊群效應,但在其具體的指標設計和計算方法上還存在缺陷,詳見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
7.首先,基金季報只公布前十大重倉股的數據;其次,前十大重倉股在基金占有很大比重,具有代表性,我國基金持倉數量平均約為80只,但前十大重倉股的市值就占了41.56%。
8.Greenwood and Nagel(2009)[18]以及潘越,戴亦一和陳梅婷(2011)[28]在衡量基金經理的投資經驗時采用基金經理的年齡這樣一個指標,但當前我國對基金經理年齡的披露很不完整,因此本文的指標更為精確。
9.但對具體計算方式進行了較大改進。第一,本文使用持倉股數代替原文使用的持倉比率,因為持倉股數的變化方向就能說明投資者的買入或者賣出行為了,與后文使用的聚點值對應;第二,李學峰和李佳明(2011) [26]在均值聚類的時候,采用矩陣每一行的增減倉數據,這樣計算不盡合理,因為既然是增減倉了,已經反映該只股票的交易分類方向了,本文采用了聚點均值分類,詳細介紹見正文。
10.以往的研究并未考慮到行為人與組織的慣性特征,本文的局部調整模型能較好地捕捉這種行為慣性。
11.即投資者的羊群效應隨著其經驗的累積出現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情況。
12.即投資者的羊群效應隨著其經驗的累積出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情況。
13.由于本文的投資經驗指標涉及到累計求和,因此本文的累計購買次數和累計購買股票種類均從2002年1月1日開始計算。2001年9月我國第一支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成功發行。
14.根據權重矩陣的不同,系統GMM可分為一步和兩步估計。Blundell and Bond(1998)[21]指出,相對于一步估計,兩步估計是漸進有效的,但存在估計量標準誤向下偏誤的缺點。而Windmeijer(2015)[20]所提出的改進后的有限樣本標準差估計能有效地對兩步法估計誤差進行糾正,使得兩步法比一步估計更為有效。
15.按是否包含被解釋變量滯后項,可分為靜態、動態估計。
16.我們也采取了非線性最小二乘法對含三次項的模型進行了回歸,結果與模型1一致,三次項系數并不顯著,一次項與二次項顯著不為零,在此受限于篇幅,實證結果略。
17.采用動態固定效應(FE)進行估計的參數估計結果與模型3一致,進一步證實了U型曲線關系的存在,受限于篇幅,實證結果略。
18.類似的比較分析思路也被一些文獻所采用(邵帥,2013;Bjorvatn et al., 2012)[30] [22]。
19.上文分析中我們使用了系統GMM、非線性最小二乘法與混合最小二乘法等多種回歸方法進行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