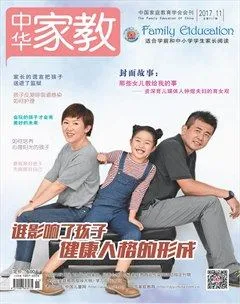曹文軒 父親的身教影響了我的人生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先生在做客《朗讀者》節目時說,他寫的《草房子》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中的桑桑與桑喬的父子情,便是他和他父親情感的真實書寫。寫它,他有一種沿著寬闊的父愛之河順流而下的感覺,這是一次感情復活,一次感情回放,也算是他對這種的感情的膜拜、深深敬意和紀念。

父親創造了我的寫作史
我的寫作興趣、寫作能力與父親密不可分,是他創造了我的寫作史,沒有他也就沒有這樣一部只屬于我的寫作史。他的作用確實無法估量。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而寫小說的人必備本領就是他得有一種出色的說事能力,用行話講叫“敘事能力”。這個能力與父親有關。我父親在那個地方有著崇高的威望,這是因為他一生與人為善,他執掌的學校給那個地方帶來了極大的榮譽。還有,就是他非同尋常的說理能力。經常發生宗族矛盾、家族矛盾、鄰里矛盾,一旦發生就難以平息。而解決矛盾的人往往就是我的父親。他被請去,最后他用天下人應當遵循不悖的道理說服了看似勢不兩立的雙方。
童年時,我就能感知到父親在用道理征服人心之后的那番快意。我母親評價我父親的說理能力是:能將打谷場上的石磙說得自己豎立起來。而我父親的說事能力更令我著迷。我父親的外號就叫“小說家”。他一旦出現在人群中,馬上人群就向他圍攏過來,圍攏過來是要聽他說事——說故事。他說故事,不加任何表演,神態自若。完全憑借語言的力量、細節的力量、故事起承轉合的力量,還有故事中暗含的道義的力量。我記得許多故事,他已經說過許多遍了,但人們還是聽得興致勃勃。我后來寫小說,許多素材就是來自他當年的說的那些故事。有些素材我沒有來得及用,別人先一步用了。當然,關鍵還不是父親給了我大量的寫作素材,而是在潛移默化中,我的敘事能力在他的說事中悄無聲息地養成。
父親讓我有了進北大的機會
北大,父親,于我而言,都恩重如山。是父親讓我有了進北大的機會。當時北大到鹽城招生,只有一個圖書館系的名額。招生的王老師,我要一生感激她,是她從我的檔案中看到我喜歡創作,并已發表作品,立即將我的檔案拿在手中再也不肯撒手。我到北大圖書館系學了一個多月的圖書分類法,一天學校通知我轉系——轉到中文系學習,理由是我喜歡寫作并能寫作。
喜歡寫作,也能寫作卻與父親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父親實際上一路上都在罩著我。是父親讓我交上了到北大讀書深造的好運。這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北大給了我知識,而知識培養了我的眼力,發現從前、發現現在、發現父親的眼力——這一點太意味深長了。
與父親的第一次告別
鹽城水鄉到北京大學,是我人生中和父親的第一次告別—— 一次真正的告別。我終于要遠去了,甚至可能永遠也不能再回到他生活的地方。這一點,他也許知道得很清楚。他當然舍不得我的離去,但內心又充滿喜悅和幸福。我的離去,無疑也是他所期盼的,他終于看到了他的收獲——上北大,在他看來,是這個家的光彩,是他一生的榮耀。他不想挽留,也無法挽留,現在他要做的就是讓我體面地上路。那時,我家很窮,幾乎一貧如洗,我甚至連一只隨行的箱子都沒有。
他拿出了一塊珍藏了許多年的木材,請木匠給我做了一只漂漂亮亮的箱子。箱子做成后,是他親自刷的油,刷了好幾遍油。那箱子裝了我的書本,裝了我的各種物件,也裝了一段永生永世難以忘懷的人生,與我一起離開了父親、家人、村莊和那邊風景獨特的田野。我是坐輪船離開的。至今我還記得父親站在岸上送別的樣子,那時已經是秋天了,水上到處飄著落葉。當時心里很難過,但我知道,分離,告別——告別無處不在,也不必難過,該難過的只怕是無處告別。

父親對我要求嚴格
父親是一個對我要求十分嚴格的父親,我吃過他的巴掌,甚至吃過他的棍棒。但我不會像今天的孩子去記仇,因為那時候的輿論沒有教會我們去記仇,而是恰恰相反。如今回頭檢點自己,依然會心悅誠服地說:該打,不打完蛋!是父親將我打到了正道上。時代不同了,對打的定義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然,在父親的教育韜略中,棍棒并非是日常選項,也不是主要選項,只是到了非棍棒不可時,才使用,用一回是一回。當然,父親根本影響了我人生的,肯定不是棍棒,甚至不是言傳,而是無時不在的身教。與人為善、扶危濟困、寬容大度、吃苦耐勞、不屈不撓、積極向上……這一切,也許我并沒有全部做到,但父親教給了我。
也就是在最后一次棍棒之后不久,在我頸部已經存在了好幾個月的腫塊,被城里醫院診斷為不治之癥。是父親帶我去的醫院。記得有好幾個醫生十分仔細地摸了我脖子上那個腫塊,他們的表情都很沉重。后來,他們笑著讓我到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坐著,單留下了父親。回家一路,父親對我格外呵護。到家時,路過鄰居二媽家。二媽問爸爸:“校長,寶寶的病沒事吧?”我父親是一個很強大的人,但在那一刻,他終于崩潰了,他拼命想克制住自己,但最終還是失聲哭泣起來。我沒有害怕,但我已經知道,我將會有可能告別父親、母親、奶奶、妹妹、老師、同學去另一個世界。在那一段時間里,我得到的愛是成倍增長,無邊無際的。那些日子,我經常沉浸在告別這個世界的想象中。還想象著我離去之后父親他們的會怎樣難過,怎樣悲傷。
接下來,就是父親不顧一切地帶著我四處求醫。當人們總是看到他背著我走出家門,又背著我回來時,人們會發現在父親的心中其實還有比他個人的榮譽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他的兒子。他要傾其所有,阻止我與他、與這個世界的告別。最后,他帶著我去了上海,上海華亭醫院的一個老醫生很有把握地告訴父親,這個腫塊只是淋巴結核,會好的。父親得知這一結論,又一次淚流滿面。經歷了這一次虛擬的告別,我更深刻地感知到了悲憫,愛與生死的含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