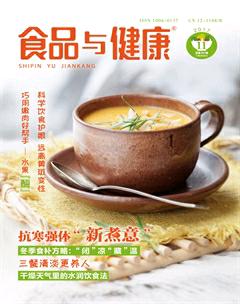香干臭干
王曉
在我居住的這個小城——江蘇省儀征市,有兩樣豆制品聲名遠揚,一個是香干,另一個則是臭干。
可惜年輕的時候,我只喜歡葷腥,無肉不歡,不識香干好滋味。偶然一次,外地朋友來小城看我,我招待她去江邊小鎮十二圩街上吃江鮮。那天的鰣魚、刀魚都給客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為盡到地主之誼感到滿足。客人臨走,羞答答地問我:“有沒有十二圩香干,想帶些回去。”香干,我是知道的,但從沒覺得能拿得出手,值得送人。問了熟識的飯店老板,原來隔壁“錢記”就是老作坊。老板熱心,幫忙去買了些過來。我那次招待的客人是一位擅寫詩的姐姐,以前只曉得她喝咖啡有癮,卻不知還有吃香干的嗜好。香干拿過來,黃而黑,顏色可疑,聞味有藥苦,印有“十二圩”字樣。這位姐姐迫不及待放了塊入口,嚼得一臉迷醉。
為了弄清楚這香干到底有多好吃,我也買了一袋回家。按照那位姐姐的提示,吃之前,香干用沸水燙熱,切成三角塊,添點香菜,加些江邊野菜,拌上麻油,細細品嘗。夾一塊送到嘴里,溫熱的干子,自內而外散發出淡淡的中藥氣味,苦里帶甜,咸香鮮美,越嚼滋味越綿長,令人欲罷不能。
知道了干子的妙處之后,我也更加關注起相關的本地美食來,家常菜常見香干炒藥芹、香干炒青椒或是香干炒秋葵,老少咸宜,幾乎人人會做。也有將普通的香干做得驚艷無比的。樓下的小飯館,有一道菜就深得我心:香干肉絲炒毛豆。菜名簡單,內容豐富。香干、肉絲、毛豆米,配兩個紅椒點綴,大油,猛火,爆炒,出鍋香氣繚繞,下飯、下酒都好。老板娘買菜挑剔,老板刀工好,香干切得細密,寬窄一樣,把做菜當藝術。這樣的兩口子珠聯璧合,是我們這些食客的福氣。
說了香的,再說說臭的——謝集臭干。我的婆家就生活在謝集附近的鄉鎮。第一次拜見婆婆,老人家熱情地做了好幾道拿手菜來招待我,其中就有萵苣拌臭干。萵苣是自家園子里種的,全是嫩筍頭,碧綠可人。臭干呢,是老人家自己鹵制的。干子灰白,汁水黑乎乎的,臭味可聞。婆婆用涼開水先將臭干洗過一遍,然后在砧板上切好,撥進萵苣盆里,加少許鹽、糖攪拌,滴一飯勺麻油,就裝盤了。婆婆端著拌好的臭干遞到我眼前,執意讓我嘗嘗她的手藝。我在旁邊看到了操作的全過程,那只黑乎乎的面目可疑的鹵缸讓我心生膽怯,但又不好意思駁她面子,只好鼓起勇氣,面帶禮貌的微笑,將臭干放到嘴里。奇怪了,那干子先臭后香,與萵苣香一對比,才覺得萵苣香是那樣的小清新,遠沒有臭干香勁道醇厚。這道菜,真是名副其實的味覺大對壘,臭干和萵筍的味道相互融合,給了我奇妙的感受。
一種二十多年從沒接觸過的食物就此走進了我的日常生活。夏天,晚風里的餐桌上,西芹拌臭干,或者萵苣拌臭干,加一碗小米粥,就能清除我一天的燥熱。秋天,來客人了,采些江灘上的野蔞蒿炒臭干,雖然平價但卻是待客的最好心意。一年四季,油炸臭干都是大人孩子喜愛的零食。在謝集,竇氏臭干臭得最地道。店門前有口大鐵鍋,食客只需一塊錢,就能換來十五塊炸得金黃起孔,薄如蟬翼的干子,再配一碟店家磨的辣椒糊,吃到嘴里那叫一個香。
受得香,耐得臭。小城生活二十年,為人處事與初來時對比,大有改變,思其緣由,時光力量之外,也有飲食的功勞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