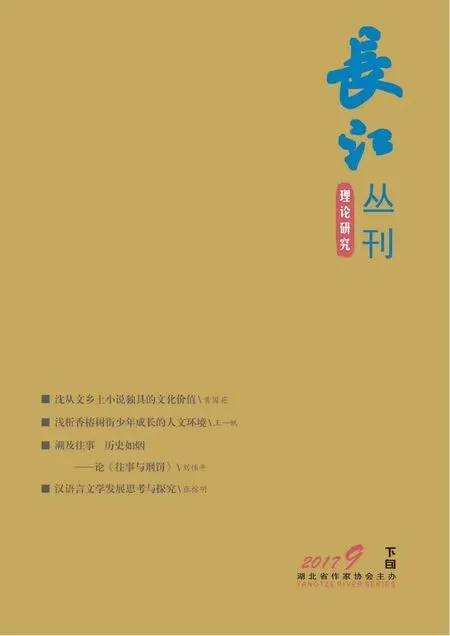從解構主義角度看意識流小說的結構安排
——以《墻上的斑點》為例
馮雙藝
從解構主義角度看意識流小說的結構安排
——以《墻上的斑點》為例
馮雙藝
本文以解構主義視角,從敘述邏輯、敘述方法、敘述背景、情節安排、言語內容以及敘述重點六個方面分析意識流小說的結構安排特點。
解構主義 意識流 小說結構
與其他類型小說相比,意識流小說的結構安排比較混亂,甚至難以捉摸。敘述者的敘述手段完全沒有遵循一套現有的秩序,而是根據意識的流動來構造篇章。這樣的反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有相似之處,因此,本文將從六個方面解讀意識流小說對傳統小說的反對模式,從而得出意識流小說的反傳統結構特點。
一、理性與感性
馬爾克斯認為,真正的“真實”,反而呈現出一種荒誕不經之感。意識流小說和這些小說一樣,往往帶著反傳統的邏輯。與之不同的是,意識流小說的邏輯不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不是屬于意識層面的理性,而是意識在行文時的自然隨意性。
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墻上的斑點》一文,體現了敘述邏輯層面的叛逆,即感性遠遠大于理性。從墻上的一個斑點出發,伍爾夫行文完全按照意識的發展方向,純自然地全盤托出。
看似漫無邊際的言語,實則透露出意識流動的真實感。在這一觀點上,意識流小說的結構有其內在的邏輯,即感性邏輯。感性邏輯和理性邏輯不同之處在于,根據理性邏輯組織的小說結構,往往具有必然性,一定是在作家有意識的前提下故意安排的,不存在行文結構的偶然性。但意識流動是必然的,是真實存在的。因此,意識流小說的感性結構對傳統小說的理性結構構成挑戰,打破以往以理性為中心的邏輯結構。
二、順序與亂序
常規的小說通常采用五種敘述方法:順敘、倒敘、插敘、補敘、平敘。而意識流小說的結構安排則采用非順序的方法,即隨意識流動的順序行文。意識流動的順序又不存在固定的順序,因此其順序即亂序。
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墻上的斑點》有其內在的亂序結構。伍爾夫從墻上的斑點想象到是一顆釘子,由釘子引出一系列遐想;之后又懷疑不是釘子,同時聯想到私人物品無法控制及生活快節奏;接著又聯想到來世的一系列虛幻景象;下面繼續猜測斑點是暗黑色的圓形物體,由此想象到被塵埃淹沒的特洛伊城;與此同時,作者寫自己不希望被打擾,以便找到一條愉快的思路;在愉快的思路里,作者開始了她的虛幻想象;接下來又猜測斑點是一個凸起物,從而聯想到古冢和營地,并引發上校和牧師的故事;作者接著猜想那個斑點是巨大的釘頭,引發一些列虛幻的想象;之后認為墻上的斑點是大自然的把戲,為了讓人們忘記不愉快的思緒;作家感覺看到斑點就如同抓住了一塊木板,通過木頭,想到其四季的成長;最后,思緒被打斷,作家發現那個斑點是蝸牛。
三、現實與虛幻
常規小說都有其敘述背景,這里的敘述背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敘述背景,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環境內,一定的人或物,發生了一定的事。而廣義的敘述背景則是為小說的內容找到一個框架,可以對其進行限制,不至于使其漫無邊際。一般來說,敘述背景都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無論是聯想、想象、幻想,都離不開文本的限制。但是虛幻的背景,就游離在文本內容之外,與主干內容有時甚至毫無聯系。
這樣的虛構敘述背景對常規小說來講是一種極大地挑戰,是反傳統的敘述模式。
四、整體與分散
與常規小說不同,意識流小說展現出的情節安排比較分散,超出了整體模式的框架,比較自由。常規小說有整體的思路安排,情節環節很緊湊,不會有散文的閱讀體驗。
伍爾夫在寫她思考墻上的斑點是什么的同時,也打亂了整體的意圖和導向。原本只是思考墻上的斑點,現在卻把寫作內容分散到任何思維可以到達的地點,沒有限制,沒有界限。伍爾夫對情節的安排以墻上的斑點為主線,發散到她能聯想到的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使得小說看起來并沒有緊密聯系的情節,甚至沒有情節。
這也是對“整體”即“情節中心”的一種反傳統,把分散的情節也推上高峰。
五、在場與不在場
“在場”是一個狀態名詞。“在場性”是德語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海德格爾在其哲學中說明“在”即“存在”。換言之,“在場”就是直接呈現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德里達認為,存在于言語和文字之間的“在場”,在大多數情況下以“不在場”的形式存在。簡言之,就是如果描述一個事物,那么這個事物成為言語的同時,可以在場,可以不在場,可以提前或滯后出現。
六、中心與邊緣
一般情況下,小說都有自己的敘述重點,不會因為文章的行文結構而喪失了本身的意旨。即使是敘述線索十分復雜的小說,也會有其中心點。但意識流小說的敘述重點就不突出,甚至被聯想的內容所忽視。
《墻上的斑點》這篇小說,伍爾夫的文章中心很明顯,是圍繞斑點發散的意識流思緒。但是在發散的同時,由斑點聯想到人生的飛速、存在的意義、女性的權利、自然的安逸等等一系列思考。傳統的小說都會把中心點突出地展示,但是伍爾夫卻將中心點向外散發,引發更多的思考,使得邊緣的思緒成為主導,中心只是襯托。她的主體意思絕不是處于中心位置的斑點,而是由斑點引發的哲學思考。
在這一點上,伍爾夫很好地將“邊緣”壓倒“中心”,使之成為意識流小說的主體。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