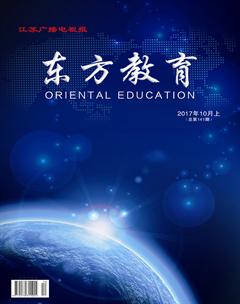論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
蔣東
摘要:各國(guó)的刑事立法中,對(duì)犯罪未遂形態(tài)的規(guī)定多有不同,歸納起來(lái)主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規(guī)定和理論解釋。其中廣義的犯罪未遂包括狹義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本文中所討論的是狹義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區(qū)別。如何區(qū)分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論界似乎已成定局,即成立犯罪中止須是行為人自動(dòng)停止犯罪。然而,何謂自動(dòng) ? 卻是眾說(shuō)紛紜,有主觀說(shuō),限定主觀說(shuō),客觀說(shuō),折衷說(shuō)之爭(zhēng),至今尚無(wú)普遍接受的標(biāo)準(zhǔn)。理論上的爭(zhēng)議反映在司法實(shí)踐中,必然帶來(lái)判例的極不一致,而此種現(xiàn)象顯然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本文將運(yùn)用比較法的研究方法通過(guò)對(duì)各國(guó)對(duì)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規(guī)定的剖析探尋兩者的本質(zhì)區(qū)別,以期對(duì)司法實(shí)踐有所幫助。
關(guān)鍵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自動(dòng)
一、簡(jiǎn)述世界各國(guó)的普遍立法狀況
(一)歐美國(guó)家的立法概況
在英美法系中,對(duì)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處理,在處罰上也不作任何特別考慮。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國(guó)有大約半數(shù)的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許被告人把非因外來(lái)障礙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為無(wú)罪辯護(hù)的理由。在大陸法系中,對(duì)于未遂犯多規(guī)定得減或必減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但也有例外。如 1951 年的《保加利亞刑法典》和 1919 年的《蘇俄刑法指導(dǎo)原則》就規(guī)定未遂犯與既遂犯同等處罰。但是,對(duì)于中止犯,各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幾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減輕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 43 條規(guī)定:“已經(jīng)著手實(shí)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減輕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減輕或者免除刑罰”。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guó)刑法典第 23 條第二款規(guī)定:“未遂可以比照既遂從輕處罰”。第 24 條第一款規(guī)定:“行為人自動(dòng)中止犯罪或主動(dòng)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處罰。如該犯罪沒(méi)有中止犯的行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為人主動(dòng)努力阻止該犯罪完成,應(yīng)免除其刑罰”。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別規(guī)定:“未遂犯處罰之程度如下,法定刑為無(wú)期徒刑時(shí),未遂犯應(yīng)處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減輕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處罰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為,只有當(dāng)以完成的行為本身構(gòu)成其他犯罪時(shí),才處以該行為規(guī)定的刑罰”,“如果自愿阻止結(jié)果的發(fā)生,僅處以犯罪未遂規(guī)定的刑罰并減輕三分之一至一半。”
(二)我國(guó)得立法現(xiàn)狀
從我國(guó)刑法的規(guī)定來(lái)看,第 23 條規(guī)定:“已經(jīng)著手實(shí)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duì)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第 24 條規(guī)定:“在犯罪過(guò)程中,自動(dòng)放棄犯罪或者自動(dòng)有效防止犯罪結(jié)果發(fā)生的,是犯罪中止。對(duì)于中止犯,沒(méi)有造成損害的,應(yīng)當(dāng)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yīng)當(dāng)減輕處罰”。顯然,我國(guó)刑法也同許多國(guó)家的刑法一樣,對(duì)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規(guī)定。對(duì)未遂犯,是“可以”從寬;對(duì)中止犯,是“應(yīng)當(dāng)”從寬。并且,從寬的內(nèi)容也差異極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減輕的待遇,而未遂犯卻是原則上至多得到減輕的待遇。
(三)各國(guó)對(duì)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規(guī)定的共同點(diǎn)
以上的論斷看起來(lái)是沒(méi)有問(wèn)題的,但必須考慮的是,各國(guó)對(duì)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區(qū)分是否一致呢?如果在根本上不一致的話(huà)就不能作上面的比較。必須指出的是,各國(guó)對(duì)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區(qū)分方式并不相同:一是把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視為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從定性到處罰均加以嚴(yán)格區(qū)分;二是在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制度內(nèi)將犯罪中止與其他類(lèi)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從處罰上加以區(qū)別。然而就其實(shí)質(zhì),各國(guó)對(duì)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所指稱(chēng)的事物,卻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區(qū)分方式的不同并不等于內(nèi)容的不一致,“因己意而停止”的中止與“因障礙而停止”的未遂早已是各國(guó)立法界、司法界、學(xué)術(shù)界達(dá)成的共識(shí),其內(nèi)涵和外延是清楚明晰的。其次,從理論上講,盡管第一種區(qū)分方式的犯罪中止包括了犯罪預(yù)備階段的中止和犯罪未遂階段的中止,時(shí)空性上不同于只包含犯罪未遂階段的中止的后一種區(qū)分方式。
二、解析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區(qū)別
顯然,各國(guó)對(duì)犯罪中止的處罰均遠(yuǎn)遠(yuǎn)輕于對(duì)犯罪未遂的處罰。這是一個(gè)奇怪的現(xiàn)象,東西方文明的激烈沖突,各國(guó)法文化傳統(tǒng)以及刑法價(jià)值觀的巨大差異,在這一點(diǎn)上都煙消云散。各國(guó)立法者莊嚴(yán)宣布:對(duì)中止犯就應(yīng)大幅度從寬處理。尤其在我國(guó)刑法中,犯罪中止不僅比犯罪未遂、犯罪預(yù)備的處罰輕,而且與整個(gè)刑法所規(guī)定的其他法定從寬情節(jié)相比,也是獨(dú)一無(wú)二屬于最輕的。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國(guó)立法者不約而同地給予中止犯如此寬宥的處罰?這是否隱含著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存在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別呢??jī)H僅局限于刑法條文,我們似乎很難找到答案。然而,拓寬視野,深入刑事責(zé)任的根基,進(jìn)入刑罰目的論研究與刑事政策學(xué)的領(lǐng)域,問(wèn)題即可迎刃而解。
(一)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定罪原則
從客觀歸罪到主觀歸罪,再到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定罪原則,人類(lèi)在刑法思想史上經(jīng)歷了大致相似的變化路程。根據(jù)相對(duì)意志自由論的觀點(diǎn),人的活動(dòng)是具有自覺(jué)能動(dòng)性的,但這并不等于意志的絕對(duì)自由,人的認(rèn)識(shí)和活動(dòng)并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觀存在和客觀規(guī)律制約的,人只有在正確認(rèn)識(shí)和利用客觀規(guī)律時(shí)才獲得意志的相對(duì)自由。
具體落實(shí)到犯罪上,首先,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根據(jù)本人的意愿選擇的,這種選擇使自己立于與社會(huì)公眾相對(duì)立的地位,必然會(huì)受到刑法的否定評(píng)價(jià)與譴責(zé)。因此,犯罪人應(yīng)該對(duì)本人危害社會(huì)的行為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這種刑事責(zé)任乃是建立在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人身危害性相統(tǒng)一的基礎(chǔ)之上的,這是相對(duì)意志自由論的必然結(jié)論。考察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構(gòu)成要件模型,就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而言,兩者雖均未發(fā)生構(gòu)成要件所要求的實(shí)害結(jié)果,但前者較后者多出具有正當(dāng)性的中止行為,平衡了先前行為之不法,恢復(fù)了先前行為所否定的法律意思,故兩者對(duì)法秩序的破壞程度并不相同。而就行為人的人身危險(xiǎn)性而言,一是出于己意而停止,一是因障礙而停止,主觀惡性不同,人身危險(xiǎn)性之差異自不待言,故刑法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權(quán)與社會(huì)防衛(wèi)的功能,必定會(huì)對(duì)其規(guī)定不同的待遇。其次,犯罪人的這種犯罪意愿的選擇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huì)物質(zhì)條件之上的,不能脫離一定的時(shí)空環(huán)境而存在。那么,對(duì)于犯罪人,國(guó)家顯然不能將其完全消滅,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應(yīng)對(duì)其進(jìn)行教育改造,使之自覺(jué)遵守法律,早日復(fù)歸社會(huì)。
(二)試析犯罪未遂和中止的情節(jié)
立法對(duì)中止制度與未遂制度的不同規(guī)定是為了獎(jiǎng)勵(lì)中止犯,反向思之,認(rèn)定中止犯的關(guān)鍵即是其在立法上有值得表彰之處,這也是判斷中止犯與未遂犯最根本的標(biāo)準(zhǔn)。運(yùn)用這種標(biāo)準(zhǔn),不僅可以解決許多在犯罪論注釋層面爭(zhēng)議不休的問(wèn)題,而且簡(jiǎn)便易行,便于司法實(shí)踐操作。例如在故意殺人、強(qiáng)奸、搶劫等犯罪中受害人為了得以脫身答應(yīng)日后滿(mǎn)足犯罪人的要求,犯罪人信以為真,遂停止犯罪,該種情形如何認(rèn)定。從注釋論層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棄其犯罪意圖時(shí),并不存在什么外界障礙致使其行為無(wú)法完成,他本來(lái)完全可以將犯罪進(jìn)行下去,這種因己意而停止的情形應(yīng)認(rèn)定為犯罪中止無(wú)疑。另一方面,犯罪人聽(tīng)到受害人假意許諾后停止犯罪的情形,實(shí)質(zhì)上與犯罪人在實(shí)際上不存在障礙而誤以為有妨礙其犯罪行為的障礙,因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樣,都是犯罪人對(duì)事實(shí)認(rèn)識(shí)錯(cuò)誤的結(jié)果,只不過(guò),后者以為犯罪已不能完成,前者以為犯罪已不必完成;但其共同點(diǎn)是,兩者對(duì)事實(shí)做出了錯(cuò)誤的判斷,基于這種錯(cuò)誤的判斷而放棄犯罪行為,是違背犯罪人的真實(shí)意志的,故應(yīng)認(rèn)定為犯罪未遂。兩種觀點(diǎn),各執(zhí)一方,理由都很充分,但又似乎難以駁倒對(duì)方的觀點(diǎn)。筆者以為,對(duì)大部分犯罪人而言,遇熟人而放棄罪行并非出于真誠(chéng)悔悟及對(duì)法律價(jià)值的重新承認(rèn),而為了保護(hù)自己。因?yàn)橐允烊藶榍趾?duì)象會(huì)使自己面臨極大的身敗名裂乃至鋃鐺入獄的危險(xiǎn),故此種停止行為不符合中止制度設(shè)立的立法本意,宜認(rèn)定為犯罪未遂。又如對(duì)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員中止犯罪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數(shù)人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棄犯罪行為外,還應(yīng)說(shuō)服其他犯罪人也放棄犯罪行為,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結(jié)果之發(fā)生。因?yàn)閺闹饔^上講,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犯意聯(lián)系,從客觀上講,其犯罪行為互相支持,故每人對(duì)全體成員的行為都承擔(dān)一定的刑事責(zé)任。一人逕自中止了犯罪行為,若其他人仍將犯罪實(shí)施完畢,因?yàn)榉缸镆堰_(dá)既遂,故對(duì)獨(dú)自中止犯罪行為者也無(wú)認(rèn)定為中止犯的法律依據(jù)。也有學(xué)者主張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參與而給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帶來(lái)的有利影響,即應(yīng)認(rèn)定成立犯罪中止。當(dāng)然,鑒于共同犯罪的復(fù)雜性,還必須考慮該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若其是教唆犯,組織犯等,只有當(dāng)他說(shuō)服他人放棄犯罪意圖,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結(jié)果發(fā)生的,才能認(rèn)定為犯罪中止。國(guó)家規(guī)定抽象的危險(xiǎn)犯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危險(xiǎn)狀態(tài)的實(shí)害化,從而更好地保護(hù)合法權(quán)益,也正因?yàn)槿绱耍庞蟹缸镏兄钩闪⒅匾T囅耄粼擃?lèi)犯罪否認(rèn)其存在犯罪中止,則必然令行為人產(chǎn)生回頭無(wú)望的消極心理,因而對(duì)危險(xiǎn)狀態(tài)聽(tīng)之任之,直至發(fā)生危害結(jié)果,而這顯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故立法為了有效地保護(hù)合法權(quán)益,必然會(huì)對(duì)自動(dòng)有效地消除危險(xiǎn)狀態(tài)的行為人給予犯罪中止的獎(jiǎng)勵(lì)。這是立法應(yīng)具備的精神,也是刑事政策的需要!
三、結(jié)語(yǔ)
無(wú)疑,在司法實(shí)踐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勵(lì)之處”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區(qū)別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然而,人類(lèi)建立的概念系統(tǒng)永遠(yuǎn)不能窮盡生活本身,生活的彩色與立法的灰色是一對(duì)永恒的悖論:一旦規(guī)范本身模糊(與具體行為相比較)或行為性質(zhì)模糊(與二值規(guī)范相對(duì)照)或行為本身的事實(shí)不能查清(受認(rèn)識(shí)條件限制),則很難判斷一行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勵(lì)之處。而且,“刑法如雙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dāng),則國(guó)家與個(gè)人兩受其害。”因此,這一標(biāo)準(zhǔn)的適應(yīng)還必須以謙抑原則作補(bǔ)充。也即是說(shuō),在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界際線(xiàn)上采取緊縮的態(tài)度,兩可情形下,定犯罪中止為宜。應(yīng)該說(shuō),這既非違背法律的擅斷,也非放棄法律的怠為,這是人類(lèi)為應(yīng)付復(fù)雜的社會(huì)生活而在最壞的兩難境遇中做出的最好選擇,也是人類(lèi)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寬容精神的體現(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陳忠林主編《刑法學(xué)》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3年版
[2]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xué)》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3]張明揩主編 《刑法學(xué)》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1997年版
[4][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出版社 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