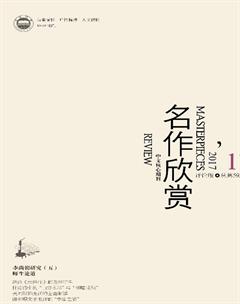農裔知識分子的身份迷失與命運分化
摘 要:相較于《人生》中進城難的高加林,新時期的農裔知識分子楊科和邵景文則順利進城,他們雖成為“城里人”,但農裔城籍的身份使得他們既得不到城里人的認可,也被村里人排除在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出于對名利的渴求,他們成為權力的依附者、金錢的奴隸,而對尊重的渴求和身份的喪失導致他們精神下行和自我墮落。
關鍵詞:農裔 知識分子 身份 迷失 沉淪
中國設置的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使城市與農村的差異由單純的經濟、地理上的差異演化為復雜的經濟、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異。而隨著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通過高考進入城市,成為擁有本科學歷以上的腦力勞動者,即農裔知識分子。
在現當代文學史中,從路遙的《人生》開始,越來越多的作家關注到“農裔知識分子進城”后面臨的生活和精神困境,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描述涂自強進城后希望的破滅;閻連科的《風雅頌》則是講述了楊科成功進城后尋求精神世界的過程。學術界對農裔知識分子進城也有了大量的研究,如沈昕苒在《城鄉演變背景下李佩甫小說中“離鄉知識分子”形象研究》中重點指出李佩甫小說中的四種農裔知識分子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命運,劉香在《城鄉間的進退——新時期“鄉下人進城”小說論》中也重點論述了農民工和農裔知識分子在城市的漂泊。
事實上,自《人生》至今四十年來,農裔知識分子進城依舊面臨著巨大困境。本文依據農裔知識分子進城面臨的困境將農裔知識分子進城情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進城的困境在于想進城卻被城拒之門外,代表人物是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適應城市生活以及在城市安家立業,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是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的涂自強。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是擁有城市戶口和城市身份后的身份迷失,代表人物為閻連科的《風雅頌》中的楊科和張者的《桃李》中的邵景文。楊科和邵景文是農裔知識分子進城中的成功者,他們擁有城市戶口、衣食無憂的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到最后一個喪失了教授身份,出逃到詩經古城,另一個則是在宋總伸出橄欖枝時,背棄教授身份,成為富翁,身敗名裂。由于在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身上存在極為明顯的城鄉對立、精神沖突等問題,因此在前人的研究中,都較多地關注了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忽略了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事實上,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在已經擁有了第二階段農裔知識分子所期望的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情況下,依舊無法成為真正的城里人,其中暗含的原因能夠更深層次地揭示出農裔知識分子進城的困境。
一、社會身份的迷失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于小農經濟的限制,“士”從事的職業較少,大多是官員和私塾先生。而到了現當代,由于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知識分子群體擴大,其所從事的職業更是五花八門,但由于農村官本位的思想和城市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性,當代文學史中的農裔知識分子大學畢業后大多在學術界、商界和政界謀得職位。例如《風雅頌》《桃李》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楊科、邵景文和井河成了大學教授,《大嫂謠》中的“我”成了編輯,《生命冊》中的吳志鵬和駱駝成了企業家,《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成了衛生部副廳長等。
對于在學術界謀得職位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其從事的職業大多屬于人文學科。20世紀90年代,市場社會的出現,使得人文學科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他們不再處于整個舞臺的中央”,對于楊科來說,大環境下的邊緣化使他無法繼續晉升,抗沙塵暴事件后被定為“精神病患者”則使他的教授身份被剝奪;為了重新找回社會對他教授身份的認同,楊科選擇回到鄉村。在鄉村,天堂街事情的暴露使得楊科無法再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在鄉村立足。至此,楊科的教授身份被社會徹底否認。
如果說,楊科的知識分子身份是被迫失去的話,那作為楊科的對立面,邵景文的社會身份則是他主動失去的。棄文從法的邵景文看似成功避開了被邊緣化的危險,但卻淪為了金錢的附庸,認識宋總之后,邵景文便從一個兢兢業業的教授變為一個身價百萬的老板,教授的身份成了商人身份的附庸和點綴,亦文亦商讓邵景文對自己的社會定位感到了迷茫。
而對商界的知識分子來說,商海中的浮沉更是讓他們感到了身份定位的無力感,《生命冊》中,來自農村的駱駝通過經商成功地在城市里立足,為了獲得更高的利益,駱駝進行了一系列瘋狂地炒股、投資,最后因為涉嫌賄賂官員,資產被查封,被“打回原型”。
對于農裔知識分子來說,職業是他們在城市里立足的根據,也是他們社會身份得到確立的基礎,更是他們在城市里建立自尊自信的源泉,而城市身份的迷失使得這一批人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成為城市里的漂泊者,而這種身份上的漂泊會逐漸造成其精神上的漂泊。
二、源身份的迷失
社會身份是用來判定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而源身份是指人的根在何處。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都是“雙重邊緣人”,也都“承受著來自城市‘他者的歧視、冷落和拒斥”,“他們的根雖然在鄉村,魂卻留在城市,再也回不了家了”{1}。不同的是對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在自我認知還是他人認知中,他們都被當作是農村人。但是在楊科和邵景文的身上,在自己和農村同鄉的認知中,已經被判定為“城里人”,但在真正的城里人看來,他們始終不是城里人。正如吳志鵬說的那樣:“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帶有黃土標記的。我已無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
1.城里的鄉下人。“五四”到新中國成立前,經濟發展緩慢,城鄉尚未在法律上進行嚴格區分,人員流動較為便利;新中國成立以后,戶籍制度將人們限制在固定區域內,也明確了“城市”與“農村”的地理概念。改革開放后,城市成為國家改革的重心,各項城市改革政策使得城市在政治上、社會保障上、醫療衛生、生活環境和教育機會上的利益優勢明顯,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城市的富裕與農村的貧困形成鮮明對比,長期的隔膜造成了城鄉兩種不同的社會生態環境,正如洛伊寧格爾所說:“僅僅因為教育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與意識的巨大差異就完全可以把這兩部分中國人劃分成兩個種族。”{2}城市的富裕與農村的貧窮,使得城市成為農村人的向往之地,并在潛意識中便對城市懷有敬畏之心。
第一、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帶著“土氣”進城時,甘愿接受城里人的同化,花盡力氣將自己的“紅薯味”洗掉。例如剛進大學的涂自強自覺培養刷牙的習慣,學習使用電腦,甚至學習周圍同學的說話方式;吳志鵬為了改變身上的“新”,主動學習城里人的穿著,學習城里人走路時的氣定神閑;馮家昌為了往上爬,全盤接受老班長的“忍住,吃苦,交心”的“成功秘訣”,并一一實踐。而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不再盲目地接受城里人的同化,開始對城市思維有著客觀的審視,楊科堅信憑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評得教授職稱,并對趙茹萍通過父親、丈夫、情人的關系評得教授職稱的方式感到不屑。認為法律高于一切的邵景文,在面對妻子靠關系、靠權勢給對方當事人施壓來解決“樓梯案”時感到悲傷。在質疑城市思維的同時,他們不再像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那樣拼命掩蓋自己骨子里的“紅薯味”,而是重新審視農村思維中的優秀內容,這使得他們在思維上更具雙重性,也使得他們無法成為真正的城里人。
此外,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在一個時期內所執行的重工輕農、以農補工的社會協調機制和傾斜政策,固然保證了中國的工業化在短期內的迅速發展和在世界格局中的競爭地位,但在社會心理上卻造成了農民的利益損害,常常使他們在人格上亦處于屈辱地位。{3}與城里人聯姻是農裔知識分子快速進城的方法,而聯姻意味著在家庭中處于屈辱地位,但第二階段農裔知識分子對妻子的俯首稱臣是有意識的行為。例如《城的燈》中馮家昌為了能夠繼續在城里立足,在面對李冬冬的無理取鬧時,內心雖千般厭惡,但也不得不賠禮道歉,好言相勸。第三階段農裔知識分子雖然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在家庭中的屈辱地位卻已經進入他們的潛意識,在城里待了二十年的楊科發現趙茹萍和李廣智偷情時,他的第一反應竟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內疚”。這種人格的屈辱地位注定農裔知識分子無法在精神上與城里人處于平等地位。
在城里人看來,農村籍知識分子是城市的局外人,他們泥土色的印記在商品化經濟的今天,不僅意味著貧窮,還意味著落伍,甚至會成為一種恥辱和罪惡。{4}這使得無論是第幾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都無法融入城里。作為城里人,政策所賦予的優勢轉化為潛意識里的優越性。對農村人的鄙視,便是對自身優越性的肯定,為了維護住自己的優越感,城市里的人無論是在行為上還是思想上,都將農村人劃為“他者”。中學輟學、懷孕墮胎的趙茹萍是“下嫁”給了博士學歷的楊科;趙茹影在評價“樓梯案”時,說“他有多少能耐我還不知道,他忙了兩年的事,我兩天就解決了”。因此,鄉下人“融”城難,不僅僅是因為自身思維的雙重性、人格上的屈辱地位,也是因為城里人的優越意識。
2.鄉下的城里人。第一、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與農村依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們無論身處何方,對鄉親們來說,依舊是自家人,小林在城里的家,也成為鄉親們來城的中轉站;剛進城的吳志鵬,成了農村鄉里的救命稻草,經常能收到老姑父“見字如面”的字條。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的長期離鄉使得他們與農村的聯系變得松散,一方面對鄉下的鄰里來說,農裔知識分子們已經是城里人。耙耬山的人在與楊科聊天的內容更多的是京城里的種種見聞;無梁村的人對身價上億的吳志鵬懷有敬畏心理。另一方面,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再次回村時,也是以城里人的身份榮歸故里,回村后的楊科始終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在精神上凌駕于村里人之上。《高老莊》中的子路在給父親做三周年祭日的時候,為了顯示自己的城市資本,大肆鋪張,并極力與地方官員進行密切交往。在村里人和農裔知識分子看來,他們早已是城市的一員,不再屬于農村。
對于那些仍對農村懷有眷戀的知識分子來說,農村是他們苦難的過去,也是美好的回憶,再次回村,他們痛苦地認識到,當年淳樸的鄉親早已是另一副嘴臉。當楊科回鄉神話瓦解時,村里人便改變了態度,搬走楊科家的東西后又覬覦他的房子。在《高老莊》的子路眼里,家園已不再是過去那種田園牧歌式的了,而是充滿著利益沖突的畫面。《知識分子》中的鄭凡過年回家時,發現家鄉淳樸的鄉親都開始懷有私心地請求他的幫助。事實上,離家多年的農裔知識分子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情感上,都無法真正再次回鄉,他們早已被農村排除在外。
對于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故鄉只是一段記憶,即使對故鄉懷著美好的遐想,但也無法面對真實的故鄉,正如回鄉后的楊科第一次看到讓他心心念念的玲珍時,卻有了一種找錯人的誤會感。但與故鄉的疏遠并沒有增強他們與城市的聯系,他們雖然有知識,有戶籍,但始終沒能與城市水乳交融,無法將城市認作“精神故鄉”,“雙重邊緣人”的身份使得他們游離在農村和城市之間。
三、身份迷失后的沉淪
從“天之驕子”到“農村來的”的身份變化,使得農裔知識分子性格中的驕傲與自卑失衡。對于第二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如何保證自己的物質生活才是重點,因此剛剛進入城市的他們,努力讓自己低到塵埃里,對“農裔”的身份認同,給了他們一個理由,讓他們說服自己,去接受城市中不公的地位和待遇。而對于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物質生活已得到了保障,但出生農村讓他們始終無法被城里人接納,由此出現了物質生活的高層次和身份認同的低層次的矛盾,社會身份帶來的自尊自信正是緩解這種矛盾的良藥。因此當社會身份迷失時,農裔知識分子身上原有的平衡性被打破,自尊自信受到了挑戰,他們便迫切要求尋得其他能夠緩解矛盾的方式。而在尋找過程中,他們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自我墮落的道路。對于憑借讀書成為城里人的楊科來說,“教授”這個身份是他立足的根本,也是他自尊自信的根源,為了重新找到“教授”帶給他的滿足感,他選擇回到耙耬山。在家鄉,知識分子的身份能夠讓他備受村里人的尊重;教授工作證使得天堂街上的小姐們柔情似火,讓他感到賓至如歸,由此楊科成為天堂街的常客。與楊科同出身的邵景文也是如此,農村生活的痛苦經歷使得邵景文的內心對金錢有著極度的渴求,金錢對于邵景文來說,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象征,更是地位的象征,是獲得他人尊重和敬仰的源泉,大量的金錢讓邵景文有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而他也由此淪為金錢的附庸。
在城市生活多年的農裔知識分子,無法再將自己與農村人等同起來,他們對農村身份的背棄,也意味著背棄了農村思維,成為無根的人,因此當他們面臨社會身份迷失時,無法做出正確的選擇,最后只能沉淪。始終堅信自己是知識分子的楊科,在回鄉考察的神話被揭穿時,瀕臨崩潰的他殺死了小敏丈夫;崇拜金錢的邵景文遇上腰纏萬貫的宋總后,迅速被金錢包圍,在聲色浮靡中被殺。
對于其他的進城者而言,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是成功的典型,他們擁有了其他進城者想要的物質財富和社會地位,成功地成為城里人,但對于第三階段的農裔知識分子來說,社會身份的迷失,使得他們喪失了在城里立足的根源,也喪失了自尊自信的根源。而源身份的喪失,又使得他們成為無根的人——城市始終沒有完全地接納他們,鄉村也將他們排除在外,他們成為“中間物”。根的缺失,使得他們在社會潮流下無法避免自身的沉淪。
{1}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2} 〔法〕洛伊寧格爾:《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王山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
{3}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頁。
{4} 關曉瑞:《農裔籍知識分子進城的現代性反思》,《許昌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
[2] 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3] 郝志東,劉栩,劉晨,郭正陽.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4] 劉萃俠.社會心理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5] 藍海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演變路徑[J].經濟研究參考,2005(17).
[6] 劉香.城鄉間的進退——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論[D].江西師范大學,2015.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南京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國家級項目“新文學史百年知識分子形象變遷”的項目成果
作 者:石婷,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2014級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編 輯: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