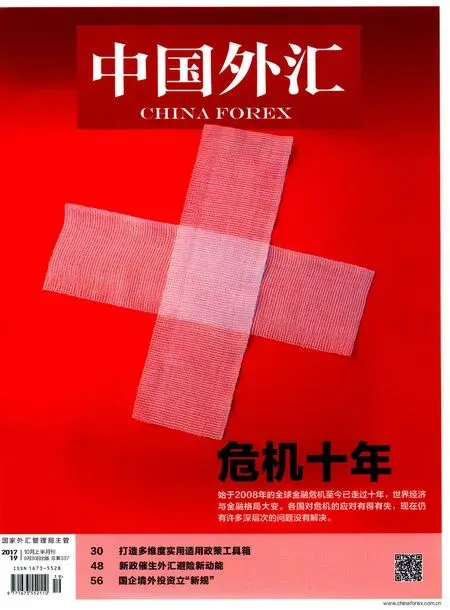世界經(jīng)濟金融格局大變
文/孫杰 編輯/孫艷芳
世界經(jīng)濟金融格局大變
文/孫杰 編輯/孫艷芳
金融危機十年來,世界經(jīng)濟與金融格局,乃至一些國家的社會思潮和政策導向,都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
2017年,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但危機依然深刻地影響著當前的世界經(jīng)濟。這不僅是因為危機本身帶來的巨大沖擊影響了全球的經(jīng)濟格局,而且由于在應對危機沖擊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也給當今的世界經(jīng)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并且對社會思潮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7年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16年,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總量在全球中的占比已經(jīng)達到了58%。
經(jīng)濟格局生變
從中文字面上看,危機一詞包括了危急和機會兩層含義。這是因為應對危急的措施可能帶來變革,因而也會成為機會。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肇始于美國,并且造成了歐洲和日本更嚴重的經(jīng)濟衰退,引發(fā)了這些國家超常規(guī)的應對政策。從目前來看,這些政策的應急特征明顯,且持續(xù)時間長。所以迄今為止,這些發(fā)達國家雖然已有所意識,但是還沒有真正來得及著手進行結構改革。相比之下,危機卻給了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加速經(jīng)濟趕超的機會。
在金融危機以前,國際經(jīng)濟學界就曾經(jīng)盛行新興市場對發(fā)達國家脫鉤論。在美國新經(jīng)濟泡沫崩潰以后,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在經(jīng)濟增長速度上相對發(fā)達國家的優(yōu)勢越來越明顯。危機發(fā)生以后,新興市場雖然也難免受到?jīng)_擊,與發(fā)達國家在增長速度上的差距不斷縮小,但是一直保持著大約3個百分點以上的優(yōu)勢。
2013年,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fā)布的世界經(jīng)濟展望數(shù)據(jù),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第一次超過了發(fā)達國家。雖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還有諸多不足(例如,由于購買力平價計算方法的調(diào)整,后來這個時點提前到了2008年),但這在當時畢竟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反映了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jīng)濟格局的變化趨勢。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7年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16年,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總量在全球中的占比已經(jīng)達到了58%。即使從以美元計算的現(xiàn)價GDP來看,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總量在全球中的占比也從2009年的31.07%上升到2016年的38.79%。與此同時,同期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相對于發(fā)達國家的比例也從18.91%上升到23.58%。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全球經(jīng)濟治理格局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金融危機以前,全部由發(fā)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在引領全球經(jīng)濟政策的走勢和協(xié)調(diào)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在金融危機后,隨著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經(jīng)濟中影響力的不斷上升,雖然發(fā)達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溢出效應依然受到重點關注,但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回蕩效應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二十國集團開始成為國際經(jīng)濟治理的主要平臺,發(fā)達國家不得不坐下來與發(fā)展中國家共同商討全球治理的問題。目前,這已經(jīng)成了全球經(jīng)濟治理中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GDP增量中,中國的貢獻一直維持在30%左右,成為支持世界經(jīng)濟從危機中復蘇的重要支柱。中國經(jīng)濟規(guī)模對美國經(jīng)濟規(guī)模的比例也從2008年的68.42%上升到2016年的114.66%。即使按照匯率法折算的現(xiàn)價美元GDP,同期的中國經(jīng)濟規(guī)模對日本的比例也從91.39%大幅躍升到227.15%。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金融危機以后,在發(fā)達國家之間,特別是歐盟與美國之間的實力對比也悄然發(fā)生了變化。按照現(xiàn)價美元計算的GDP,2008年歐盟是美國的1.39倍,而到了2015年情況發(fā)生了逆轉(zhuǎn),歐盟僅為美國的0.98倍。顯然,美國對歐盟的經(jīng)濟實力在相對上升。這其中折射出了兩個問題:其一,美國的危機應對政策盡管存在問題,但的確使其很快走出了危機,恢復了溫和增長;而歐洲的危機應對政策則不盡如人意,還爆發(fā)了主權債務危機。其二,歐盟的統(tǒng)一政策在面臨外部沖擊的時候無法適應各國的具體情況,所以在債務危機以及救援過程中暴露出了種種分歧,并導致英國脫歐以及各國社會思潮的差異。這些問題不僅成為歐洲各國大選的焦點,而且也拖累了歐洲經(jīng)濟的增長。由于歐洲更多地被內(nèi)部事務所羈絆,在國際經(jīng)濟治理中,美國與新興市場之間的博弈就顯得更加突出。
債務問題更加凸顯
金融危機以后,主要發(fā)達國家先后都實行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政策雖然在刺激經(jīng)濟增長方面成效不甚顯著,但是對于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防止危機的惡化和蔓延仍功不可沒。不過,財政刺激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給經(jīng)濟穩(wěn)定帶來了新的問題。
金融危機以前,由于在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監(jiān)管的缺失,加之對未來經(jīng)濟增長的盲目樂觀預期,使得私人部門往往傾向于借助債務杠桿來博取超額收益。因此,超出正常水平的企業(yè)和個人債務都源于對未來過度樂觀的預期和對利用杠桿提高收益和享受的狂熱追求。而當非理性繁榮結束,泡沫崩潰,整個經(jīng)濟就陷入了債務危機。所以我們可以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過度負債不可持續(xù)造成的危機。既然如此,按照正常的邏輯,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就應該是降低債務水平和去杠桿化。然而在危機期間,為了消除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恐慌,各國央行不僅沒有緊縮債務,反而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用繼續(xù)擴張債務來應對危機。甚至在危機過后,政府仍通過量化寬松政策,在居民和企業(yè)去杠桿的同時加杠桿,其結果是債務從私人部門轉(zhuǎn)移至政府部門。
問題在于,用政府更高的信用去代替企業(yè)和個人的信用不足以應對市場危機的方法,其可持續(xù)性是有限度的。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的后遺癥,2009年底爆發(fā)了歐洲債務危機,隨后是2011年美國國債被降級,以及日本公共債務負擔的持續(xù)惡化。這一系列的挑戰(zhàn)再次證實了金融危機后必然跟隨政府債務危機的歷史規(guī)律。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而從理論邏輯上看,李嘉圖等價原理已經(jīng)指出,過度負債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將當前問題推給未來的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更為嚴重的是,在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各國政府為了防止受到危機的沖擊,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經(jīng)濟刺激政策,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過度債務。根據(jù)BIS的統(tǒng)計,全球40個主要國家(26個發(fā)達國家和14個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總額(total credit to non-financial sector of all reporting countries,這里Credit包括負債證券和銀行信貸)從2008年第一季度的119.3萬億美元上升到了2016年三季度的166萬億美元。其中政府部門的債務總額從35.2萬億美元上升到了60.4萬億美元,上升最為明顯;居民和非盈利組織的債務總額從36.9萬億美元上升到41.2萬億美元;非金融公司的債務總額從46.7萬億美元上升到了64.4萬億美元,上升幅度也比較明顯。同期,全球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總額與GDP之比也從216%上升到246.1%,總計上升了30.1個百分點。其中政府部門債務比率上升了24.8個百分點,居民和非盈利組織債務比率降低了5.6個百分點,而非金融公司債務比率則上升了11個百分點。
顯然,考慮到經(jīng)濟增長因素,從各部門債務對GDP的占比看,只有居民部門實現(xiàn)了去杠桿,而政府和公司部門都在加杠桿。其結果是對主權債務危機的擔心不斷加劇,而僵尸企業(yè)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長期存在不斷刺激著債務膨脹,舉債人的償債能力更值得懷疑。隨著美聯(lián)儲開始加息并且不斷提高加息的節(jié)奏,新的債務危機風險有可能再次上升。盡管到2017年一季度全球債務情況略有好轉(zhuǎn),但是積重難返。
相比金融危機本身的沖擊,債務問題需要更長的時間去修復。但是更可怕的問題在于,伴隨著高企的全球債務負擔,實體經(jīng)濟增長卻不斷放緩。在全球范圍內(nèi),新常態(tài)和長期停滯的觀點正在逐漸成為現(xiàn)實。盡管加息可能會抑制債務的增長,但是由于經(jīng)濟增長放緩造成償債備付率(Debt Service Ratio或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即可用于還本付息的收入與當期應還本付息額的比值,顯然越高越好)的下降,債務風險還會持續(xù)存在,成為威脅世界經(jīng)濟長期穩(wěn)定的隱患。
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發(fā)達國家貨幣政策的決策變得越來越引人矚目。目前,美聯(lián)儲的貨幣政策規(guī)則不斷被修改,相機抉擇和政策不確定性程度不斷提高。貨幣政策的變化會不會給市場帶來意外沖擊而引發(fā)波動甚至危機?貨幣政策正常化將如何進行?中央銀行將如何與市場進行充分的溝通而又不會貽誤正常化的進程?不斷提速的加息會不會引爆債務危機?各國之間貨幣政策的分化還要持續(xù)多久?各國之間的宏觀經(jīng)濟政策如何協(xié)調(diào)?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將直接關系到宏觀經(jīng)濟的穩(wěn)定。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危機十年以后,對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討論和警示聲不絕于耳。
社會思潮動蕩
1929年的大蕭條,曾經(jīng)給當時的社會思潮帶來深刻的沖擊,且影響深遠。而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言,雖然目前還不能斷言其也會造成深遠、重大的影響,但已經(jīng)可以看到社會思潮的轉(zhuǎn)向和相應的政策變化。在危機爆發(fā)后不久,美國就出現(xiàn)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不少國家也出現(xiàn)了社會動亂。雖然這些已經(jīng)過去,但是危機促使人們反思以往的政策和理念。毫無疑問,全球化加速了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這就使得逆全球化思潮開始逐漸顯現(xiàn)。如果說因為受到危機沖擊,這些思潮在英國脫歐和歐洲大選中得到反映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金融危機策源地和溢出國——美國,逆全球化和貿(mào)易保護主義主張能夠幫助特朗普取得總統(tǒng)競選的勝利,就更加令人深思。
特朗普不僅在競選中利用了危機以后美國選民對于全球化的不滿,而且一改以往政客的風格,執(zhí)政后更雷厲風行地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提案。除了進行稅改、修建邊境墻、廢除奧巴馬醫(yī)改以及反對法條主義等反建制派的政策之外,在特朗普主張“美國第一”的理念下,其所提出的要提升美國經(jīng)濟實力、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讓制造業(yè)企業(yè)回流、消除美國巨大的貿(mào)易逆差,以及用創(chuàng)新推動經(jīng)濟增長等,都離不開貿(mào)易保護政策的支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NAFTA),甚至退出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這些頗為大膽的政策主張,更為突出地顯示了危機十年后美國社會思潮的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貿(mào)易保護是通過所謂的公平的對等貿(mào)易表現(xiàn)出來的,即其他國家的貿(mào)易和關稅政策只有以美國為標準,才是公平的。顯然,這與二戰(zhàn)以后長期得到國際社會共識,而且也是美國在過去一直倡導和力主的自由貿(mào)易理念嚴重沖突,也否認了現(xiàn)行國際貿(mào)易秩序所承認的歷史背景和國別差異。因為,要求所有國家實行相同的貿(mào)易政策,本身就是不對等的。
目前已經(jīng)有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學者指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僅對美國的任何貿(mào)易伙伴采取制裁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赤字問題的,解決問題的根本的方法,應是對美國國內(nèi)投資與儲蓄進行宏觀調(diào)控。更有學者指出,考慮到政治動機、世貿(mào)組織成員國的制約、其他國家的報復、全球價值鏈整合以及自動化會造成美國更多失業(yè)等原因,特朗普不太可能訴諸全面保護主義。因為,如果特朗普訴諸保護主義,而其他國家不得不采取報復措施的話,美國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在兩年內(nèi)的累積損失可能會高達4.5%。這表明,貿(mào)易保護主義既害人又害己。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原因,近來特朗普政府轉(zhuǎn)而從國家安全角度處理貿(mào)易問題。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措施不僅會削弱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國際貿(mào)易體系,而且一旦調(diào)查成立,總統(tǒng)就有權繞開國會直接發(fā)布行政命令,實施懲罰性關稅或進口配額。這說明,特朗普政府仍在一意孤行,單邊主義色彩明顯,世界貿(mào)易秩序因此面臨失序的挑戰(zhàn)。
總之,金融危機十年后的世界經(jīng)濟與金融格局,乃至一些國家的社會思潮和政策導向都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進而影響到全球經(jīng)濟治理的局面。按照長期停滯的理論,擴大基礎設施的投資是走出低迷增長的一種可行路徑。特朗普執(zhí)政后的財政預算案也的確反映了這種努力。但美國嚴峻的財政形勢,則使得美國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顯得捉襟見肘,且在“美國第一”的口號下還只能局限在美國國內(nèi)。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主導的金磚發(fā)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致力于“一帶一路”建設的絲路基金,正在區(qū)域和全球范圍內(nèi)努力拉動基礎設施投資,并因此成為推動國際貿(mào)易和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全球經(jīng)濟治理中的話語權也日益上升,不僅“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響應,而且在20國集團等各種國際組織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金融危機給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經(jīng)濟治理中作用的不斷上升提供了契機,也給應對危機后的全球性挑戰(zhàn)帶來了新的思路和可能。
作者系社科院世經(jīng)政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