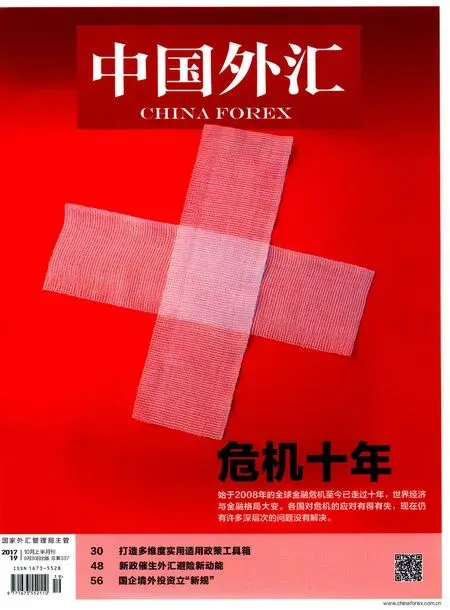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
文/謝亞軒 編輯/孫艷芳
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
文/謝亞軒 編輯/孫艷芳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全球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從高位大幅回落,呈現出六大特征。未來有望穩步走出當前的低谷。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倒閉,將美國次貸危機推向頂點,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全球國際資本流動出現劇烈波動。本文將通過回顧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國際資本流動的全過程,找出危機后國際資本流動的新特征,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并研判其未來的走勢。
呈現六大特征
第一,全球國際資本流動的活躍度遠未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
次貸危機以來的全球國際資本流動形勢就像“飛人”博爾特在退役之戰上的表現一樣:高位急跌后踉踉蹌蹌重新起步。根據麥肯錫的有關統計,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全球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達到歷史高點,年資本流動總規模高達12.4萬億美元。在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全球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從高位大幅回落。2009年,全球資本流動規模達到低點,略超2萬億美元;此后,在2010年雖低位反彈至6.4萬億美元,但其后在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下再次一蹶不振,直到2016年,全球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可能僅為4.3萬億美元,是2007年高點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二,債務性質的國際資本流動大起大落。
國際資本流動一般分為四種主要方式:直接投資、權益類證券投資、債券類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以銀行借貸和商業信貸等債權債務資本流動為主)。其中,直接投資和權益類證券投資被歸類為股權性質的資本流動,而債券類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被歸類為債務性質的資本流動。從過去的歷史經驗看,股權性質資本流動的波動性較低,穩定性較強;而債務性質的資本流動波動性高,大起大落,缺乏穩定性。這次也不例外。危機前的2000年至2007年,債務性質的國際資本流動在資本流動總規模中的占比平均高達64%;危機后,其在國際資本流動總額中的占比大幅下降至31%,僅為危機前的一半不到。其規模也顯著下降,從2007年高點時的近8萬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低點時的1萬億美元。從結構上來看,債務性質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顯著回落,是危機后全球國際資本流動活躍度遠低于危機前的重要原因。
第三,歐洲商業銀行是國際資本撤回的最主要源頭。
這一點再次表明,商業銀行對風險的容忍度低,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由于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又由于歐洲的商業銀行傳統上就在國際信貸市場非常活躍,所以,危機后當這些銀行不得不收回大量國際銀行信貸時,就成為全球國際資本撤回的主要“宗主國”或來源地。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歐洲商業銀行對外發放的信貸余額由2007年的23.4萬億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3.9萬億美元,下降了9.4萬億美元。而同期,日本商業銀行發放的國際信貸余額則由2.3萬億美元上升到3.9萬億美元,增加了1.6萬億美元;美國商業銀行發放的國際信貸余額一直維持在3萬億美元。從中不難看出,歐洲商業銀行是國際債務性資本流動規模顯著下降的主要源頭。
第四,中國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出現國際資本凈流出。
次貸危機之后,相對于發達國家之間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下降(比如銀行間的拆借和債券交易活躍度明顯降低),新興經濟體受到的沖擊更為明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45個樣本新興經濟體的統計,76%的經濟體在最近數年出現了國際資本凈流入(流入減流出)規模的顯著下降。這一比例甚至超過了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特別是2014年以來,部分新興經濟體從過去的國際資本凈流入國轉為國際資本凈流出國(注:筆者將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視為國際資本凈流出)。其中比較突出的幾個地區包括:部分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等)、俄羅斯和中國。以中國為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順差規模在2007年為911億美元,與GDP之比為2.7%;至2010年分別增長至2822億美元和4.7%。但從2014年始轉為逆差并持續3年,逆差與GDP之比分別為0.5%、4.4%和3.7%,逆差規模在2015年甚至一度高達4856億美元。
第五,新興經濟體增加持有國外資產的規模呈上升趨勢。
國際資本流入被定義為非居民投資者增加購買某國的資產,資本流出被定義為居民增加購買國外資產。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國際資本凈流入規模的下降乃至由順差轉為逆差,一方面是由于國際資本流入規模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際資本流出規模的上升。為便于理解,筆者將前者比擬為“外部矛盾”,將后者比擬為“內部矛盾”。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期間和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凈流出基本是國際資本流入規模下降所致,即主要是“外部矛盾”。而次貸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居民部門增加對國外資產的購買和持有是一個新現象,“內部矛盾”正在成為造成資本凈流出的主要原因。同樣以中國為例。2015年4856億美元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逆差中,增持對外資產帶來的資本流出為3920億美元,貢獻度高達81%;而2016年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入由負轉正為2441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出現4170億美元的逆差,則完全是因為國際資本流出大增6611億美元所致。
第六,新興經濟體所受沖擊不小但危機不多。
次貸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所受到的沖擊不小。如前所述,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國際資本凈流入規模的下降,有些經濟體甚至出現比較大規模的資本凈流出。與此相伴生,多數新興經濟體貨幣匯率出現顯著的波動。2014年以后,部分貨幣的貶值幅度和波動幅度巨大。以新興市場貨幣指數為例。受次貸危機的沖擊,該指數從2008年9月112.5的高位快速回落至2009年3月初的83.9,跌幅超過25%;此后反彈到2011年4月底的108.6之后,又開始一路下跌,到2016年1月底最低時達62.9,下降幅度超過42%;目前該指數雖已回升到71左右,但仍較2011年下降近35%。雖然不論從國際資本流動規模下降的幅度還是從匯率下跌的幅度來看,新興經濟體在次貸危機后所經受的外部沖擊都不能算小,但是爆發危機的次數卻較上世紀90年代顯著下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2008年以來新興市場僅出現了13次外部危機;而在1990至2003年,新興市場出現外部危機的次數高達20次。
波動原因探析
造成次貸危機后全球國際資本流動出現巨大變化的原因多樣,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既有國際性因素也有各個國家自身的國內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一些非經濟因素。
第一,全球風險因素解釋了危機期間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快速下降。
我們可以用VIX指數來衡量全球市場恐慌與波動程度或者說全球風險因素。該指數在2008年雷曼事件爆發和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期間,均出現過顯著的上升。研究表明,全球風險因素上升期間,各個經濟體的國際資本流入出現下降,資本撤回的情況也非常普遍,特別是銀行信貸和商業信貸的收回。對外負債頭寸比較高的國家和信貸擴張及資產價格泡沫問題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捷克等東歐國家)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因此,全球風險因素的變化解釋了國際資本流入規模在2008至2009年以及2011至2012年期間的快速下降。
第二,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顯著影響了國際資本流向。
一般認為,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債務性質的資本流動,與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有密切關系。國際清算銀行何東的研究認為,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通過貨幣政策渠道、全球金融市場渠道、匯率渠道、國際銀行信貸渠道和資產組合再平衡等多個渠道影響其他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估算,美聯儲通過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操作,向全球其他經濟體“泵出”超過4.3萬億美元的國際資金,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2009至2011年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低位反彈。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際清算銀行Eugenio Cerutti、Stijn Claessens 和 Andrew K Rose 2017年8月合寫的工作論文《全球金融周期有多重要?來自國際資本流動的證據》認為,國際銀行信貸和債券發行有關的資本流動,在次貸危機后,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敏感度顯著上升,并在2013年聯儲宣布將退出量寬時,出現的“消減恐慌”(Taper Tantrum)時達到極點,導致債務性質的資本流動規模顯著下降。這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另外一種體現方式。
第三,歐洲商業銀行大規模撤資主要是由一系列結構性因素所致。
首先,歐債危機嚴重影響到歐洲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使得這些銀行不得不撤回之前在全球投放的銀行信貸。其次,2010年以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同時出現經濟增速放緩,全球出現所謂的“長期停滯現象”。這使得國際銀行業務的風險上升,利潤率下降,也導致歐洲商業銀行重新發放國際銀行貸款的積極性下降。第三,包括中國在內的相當一部分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資本大舉涌入的情況下,采取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控制短期債務性國際資本流入,也使得歐洲商業銀行的國際信貸規模增長乏力。這方面,國家外匯管理局在2013年5月發布的《關于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13〕20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四,新興經濟體的國內制度性改革對于次貸危機后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影響顯著。
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多個新興經濟體匯率彈性的提升有助于緩沖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認為,之所以次貸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凈流出規模創歷史新高,而出現外部危機的次數卻低于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和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原因之一就是近年來多個新興經濟體的匯率彈性提升(如巴西、南非等),有效緩沖了外部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實證檢驗也表明,2010年至2015年,匯率下跌幅度超過20%的新興經濟體,其國際資本外流規模與GDP之比平均為2.3%,要遠低于匯率彈性相對低的經濟體4.5%的平均水平。其二,新興經濟體國際儲備資產同樣有助于平滑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2007年,全球國際儲備規模為3.9萬億美元,與GDP之比為25%。在美聯儲等發達國家央行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全球國際儲備規模進一步上升,到2013年達到7.5萬億美元的高點,與GDP之比為27%。此后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導致多個新興經濟體出現明顯國際資本外流的情況下,國際儲備資產開始下降,發揮了緩解外部沖擊、穩定匯率的作用。2016年,全球國際儲備的規模下降到6.6萬億美元,與GDP之比下降為24%。此外,多個國家實行的通脹目標制、保持國內價格水平穩定的政策,以及旨在防范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措施,也都功不可沒。
中國國際資本流動的多變性
次貸危機以來中國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呈現出多變性。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力巨大,資本和金融賬戶雖仍保持順差,但與GDP之比由上年2.7%的高位回落至0.9%。此后,一方面由于美聯儲開始實行非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經濟在多項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恢復了較快的增長,所以2009年至2011年中國吸引的國際資本凈流入快速反彈:2010年,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規模與GDP之比達到歷史高點的4.7%。此后,歐債危機爆發,2013年,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疊加中國國內杠桿率持續上升,經濟增速逐步下降,國際資本凈流入的規模也逐漸下降,甚至在2012年轉為凈流出。2012年年底,歐債危機風險顯著下降,2013年,中國加快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這兩個因素將2013年中國國際資本流入規模推高到創紀錄的3430億美元。從2014年開始,中國國際資本連續3年出現凈流出,其中2015年的外流規模高達4856億美元。
危機后中國國際資本流動形勢的多變性需要多維度加以解讀:一是國際因素。比如由于歐美經濟復蘇速度差異和貨幣政策分化,導致美元在2014年至2015年快速走強,使得國內企業和個人增加持有外匯資產,加快償還外幣負債的積極性上升,導致國際資本外流。二是國內因素。比如2015年6月和7月股票市場劇烈調整,導致投資者出現嚴重的恐慌情緒,對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廣義中國資產失去信心,購匯和持有外匯資產的需求顯著上升;又比如,中國對外投資戰略調整,“走出去”步伐加快等。三是周期性因素。比如2014年至2015年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內資產的吸引力。四是結構性和制度性原因。比如2015年“8·11”匯改帶來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放大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波動性等。
預計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國際資本流動活躍度處于低位的一系列結構性因素,仍然會發揮作用,包括歐洲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修復,中國等部分新興經濟體出現的高杠桿率和資產價格泡沫問題等等。此外,一些周期性因素似乎也還在對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負面影響,如美聯儲加息進程的快慢,縮表操作可能的節奏及產生的溢出效應,歐央行何時開啟退出量化寬松操作等。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經過次貸危機后的調整,全球系統性風險已呈下降趨勢,預計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收縮也將會以較慢的速度推進;此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動能正在逐步恢復,而中國國內投資者對于“8·11”匯改的理解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認識也在加深。據此預判,未來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有望穩步實現總體平衡。在此條件下,中國的宏觀決策層宜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立場,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對因私人部門增加持有海外資產而帶來的國際資本流出,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不應加以限制;同時,應以中國債券市場開放為主戰場,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流入,以利于在資本更為自由流動的新層面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作者系招商證券宏觀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