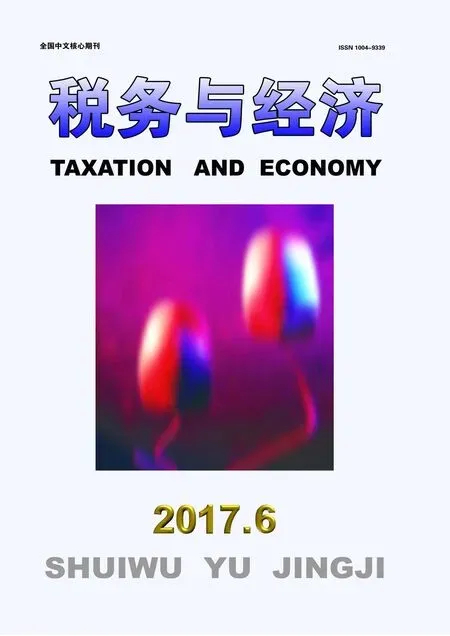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與對策研究
張達君 , 趙 鑫
(東北師范大學 商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一、引 言
2015年9月,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這標志著國家已明確細化了高技術產業未來發展的具體門類與前進方向。然而,縱觀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地理布局,長三角、珠三角以及環渤海地區已率先形成特色鮮明的高技術產業帶,相比之下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卻相對滯后,傳統老工業基地難以煥發生機并助力本土高技術產業騰飛。劉華軍、趙浩(2013)[1]曾撰文指出,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存在空間非均衡性和極化趨勢。不同地區的高技術產業因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形成了顯著的產業發展“馬太效應”。2017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再次出臺系列重要文件,啟動新一輪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計劃三年之內繼續向東北地區注入1.6萬億投資,以扭轉東北地區經濟發展劣勢。對于東北地區的高技術產業而言,只有積極把握此次振興契機,深度挖掘制約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桎梏,有效借助“工業2025”的東風,才能真正實現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的戰略突圍。
在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研究方面,方毅等(2010)[2]利用因子分析,得到了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競爭能力的評價結果。[2]孫漢杰等(2015)[3]基于規模產出水平、技術創新能力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層面,給出了提升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有效路徑。白雪飛、溫鳳媛(2011)[4]基于技術體制框架,探析了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為體現研究視角的差異性,本文著眼于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問題,試圖探析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并給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二、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5年,在產業收入方面,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為4284億元,而東部地區則高達99 930億元,西部地區也實現了14 919億元的產業收入。在產業利潤方面,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利潤總額為412億元,僅為東部地區的6.34%;其中吉林省高技術產業利潤總額最高,為1848億元,黑龍江省高技術產業利潤總額只有622億元。在產業R&D活動方面,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擁有研發機構228家,其數量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R&D經費內部支出為68.69億元,R&D項目數僅為2282項。在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方面,東北地區專利申請數為3791件,其中發明專利為2183件。這一指標與我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對比結果,如圖1所示。
專利申請數是最能夠準確衡量地區高技術產業研發能力的數據指標,根據圖1,我們不難發現東北地區在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方面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甚至與經濟同樣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相比,也形成了明顯差距。在高技術產業技術獲取與改造方面,東北地區技術引進支出為627萬元,消化吸收經費支出為5008萬元,技術改造經費支出為173 579萬元。而這三項指標全國的平均水平分別為189 232.75萬元、34 811.75萬元和1 002 142.5萬元。由此可見,東北地區高技術企業的技術獲取途徑與技術改造難度十分巨大。在高技術產業投資方面,2015年東北地區正在開展的施工項目個數為1288個,其中新開工施工項目為1031個,全部建成投產項目為1050個,總投資額達到了1172.7億元,約占同年度東北地區固定投資總額4%左右,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依然十分有限。
總體而言,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呈現出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行業規模偏低、缺乏高技術產品特色和研發經費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只有深入挖掘造成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桎梏的制約因素,才能標本兼治,扭轉高技術產業發展落后的不利局面,從而釋放其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帶動作用,最終實現東北經濟的再振興。
三、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
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可以基于自然因素、金融支持因素、產業結構因素和人才因素四個方面加以分析。其中,自然地理條件與金融支持屬于產業發展的外部制約因素,而市場機制不徹底與人才流失則屬于產業發展的內部制約因素。
1.自然地域限制。地域限制與經濟開放力度不足,極大制約了東北經濟的內外部需求。東北地區被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長白山和陰山山脈包圍,在交通運輸方面,不論是海運、陸運都遠遠不及長三角和珠三角便利,這也直接導致東北地區的生產成本節節攀升。加之東北地區冬季較長且氣候寒冷,采暖費用也進一步推升了高技術產業的經濟成本,甚至加重了重工業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與此同時,除遼寧外,東北地區沒有出海口,無法承接沿海城市轉移的經濟和技術。在對外貿易方面,與東北地區直接接壤的境外國家,僅有俄羅斯和朝鮮。歸根結底,在自然與地域層面,東北地區存在自身的封閉性和孤立性,經濟的可承載量已然有限,更無力助推高技術產業的內外部發展需求。[5]
2.高技術產業金融支持體系不完備。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根本在于不斷提升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但技術創新的過程是復雜而艱難的,暗藏著巨大的創新風險。加之創新研發周期較長,投入資金難以在短期內迅速回收,這也使得高技術企業難以單純依靠自有資金積累實現創新過程。而令人遺憾的是,東北地區金融市場的深度不足,融資手段單一且融資渠道匱乏,傳統金融中介基于風險防范和風險偏好的考慮,甚少向高技術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與此同時,民間資本引入計劃與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在東北地區建立,嚴格的資本管制令高技術企業不得不選擇高利貸等融資方式,而由資金鏈斷裂所誘發的連鎖反應又使得高技術企業發展更加舉步維艱。[6]由此可見,金融抑制始終是阻礙東北地區經濟增長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癥結所在。
3.市場機制不完善,私營企業發展艱難。東北地區金融市場的嚴格準入,使得眾多高技術企業資金缺口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滿足。這便引致權力在資本的配給方面起到了更加決定性的作用,使得那些更靠近權力的個體擁有更多套利空間。近年來,東北地區的市場效力遠小于其他地區,觸及資源越多的國有企業獲利越多。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掌握更多資本與話語權的當下,私企資本的稀缺、私營就業崗位減少的問題也日益暴露[7];國企高資本人力比所帶來的工資提高,更使得東北地區普遍存在對國企崗位的強烈追逐。顯然,這將最終導致私營企業發展更加受到抑制,甚至推高失業率,降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效果。追本溯源,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東北地區市場機制落實十分不徹底。資源、人力、技術、財力無法在需求和價格機制的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與自由流動。這也是令私營高技術企業無法處于自由、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的根本原因。
4.人才外流現象嚴重。國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近十年來,東北地區累積人才外流總量已超過一百萬,人才外流速度存在持續擴大的態勢。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高技術人才、高級管理層、優秀大學畢業生和生產業務骨干已成為東北地區人才外流的主力軍。對于高技術產業而言,技術和知識的創新應用均源自于產業內部的人才積累,高技術產業的競爭,根本在于人才的競爭,在于人才創造性與知識儲備的比拼。然而,隨著人口增速放緩與老齡化加重,東北地區的高技術企業已愈發無力抵御人才外流之殤。一方面,它們需要面對技術壁壘日益增強的現實;另一方面它們更缺乏吸引高技術人才落戶的比較優勢。[8]由此可見,人才制約已成為阻礙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
四、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1.提升東北地區的經濟開放度。客觀而言,東北地區的資源優勢和農產品特色十分突出,相較于京津冀地區的人口資源飽和態勢,東北地區擁有一定的分流和吸納能力。發揮自身優勢,既可以形成資源分流,又能夠緩解自身的人才緊缺困境。在國家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當下,不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吉林省絕不可坐以待斃。吉林省琿春市需要繼續加強與俄羅斯扎魯比諾地區的國際合作,推進萬能海港區和濱海邊疆區的跨越式發展,形成中俄兩國間更緊密的物流與貿易往來。黑龍江省也需要進一步打通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的線網建設,創立東北地區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只有積極借助政策契機,東北地區才能夠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與俄羅斯、朝鮮、蒙古形成更為廣泛和深入的經濟合作。也只有區域經濟的持續開放與提振,才能夠增強東北地區高技術產品的消費水平。[9]東北地區要解除思想桎梏,不遺余力地開放經濟,盤活民營企業生產力,為高技術產業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促使東北地區的高技術產業更好地煥發其正向拉動作用,助力東北地區經濟再騰飛。
2.增強區域金融市場開發的深度與廣度。在資金需求方面,廣大的高技術企業仍然存在融資困境,正規金融渠道受限,只能大量依靠民間借貸。當傳統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因風險偏好無法為高技術企業持續性輸血時,風險投資基金、天使投資人、私募基金、民間資本都需要在合規的監管框架下參與到高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過程中。誠然,對于東北地區的高技術企業而言,上述金融機構的設立并不意味著可以一勞永逸。與之配套,還需要更多政策方面的引導以及監管措施的傾斜。與此同時,進一步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也是高技術企業多元化融資的一條有利途徑。眾多發達省市諸如廣州、浙江均在此方面做了許多嘗試。但畢竟高技術產業的融資交易規模十分有限,且證監會監管限制嚴苛,因此依托資本市場實現資金融通的愿望,在短期內還難以實現。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金融機構扎扎實實地服務于高技術企業,發揮其金融功能,實現資金高效運轉,那么高技術產業勢必會不斷發展,走出融資困境。
3.深化市場化改革,釋放高技術企業活力。市場機制是通過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它充分依靠價格、供求關系和市場信號進行要素轉移與調配。深化市場改革意在協調政府與市場的主體關系,降低政府職能越位的可能,讓政府以服務型主體的姿態參與到高技術企業的經營建設中,從而起到釋放企業活力的根本目的。為此,東北地區應該在以下三方面進行深入改革:
第一,深化簡政放權,降低行政管制。簡政放權旨在將經營管理權真正交由企業主理。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是整治市場失靈的良藥,卻不是引領經濟騰飛的法寶。東北地區長期的制度僵化與思想束縛,需要政府首當其沖,做出調整與改變。
第二,切實降低高技術企業稅費。高技術企業屬于高端制造業領域,創新欲望強烈但資金供給嚴重不足,同時,企業稅費的居高不下更是給其成長增添了不小的負擔。根據國聯證券研究所的調查,東北地區高技術企業的平均稅負趨近40% 。雖然地方政府已部分降低企業的經營性服務收費,但地方性行政收費名目依然較多且費率偏高,即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東北地區需要出臺力度更大的稅費減免措施,切實降低高技術企業的經營負擔,使其能夠將有限的資金專注于技術研發與市場拓展。
第三,放松行業管制,推進高技術產業融合發展。伴隨著市場的成熟與科技的進步,高技術產業的融合趨勢已愈發顯著,而這也是高技術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產業融合意味著原有產業邊界日漸模糊,技術資源互相滲透,產品附加值顯著提升。對于東北老工業基地而言,放松行業管制,允許技術、資源、人才實現跨行業流動,形成高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式發展,是助力東北經濟振興發展的源動力。這種產業融合方式使得最終產成品可兼具兩大產業之所長,形成性能與特質的雙疊加,令其更易于被消費市場接受。與此同時,這種產業融合的正向溢出效應也將深刻惠及傳統產業自身,技術進步與創新理念的協同作用也將助力傳統產業煥發出新的生機。
4.形成有效的人才培養與激勵機制。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核心在于人才優勢,因此,高技術產業的人才儲備體系需要率先構建合理的高知型人才和高技能型人才培育機制。對于高知型人才的引進,高技術產業需要充分依托產學研合作平臺,深入加強同地方高等院校、國家級創新實驗室等科研組織的緊密合作。促成生產研發與高校實驗室的無縫對接,立足于理論創新,并不斷尋求向應用式創新過渡,進而形成一套完備的科技成果轉化鏈條。高等院校也應進一步完善職稱評聘制度改革,鼓勵高校教師積極參與校企共建,對其智力勞動的成功輸出給予豐厚回饋。就高技術企業而言,企業管理層也應達成共識,為人才引進與激勵政策的落實提供更大的財力支出,不遺余力地推進與人才培育相關的硬環境和軟環境建設。對于高技能型人才而言,其用工數量要顯著高于高知型人才,因此,高技術企業的藍領用工難題,更需要職業教育機構和企業自身形成合力,加以解決。一方面,高技術企業應該建立彈性靈活的薪酬進階機制,懲罰分明,給予高技能型人才更多自主權,鼓勵其夯實工藝技能。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更加注重東北地區的高職教育,扭轉守舊思維,注重新生代技術人才的專業培訓,讓更多優秀畢業生參與到高技術產業的運營與生產中去。
5.加強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建設。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的建立旨在提升高技術產業的創新決策能力、健全技術創新的市場指引和有效協調產學研各層次交流合作。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建設內容,分別是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機制建設、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建設和高技術產業園區建設。
在自主創新機制建設方面,高技術企業應主動出擊,將技術創新研發模式由模仿型創新向自主型創新逐步轉變。將更多的研發資金和人才投向自我知識產權的開發與應用。高技術企業需要樹立內部攻破核心技術的信心,在對外部技術引進、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實現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并在此之上進行再創新,從而最終掌握企業技術開發的真正主導權。
在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建設方面,東北地區需要更加注重技術交易轉讓平臺的建立與完善。技術交易轉讓平臺可以聯通關鍵技術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形成有效技術資源對接;其價格發現機制也能夠為技術供給者提供最為優厚的專利轉讓回報。與此同時,技術創新服務體系還可以發揮其信息中介的優勢,為區域內的高技術企業發布更多商業交流、科技培訓、產品展示和合作共建等信息。以吉林省機器人產業為例,截至2016年末,省內僅有北方罐裝集團一家企業加入了全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由此可見,閉塞的產業研發現實,需要完善的創新服務體系對其持續改進,而這也是增強企業自主研發實力的有力突破口。
在高技術產業園區建設方面,政府應鼓勵中小高技術企業積極加入地方高技術產業園區,強化風險管理,努力招商引資,打造創新特色,讓高技術產業園成為科技興省的先導。通常,優惠的科技政策與幫扶措施并不會輻射至全部高技術企業,但這些有利舉措將向各大高技術產業園區優先傾斜。只有加強高技術園區的內部基礎設施建設,集成創新孵化體系,形成產學研金融一體化的服務網絡,才能夠打破東北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讓高技術產業騰飛的夢想,照進現實。
[1]劉華軍,趙浩.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空間非均衡與極化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 2013,(10).
[2]方毅,林秀梅,徐光瑞.東北三省高技術產業競爭力提升策略研究[J].軟科學,2010,(3).
[3]孫漢杰,李春艷,秦婷婷.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升級能力評價比較研究[J].經濟縱橫,2015,(12).
[4]白雪飛,溫鳳媛.東北地區高技術產業技術體制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4).
[5]張娜,楊秀云,李小光.我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5,(1).
[6]關欣,喬小勇,孟慶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
[7]Hangyeol Seo,Yanghon Chung,Hyungseok (David) Yoon. R&D Cooperation and Unintende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ole of Appropriability Regimes and Sectoral Characteristics[J].Technovation,2017,(6).
[8]劉筱,Jung Won Sonn,王錚.弱研發城市的高技術產業發展——以深圳高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為例[J].科學學研究,2014,(1).
[9]肖剛,等.中國區域高技術產業發展差異的時空演變[J].中國科技論壇,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