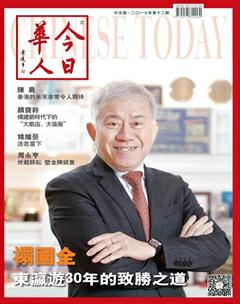一切景語皆情語
溫秋園+程晨
一幅《夢中的布達拉》,將她對自然和人間世相的理解與體悟表達得透徹,她擅畫云,尤擅畫西藏禪意之云。云,也正是她精神升華的內在觀照。畫中,天空是大舞臺,云是舞臺上的主角,云團無停歇翻捲呼嘯,云層在推移中淡化或疊積,無拘無束,趨於主觀,或放懷超然,或充滿禪意,滲透著某種隱喻性特徵和象徵性義涵,流露出她的智慧與慈悲心境。
選擇:於生活乏味處 追尋詩和遠方
那時候,人生在她心底深處的樣子,應該是詩和遠方,是一縷縷金燦燦的陽光,可生活卻是掉落了一地雞毛這般,枯燥乏味。她陷入了憂郁、焦躁和自我否定中。
生於書畫世家,對母親的畫室充滿好奇,一雙眼睛總被畫布上勾勒出的繽紛世界所吸引——這是李謙謙小姐有關童年的深刻印記。受家庭氛圍熏陶,李謙謙小姐自小喜歡畫畫,小學至中學階段,她的繪畫稟賦更是有了發揮空間,作品常常代表學校參加市裏的美術比賽並屢次獲獎。
直到高中文理科分班,李謙謙小姐繪畫的熱情絲毫沒有褪減,反而日漸濃厚。從一開始的為順父母意選擇了理科班,到後來聽從內心想法改選了文科,李謙謙小姐在人生第一次重要決定中選擇了畫畫,選擇了藝術。當她後來因種種原因感到迷茫、動搖時,卻同時有種種理由支撐自己堅持下去。既然選擇了,便無怨也無悔。

她開始跟著父母系統地學習素描和速寫。對於從小手腳靈活的李謙謙小姐而言,講究手感、靈感與速度的速寫不是難事,而學好注重畫作整體達到唯美,以準確表達畫者內心情感的素描,卻要煞費苦心。在學習描畫石膏頭像和人物頭像時,為更快掌握人物五官及頭部的基本結構與立體感的塑造方法,李謙謙小姐常把自己的頭當作練習模型,通過觸摸臉部來感受其凸凹的感覺。
1999年,李謙謙小姐考入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在校四年間,涉獵各種美術、美學課程,不斷從書中汲取藝術的養分。每天黃昏時分,總會有個女孩的身影出現在校園一角。那是她捧著素描本,在一筆一畫執著於埋頭創作。習畫的本子寫了一本又一本,每有所得便欣喜不已,這種滿足感,串連起她在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四年的學習時光。

大學畢業後,原以為可以如愿走上理想的工作崗位,繼續追逐甜蜜的夢想,可生活並不給她做這樣的安排。畢業之初,李謙謙小姐被安排到北京文化局做基層文化服務工作。起稿文件、組織文化活動、調解居民矛盾等,成為她每天的日常。單調乏味的生活,讓她幾近忘記了那個渴望畫畫的初衷,調色盤和毛筆,以及那為她繪出五顏六色的夢想的顏料,這開始一遍遍地揪痛她的心。
那時候,人生在她心底深處的樣子,應該是詩和遠方,是一縷縷金燦燦的陽光,可生活卻是掉落了一地雞毛這般,枯燥乏味。她陷入了憂郁、焦躁和自我否定中。
她想到了改變。從小骨子裏就有的倔強,讓她從不滿足於平庸的當下,在她腦海中,那個遠在未來的天空,五彩繽紛,流云朵朵。於是,她重新拾起塵封已久的畫筆,工作之餘堅持創作,日子一天比一天讓她更有期待。之後,她又進入北京畫院研修,師從王文芳老師和莊小雷老師,得老師真傳。在創作過程中,李謙謙小姐還幸運地得到了著名畫家官其格、丁紹光老師的指導,繪畫技藝日益見長。
修行:墨彩日臻化境 筆意自成一格
藝術好比修行,修行的路總是艱辛的,但付出了汗水與堅韌,人生報她另一種斑斕。
在堅持創作的過程中,李謙謙小姐對人生、對生命似乎有著更深刻的感悟和體會。她開始慢慢感悟到,那個童年時父親追問自己“蛋炒飯怎麼炒才好吃”的問題,今天終於有了答案。蛋炒飯要炒得好,就要炒到米粒在鍋裏蹦起來,好像米粒在鍋中跳舞一樣。她說生活就像蛋炒飯,每一天若過得像米粒在跳舞一樣動人,人生便也有了色彩和意義。
藝術好比修行,修行的路總是艱辛的,但付出了汗水與堅韌,人生報她另一種斑斕。不甘平庸的心,使得她的藝術造詣日臻化境,她筆下那些畫筆、那些水墨,已讓她揮灑得遊刃有餘。《眷戀晨曦》《春韻》《守望靈山》《關照般若》《荷月邂逅?地藏寺》……一幅幅或莊嚴或活潑,或章法恣肆或佈局有致的畫作在她筆下誕生,部分作品先後刊登在《美術》《世界美術》《WOMEN OF CHINA》《藝術經緯》等專業主流刊物上,其人還榮獲“首都優秀中青年文藝人才”稱號。
隨著知名度的不斷提高,李謙謙小姐的作品從“養在深閨人未識”,開始被更多人所知,並逐漸走進各類大型展覽中。作品《西藏的天空》入選美國洛杉磯“國際現代油畫大展”;《寂寞的天空》入選澳門“國際油畫藝術大展”;《荷月邂逅·地藏寺》入選中國美術館“北京意向?美麗延慶美術作品展”;《她的天空》入選“回望中國?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美術展”;《再創新的輝煌》入選“中國名家畫北京——主題創作展”;《夥伴》入選“青春芬芳?全國文化系統青年美術書法展”等,作品多次獲得國際、國家及省市級獎項,並先後被中國美術館、北京畫院、北京市委市政府等機構收藏。
大大小小的獲得,累積成她對藝術更高的向往和追求。當內心渴望抵達的東西終於如愿來到自己面前,一切的追求似乎都變得值得,一切的期待也都不再形同虛無。
藝道:恭默而守靜 極簡而至深
王國維先生在他的《人間詞話》中寫道:“昔人論詩,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世間一切藝術,大抵都是如此,繪畫也不例外。
藝術上的創新是繪畫永遠不變的主題,在繪畫中創造出既有表現力,又符合時代特徵的藝術作品,是每一位藝術者所追求的目標。多年的沉淀,讓李謙謙小姐形成了獨特的繪畫風格。無論是寫實的風景、寫意的物象,還是對人物的描畫,其別出心裁的構圖、色彩的表現和形式的張力,總會表現出獨特的藝術內涵。其畫作所表達的豐富的細節與視覺效果,恰是畫家心境的寫照,容易讓人產生強烈的意識回響和心靈共鳴。
縱觀李謙謙小姐的藝術作品,有一個永恒不變的特點,那就是“借景抒情”。借用一切外物承載內心的主觀投射,以表達一種藝術的直觀和生命的主觀,是李謙謙小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手法。
王國維先生在他的《人間詞話》中寫道:“昔人論詩,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世間一切藝術,大抵都是如此,繪畫也不例外。李謙謙小姐尤喜以自然入畫,自然中的一切景物皆能引起她內心情感的波動,讓她付諸筆端,形成景語;而筆下任何用來描繪景物的繪畫語言,也都是她表情寄意的載體,景與情,情與景,二者相因相成,不可分離。
李謙謙小姐的創作尤以云居多,很難想象外表纖柔的她,內心卻蘊藏著如此巨大的創作熱情和力量。她常說,風景畫是對自然的選擇,而不是簡單的復製,要義在人而非在自然本身。自然本就有生命,李謙謙小姐的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她把云從自然中抽象出來,賦予其獨立的品格。云的變化和流動,張弛與閉合都具有抽象的形式感,她在這裏得到充分的自由,再現與抽象融為一體,沒有任何的束縛。實際上,李謙謙小姐正是通過對云的表現來表達她的個性,云被人格化了,既是個性化的藝術再現,也是其自我人格的表現。
云的氣勢也是李謙謙小姐畫出來的,毫無疑問,只有對云有某種獨特的感受才可能把云畫成這樣。“風景之所以有打動人的力量,是因為人的感情移入。”從更深層次來說,李謙謙小姐的云,是她生命主觀的最高呈現。對她來說,生命的主觀遠比藝術的主觀更加重要,作為藝術作品,風景是藝術家把自然畫成了風景,這是藝術的直觀。而畫家生命的主觀表現在她在創作一幅畫時,怎樣調動記憶中對事物的固定印象,借由它在當下將生命串連起來,以表達對過往的追憶,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在李謙謙小姐這樣的畫作面前,我們感受到的就不只是云的表現,還有這種表現中的神情,這樣的云,讓她為自己的情結找到一種有效的表達方式。
那麼,李謙謙小姐這種生命的主觀呈現,是如何借藝術手段表現出來的呢?這要談到她的創作技巧。欣賞她的畫作,不難發現,她總是把地平線壓得很低,為云的湧動變幻留下廣闊空間。在山後,云仿佛是從山間拔起,頓時風起云湧,變化莫測。山前,云氣又從眼前消失,戈壁草原無限遼遠,云朵在遠方的地平線上緩慢地移動和變化,尤其是落日時分,在餘輝照映下,幾分蒼茫,幾分壯麗,如此便能在佈局空間上取勝。
在表達上,李謙謙小姐更趨向於把物象抽象化,特別是那些截取云的某一片斷的畫面,筆觸、色彩及其形式都統一在抽象的結構中,使人感受到視覺的衝擊和氣勢的壓力。她仿佛是把客觀的形象轉換為抽象的語言,實現她在形式表現上的衝動與渴望。有畫家評論她是用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在創作,而這種形式不只是視覺的美感,還有更深的含義,即記憶的形象和生命的召喚。其畫作《她的天空》,大概就是這類創作的代表,在這幅作品中,瞬息萬變的天空和云彩,對於恒定的生活和外境,更加充滿著一種視覺的誘惑,那種戲劇性的不確定因素,每時每刻都有一種新的可能發生,讓人在一片虛無中充滿對“壯觀”的期待。
“藝術不是技巧的活兒,而是心靈需要堅守的活兒。”李謙謙小姐常常這樣告訴自己。也許在每一次埋頭走路之時,眼下的風景就觸及內心的某個角落,進而讓人迸發出創作的靈感,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但在這條路上,藝術家的心注定是孤獨的,因為唯擁有恭默、守靜的心靈,外界的美好才會源源不斷地來到人的生命中。李謙謙小姐正是這樣的堅守者,不俗媚,極簡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