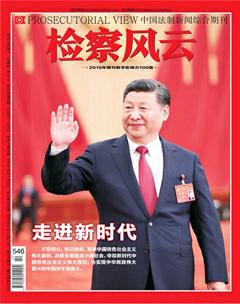破解整治傳銷的法治難題
阮傳勝
傳銷活動(dòng)為何屢禁不止、屢治不絕呢?這其中的原因應(yīng)是多方面。其中,法律方面的現(xiàn)實(shí)難題尤其需要破解。
整治傳銷活動(dòng)的立法歷程
回顧我國(guó)整治傳銷的立法歷程,最早當(dāng)屬1998年4月國(guó)務(wù)院下發(fā)的《關(guān)于禁止傳銷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的通知》。該《通知》第1條強(qiáng)調(diào):“傳銷作為一種經(jīng)營(yíng)方式,由于其具有組織上的封閉性、交易上的隱蔽性、傳銷人員的分散性等特點(diǎn)……嚴(yán)重?fù)p害消費(fèi)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jīng)濟(jì)秩序。因此,對(duì)傳銷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必須堅(jiān)決予以禁止。”但該《通知》未對(duì)傳銷概念進(jìn)行界定,有混同傳銷和直銷之嫌。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情節(jié)嚴(yán)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fù)》指出:“對(duì)于1998年4月18日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禁止傳銷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的通知》發(fā)布以后,仍然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dòng),擾亂市場(chǎng)秩序,情節(jié)嚴(yán)重的,應(yīng)當(dāng)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xiàng)的規(guī)定,以非法經(jīng)營(yíng)罪定罪處罰。”這里,也沒有具體界定傳銷與直銷的區(qū)別。
按照該司法解釋,對(duì)具有經(jīng)營(yíng)內(nèi)容的傳銷行為按照非法經(jīng)營(yíng)罪處理,對(duì)以傳銷為名實(shí)施的詐騙以詐騙犯罪處理。需要指出的是,其后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適用法律時(shí)有現(xiàn)實(shí)的難題。作為傳銷活動(dòng)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拉人頭”傳銷并不完全符合非法經(jīng)營(yíng)罪的特征,造成實(shí)踐辦案中適用法律的困難,也嚴(yán)重影響了打擊傳銷的工作力度與效率。“拉人頭”傳銷是指欺騙他人發(fā)展人員或者繳納一定的費(fèi)用,才能取得入門資格。這種傳銷活動(dòng)既沒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務(wù),不存在真實(shí)的交易標(biāo)的,實(shí)際上也沒有“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按照前述《批復(fù)》適用非法經(jīng)營(yíng)罪進(jìn)行打擊。這樣,也給整治傳銷活動(dòng)的司法實(shí)踐帶來(lái)了現(xiàn)實(shí)的困難。
直到2005年9月,國(guó)務(wù)院同時(shí)頒布了《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xiàng)l例》,才區(qū)分了傳銷和直銷的概念,在法律立場(chǎng)上禁止傳銷和允許直銷。《禁止傳銷條例》將“傳銷”定義為:“組織者或者經(jīng)營(yíng)者發(fā)展人員,通過對(duì)被發(fā)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fā)展的人員數(shù)量或者銷售業(yè)績(jī)?yōu)橐罁?jù)計(jì)算和給付報(bào)酬,或者要求被發(fā)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fèi)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jīng)濟(jì)秩序,影響社會(huì)穩(wěn)定的行為。”《直銷管理?xiàng)l例》將“直銷”定義為:“是指直銷企業(yè)招募直銷員,由直銷員在固定營(yíng)業(yè)場(chǎng)所之外直接向最終消費(fèi)者(以下簡(jiǎn)稱消費(fèi)者)推銷產(chǎn)品的經(jīng)銷方式。”
上述規(guī)定試圖將直銷與傳銷加以區(qū)別:直銷須有使用價(jià)值的產(chǎn)品;傳銷則沒有具有使用價(jià)值的產(chǎn)品。但是,在現(xiàn)實(shí)中,部分直銷企業(yè)存在著違規(guī)經(jīng)營(yíng)的行為,導(dǎo)致公眾對(duì)直銷存在著誤解和認(rèn)識(shí)誤區(qū),常常對(duì)直銷與傳銷難以界分。
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后增加一條:“組織、領(lǐng)導(dǎo)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wù)等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fèi)用或者購(gòu)買商品、服務(wù)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jí),直接或者間接以發(fā)展人員的數(shù)量作為計(jì)酬或者返利依據(jù),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騙取財(cái)物,擾亂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秩序的傳銷活動(dòng)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罪名為“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
2010年頒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公安機(jī)關(guān)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二)》第78條規(guī)定,涉嫌組織、領(lǐng)導(dǎo)的傳銷活動(dòng)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jí)在3級(jí)以上,應(yīng)予立案追訴。認(rèn)定何為“情節(jié)嚴(yán)重”,主要應(yīng)從行為人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涉案的財(cái)物金額,誘騙、發(fā)展參與傳銷人員數(shù)量,給他人造成財(cái)產(chǎn)損失的數(shù)額或者造成其他后果的情況,傳銷活動(dòng)影響社會(huì)秩序的程度等方面考慮。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lián)合印發(fā)《關(guān)于辦理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jìn)一步明確了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的有關(guān)法律適用問題。例如,明確了傳銷組織層級(jí)及人數(shù)認(rèn)定等操作層面的問題。
整治“傳銷”活動(dòng)的法治難題
傳銷活動(dòng)具有多重社會(huì)危害。一是瓦解社會(huì)倫理體系,破壞社會(huì)穩(wěn)定基礎(chǔ)。二是侵犯公私財(cái)產(chǎn),破壞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三是引發(fā)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破壞社會(huì)治安秩序。特別是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軟件、自媒體以及第三方支付平臺(tái)的發(fā)展,涉?zhèn)麂N信息傳播更為廣泛,涉案資金轉(zhuǎn)移更加迅速,社會(huì)危害更嚴(yán)重。
從認(rèn)識(shí)層面看,“重拳出擊”整治傳銷活動(dòng)已成為社會(huì)的共識(shí)。問題是,這個(gè)重拳究竟重到什么程度?依照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整治“傳銷”活動(dòng)是否屬于“重拳出擊”?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能否承載與貫徹我國(guó)“寬嚴(yán)相濟(jì)”的刑事政策?
根據(jù)《禁止傳銷條例》,傳銷有拉人頭計(jì)酬、收取入門費(fèi)和團(tuán)隊(duì)計(jì)酬這三種傳銷方式。但在刑法第224 條關(guān)于傳銷的概念中,只規(guī)定了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fèi)的傳銷形式,去掉了具有經(jīng)營(yíng)內(nèi)容的團(tuán)隊(duì)計(jì)酬的傳銷形式。至此,刑法關(guān)于傳銷犯罪的規(guī)定調(diào)整范圍較窄: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的“傳銷”不包括有經(jīng)營(yíng)內(nèi)容的傳銷。如遇包含有少量經(jīng)營(yíng)內(nèi)容的“傳銷”,整治起來(lái)必然會(huì)遇到困難。
現(xiàn)行刑法對(duì)于整治傳銷活動(dòng)遵循的刑事政策是傳統(tǒng)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刑事政策。實(shí)際上,參與傳銷的人要么被洗腦,不會(huì)認(rèn)為自己被騙,要么本身也是積極發(fā)展下線的獲利者,只是未達(dá)到刑法的追訴標(biāo)準(zhǔn)。依據(jù)現(xiàn)行刑法中對(duì)“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的規(guī)定,公安機(jī)關(guān)只能對(duì)傳銷的“組織者、領(lǐng)導(dǎo)者”予以刑罰,但傳銷組織大多采用單線聯(lián)系、隱秘發(fā)展、份額傳承等規(guī)避手段,發(fā)展的下線人數(shù)是否達(dá)到“30人以上且層級(jí)在三級(jí)以上”難以準(zhǔn)確認(rèn)定,導(dǎo)致難以追究傳銷頭目的刑事責(zé)任。
同時(shí),傳銷案件證據(jù)收集也十分困難。伴隨互聯(lián)網(wǎng)的飛速發(fā)展,部分傳銷組織借助網(wǎng)絡(luò)來(lái)實(shí)施其傳銷犯罪行為,通過將服務(wù)器設(shè)置在境外等形式,增大公安機(jī)關(guān)的打擊難度。由于電子數(shù)據(jù)易被篡改和刪除,一旦服務(wù)器數(shù)據(jù)提取不及時(shí)或不全面,對(duì)傳銷組織的募集登記、層級(jí)管理、利潤(rùn)分紅、發(fā)展人數(shù)等情況均難以在網(wǎng)站上找到相應(yīng)的電子數(shù)據(jù),導(dǎo)致相關(guān)證據(jù)難以被保全。endprint
即使成功抓獲了犯罪嫌疑人,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刑事打擊也只能針對(duì)30名以上且層級(jí)在三級(jí)以上的下線傳銷頭目人員,對(duì)其他人數(shù)眾多卻構(gòu)不成刑事處理的傳銷中低層人員,只能進(jìn)行行政處罰。對(duì)于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活動(dòng)的人員,也只能根據(jù)《禁止傳銷條例》規(guī)定,由工商部門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以罰款。許多傳銷人員本身無(wú)正當(dāng)職業(yè)及經(jīng)濟(jì)來(lái)源,無(wú)法對(duì)其執(zhí)行罰沒處罰,最后只能遣返或驅(qū)散了之,起不到教育震懾作用。
實(shí)踐中,傳銷可能引發(fā)的違法犯罪遠(yuǎn)不止“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罪”。傳銷行為往往伴隨暴力型和非法拘禁型犯罪,可能涉嫌的罪名還有非法拘禁罪、綁架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其中又以非法拘禁定罪的占比最多。不可否認(rèn)的是,相比普通詐騙犯罪騙取3萬(wàn)元以上就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罪需要騙取資金250萬(wàn)以上或者參與人數(shù)120人以上才能認(rèn)定為情節(jié)嚴(yán)重,從而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之取證困難,這導(dǎo)致實(shí)踐中僅有很少部分的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人員被懲治。此外,實(shí)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以非法拘禁罪這種輕罪來(lái)處理傳銷活動(dòng)中的組織者、領(lǐng)導(dǎo)者也往往是由于對(duì)傳銷取證難的無(wú)奈之舉。
破解整治“傳銷”活動(dòng)的法治難題
對(duì)于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首選需要改變的是傳統(tǒng)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刑事政策。這種刑事政策對(duì)打擊一些團(tuán)伙性犯罪,不無(wú)一些作用,但對(duì)于傳銷這種復(fù)雜的涉眾犯罪,并不太合適。與之前的非法經(jīng)營(yíng)罪相比,這個(gè)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的刑罰尺度并沒有體現(xiàn)“嚴(yán)厲打擊”的立法意圖。現(xiàn)實(shí)中,傳銷活動(dòng)所造成的犯罪后果之嚴(yán)重,遠(yuǎn)超非法經(jīng)營(yíng)對(duì)經(jīng)濟(jì)秩序的單一損害。很多時(shí)候,傳銷分子為了達(dá)到目的,往往還采取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綁架等犯罪手段,對(duì)被害人的人身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實(shí)施直接的侵犯。在這種情形下,仍以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dòng)罪處置,顯然打擊力度偏輕,難以體現(xiàn)罪責(zé)刑一致的刑法原則。正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學(xué)者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對(duì)刑罰必定性的闡述:“對(duì)犯罪最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yán)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對(duì)傳銷活動(dòng)的法律懲治也是如此,法網(wǎng)恢恢,方能疏而不漏。
建議降低對(duì)傳銷活動(dòng)組織、領(lǐng)導(dǎo)者的刑事追訴標(biāo)準(zhǔn)。建議在刑事法律層面,降低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罪的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提升對(duì)傳銷的刑事打擊效果。現(xiàn)有的追訴標(biāo)準(zhǔn)與當(dāng)前傳銷組織出現(xiàn)的小規(guī)模分散聚集、裂變式發(fā)展、通過提高“入門費(fèi)”門檻減少人員規(guī)模等新情況不相適應(yīng),建議將該標(biāo)準(zhǔn)修改為“組織內(nèi)部參與傳銷活動(dòng)人員在20人以上或者層級(jí)在三級(jí)以上的”。
為有效打擊傳銷違法犯罪,需制定執(zhí)法、司法統(tǒng)一適用的更加具體明確的實(shí)施意見,確保各地公檢法機(jī)關(guān)在對(duì)傳銷案件的證據(jù)認(rèn)識(shí)、案件定性、量刑等方面的有效統(tǒng)一,增強(qiáng)依法打擊傳銷犯罪的震懾力。同時(shí),對(duì)組織、領(lǐng)導(dǎo)、參加傳銷活動(dòng)的行為人的行政處罰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也應(yīng)降低、細(xì)化。
欣慰的是,2017年1月,公安部在官網(wǎng)發(fā)布《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huì)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33條將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行為、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活動(dòng)、多次參加傳銷活動(dòng)行為納入行政處罰的范圍。
該草案擴(kuò)大了法律規(guī)制的范圍是值得肯定的。該草案對(duì)傳銷人員區(qū)分為一般的參加者和組織策劃者,沒有發(fā)展下線、僅僅是偶爾參與傳銷的人員是一般的參加者,對(duì)該部分人員以教育、遣散為主,對(duì)多次參加傳銷活動(dòng)的,處“五日以下拘留”。發(fā)展下線但尚不構(gòu)成刑事犯罪的組織策劃者(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活動(dòng)的),則一律適用行政拘留,加大懲處力度,形成對(duì)組織策劃者的全方位打擊。
在執(zhí)法層面,對(duì)于傳銷的打擊,目前主要由工商、公安負(fù)責(zé)。但過去實(shí)際工作中,兩部門常常出現(xiàn)協(xié)調(diào)不力的情況。對(duì)此,傳銷案件辦理不妨實(shí)行兩部門同步介入。現(xiàn)在傳銷組織的活動(dòng),多利用私人住宅,許多團(tuán)伙力量非常強(qiáng)大,對(duì)此工商部門往往感到無(wú)力,只有公安同步介入,才能提高執(zhí)法的效率和震懾力。同時(shí),公安同步介入,還有利于及時(shí)取證,為后期的刑事追訴提供便利。針對(duì)一些執(zhí)法部門打擊傳銷中工作怠惰,對(duì)公眾舉報(bào)和求助不聞不問的情況,也需加大追責(zé)力度,提高地方官員對(duì)于傳銷活動(dòng)的重視程度。
此外,傳銷活動(dòng)已然升級(jí),其絕大多數(shù)既無(wú)公司又無(wú)產(chǎn)品,取證很難,還有的公司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模式進(jìn)行金融傳銷,這就牽扯到第三方支付、資金存管問題,會(huì)涉及央行、銀監(jiān)會(huì)等部門,僅僅依靠工商和公安兩個(gè)部門,很難進(jìn)行有效查處,亟需多部門形成合力。鑒此,法律也要針對(duì)這些金融傳銷頒布一些有針對(duì)性的與時(shí)俱進(jìn)的規(guī)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