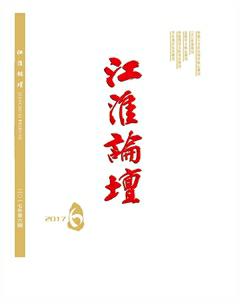論馮友蘭現代進步哲學史觀
徐建勇
摘要:馮友蘭現代進步哲學史觀源于其進步的歷史觀。從歷史角度來看待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性,他得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古今時代的不同,是社會類型的不同,從而在社會歷史領域確立了他的進步史觀。之后,馮友蘭將這種觀點應用到中國哲學史的整理研究和中國哲學的創作發展之中,寫出了《中國哲學史》和“新理學”等著作。它們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思想內容上,都貫穿了進步的主線,為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和中國哲學的發展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形式;歷史;義理;新理學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6-0074-005
一
“五四”時期關于文化的爭論,對馮友蘭產生了很大影響。馮友蘭通過自己的深入思考,逐漸拋棄了淺顯的中西文化表象比較,而走向了更加宏觀和深入的社會歷史之中。一是從縱向的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中西文化上的差異,馮友蘭認為就是古今時代不同,即西方已經發展到了現代,而中國文化仍然停留在古代。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后,是因為它是古代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先進,是因為它已經發展到了現代文化。他說:“在‘五四運動時期,我對于東西文化問題,也感覺興趣,后來逐漸認識到這不是一個東西問題,而是一個古今的問題。一般人所說的東西之分,其實不過是古今之異。我在20年代所作的《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牽涉到這個問題。我的那部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證明,各派的人生理想,是世界各國的哲學史中都有的。很難說哪些理想是西方所特有的,哪些理想是東方所特有的。在30年代,我到歐洲休假,看了些歐洲的封建時代的遺跡,大開眼界。我確切認識到,現代的歐洲是封建歐洲的轉化和發展,美國是歐洲的延長和發展。歐洲的封建時代,跟過去的中國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異。至于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應該說是近代化。”[1]196二是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中西文化,馮友蘭認為就是社會類型的不同,即西方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以工業生產為主的城市社會,而中國仍然停留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鄉村社會。他說:“所謂東方和西方的差別,實際上就是鄉下與城里的差別。”[1]198通過這樣的認知,馮友蘭首先在社會歷史領域確立起了自己的進步觀。
在社會歷史領域確立了進步的觀點之后,馮友蘭將其應用到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哲學創作活動之中,先后寫出了三部哲學史和“貞元六書”,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
將進步史觀運用到哲學史的整理之中,馮友蘭首先寫出了《中國哲學史》上下卷。這一著作,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思想內容上,都貫穿了進步的主線。
在思想上,馮友蘭以進步歷史觀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古代哲學的觀念變遷,認為后人的哲學觀念較之前人的觀念總有進步。例如:中國傳統學術有漢學與宋學的區別,漢學注重考證、訓詁,宋學重義理。馮友蘭認為考證和訓詁做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向前進一步,去體會和了解文字背后所表達的義理,所以宋學是對于漢學的發展和進步。他說:“社會組織,由簡趨繁;學術由不明晰至于明晰。后人根據前人已有之經驗,故一切較之前人,皆能取精用宏。故歷史是進步的。”[2]257馮友蘭認為自己正是按照歷史的進步觀來研究和整理哲學史的,由此寫出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沒有按照漢學的治學方法,而是接著宋學的義理路徑繼續前進,所以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主要是在哲學的義理上發揮得比較多。馮友蘭認為這也正是他的《中國哲學史》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不同之處。之后,為了更加明確闡述中國哲學在歷史上是如何進步的,馮友蘭以“釋孔”為例加以說明。他認為漢代確定儒學的至尊地位后,從董仲舒開始,接下來許多學者主要的工作就是“釋孔”。如朱熹、王陽明、戴東原、康有為等等,大家都在“釋孔”,形式上看一樣,好像沒有區別,然而事實上,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哲學思想,彼此并不相同。例如康有為與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他們每個人都有對于孔子和前人的哲學思想的發揮、引申,馮友蘭認為這種發揮引申就是進步。如果我們將各個時代的哲學思想歸集到各個時代,各個人的哲學思想歸集到各個個人,則哲學史上的進步的痕跡便一目了然。對于這種哲學史上的進步,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的《自序》中,借用黑格爾的正、反、合之說加以申明。他說:“吾亦非黑格爾派之哲學家;但此哲學史對于中國古代史所持之觀點,若與他觀點聯合觀之,則頗可為黑格爾歷史哲學之一例證。黑格爾謂歷史進化常經‘正、‘反、‘合三階段。前人對于古代事物之傳統的說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說法多為‘查無實據,此‘反也。若謂前人說法雖多為‘查無實據,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2]244后人對于前人的繼承和發揚,就是歷史的進步。可以看出,馮友蘭的歷史進步觀顯然是受到西方進化論和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影響之后形成的,與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完全不同。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是循環的歷史觀,它將歷史看成是循環往復,周而復始,以至無窮。這種歷史觀認為沒有進步和發展,只是治世與亂世不斷重復往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完全拋棄了這種觀念,直以進步的觀點來看待哲學史。在這種意義上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完全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史,也可以說,是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帶入了現時代。
在形式上,用歷史進步的觀點來看待哲學的發展。第一,馮友蘭參照西方哲學史劃分上古、中古、近代的做法,將中國古代哲學劃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他認為子學時代相當于西方的上古時代,經學時代相當于西方的中古時期。歷史地看,經學時代是子學時代的發展進步,他說:“從歷史的發展說,在我稱之為經學的時代,研究學問的人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儒家的經典。”[1]180馮友蘭更認為中國傳統哲學還沒有發展到近代哲學。這種看法也與馮友蘭對中西文化的認識相關:中國文化還是古代文化,西方文化是現代文化,現代文化自然是古代文化的發展,中國要發展,就必須將自己的古代文化發展到現代文化上來。同時,馮友蘭還認為應該采用西方現代先進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他認為科學方法即是哲學方法。他說:“無論科學哲學,皆系寫出或說出之道理,皆必以嚴刻的理智態度表出之。”[2]247第二,借鑒和運用現代的學術術語來詮釋中國哲學。在哲學史中,馮友蘭基本上是從哲學、倫理、宗教、政治、藝術、社會等方面來整理和闡述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另外,如理想、人格、平等、自由、理智、純粹經驗、功利主義等西方現代概念,也是他經常運用到的。不僅如此,馮友蘭敘述的形式也是現代分析式的,他說:“在中國文字中,所謂天有五義:曰物質之天,即與地相對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謂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運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如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如《荀子·天論篇》所說之天是也。曰義理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說‘天命之為性之天是也。”[3]這種對于現代學術術語的借鑒和運用,在其早期所寫的《一種人生觀》中,表現得更加明顯。endprint
在中國哲學的內容上,馮友蘭也采用了現代哲學的分類模式來選擇中國古代史料。西方哲學包含宇宙論、人生論和知識論,三者之間相互聯系,互為依托,西方的哲學史就是這三方面自古至今的發展變化史。馮友蘭根據這一標準,對中國古代史料也進行了剪裁選用。特別是傳統思想中不重視的知識論,馮友蘭重點闡述了墨家和名家的思想。同時,他認為哲學史的發展和進步,包括兩個方面:形式的系統和實質的系統。他說:“中國哲學家之書,較少精心結撰,首尾貫串者,故論者多謂中國哲學無系統。”[2]252馮友蘭認為這應是指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沒有形式上的系統,可是中國哲學家的思想卻有實質的系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就是要從史料中,找出中國哲學進步的實質系統。他說:“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2]252更進一步,馮友蘭提出,史料的真偽,也對哲學的進步產生影響。他說:“從前研究中國學問者,或不知分別真書偽書,或知分別而以偽書為無價值,此亦中國哲學之所以在表面上似無進步之一原因。”[2]258他認為,對于史料的真偽,首先是辨別真偽,辨真偽則真知各個時代思想的真實面目。其次,偽書亦不是毫無價值,它仍然代表其產生時代的思想,所以將偽書還原到其自身的年代,使其與實際相符合。這樣它也可以和真的史料一樣,反應出中國哲學的進步。他說:“欲看中國哲學進步之跡,我們第一須將各時代之材料,歸之于各時代;以某人之說話,歸之于某人。如此則各哲學家之哲學之真面目可見,而中國哲學之進步亦顯然矣。”[2]258馮友蘭的哲學史研究,就是努力整理這些材料使其能夠反映中國哲學的發展進步。可以說,馮友蘭在這方面的努力顯然是成功的,這一點從陳寅恪的《審查報告》就可看得出來。陳寅恪說:“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為一傳燈之語錄。而龂龂致辯于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而馮君之書,獨能于此別具特識,利用材料,此亦應為表彰者也。”[2]613
對于中國近年哲學史的研究現狀,馮友蘭也提出了自己的進步觀點。這一觀點,其實也是與他以進步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哲學相一致的,是其自然的延續。只不過他在這里,用“信古”、“疑古”、“釋古”的提法分別代替了先前“正”、“反”、“合”的概念,使其更加符合中國文化的傳統習慣。他認為,“信古”一派相信古書是歷史的實錄,并以此立論。“疑古”一派以為古書所載,多非可信,并以此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張。“釋古”一派則是前兩派的中和,認為可以透過古書的記載,看到古代社會的部分真相。這三種對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態度,在近代以來也依次走過了不同的歷史時代,對社會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也反映了當時對于古代史研究的進步。在民國初年,“信古”首先出現,并成為當時古史研究的主流,例如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這種研究對于社會的影響就是當時社會上盛行的“復古運動”。這一方法的缺點在于因崇信而往往陷于盲目自大,從而行動上故步自封。“疑古”在“信古”之后出現,其態度較后者為進步。例如錢玄同的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顧頡剛的《古史辨》等,其最直接的社會影響就是開啟了“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這一態度和方法的缺點在于不離懷疑主義的窠臼,有抹殺一切的危險。總之,以上兩種態度都有偏于極端的毛病。“釋古”是研究史學進步到的第三個階段,它是前兩種態度的折中。它探索疑問,比較求證,以獲得客觀真實的歷史事實,富有科學精神。馮友蘭認為自己就是用“釋古”的態度來對待古代哲學史料的,他的《中國哲學史》就是應用這一方法的研究成果。陳寅恪對此也是積極肯定,認為《中國哲學史》對于史料的把握,“取材謹嚴,持論精確”、“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2]612 。應該說,“信古”、“疑古”、“釋古”這三個概念,不僅是馮友蘭用來指稱當年研究歷史的三個派別或研究方法,而且是馮友蘭用來描述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具有進化論的色彩。他說:“信古、疑古、釋古的三種攻研史學的態度,正若歷史進化般的有了‘正‘反‘合的三種不同的嬗變一樣。”[4]
三
將進步史觀應用到哲學創作活動,就是馮友蘭在“新理學”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進步觀念。馮友蘭認為哲學上的進步,與科學完全不同。科學上可以有日新月異的進步,哲學的進步則要緩慢得多。但是歷史地看,馮友蘭認為哲學本身也是有進步的。他說:“然全新底哲學雖不能有,或不易有,而較新底哲學則能有,而且事實上各時代皆有。”[5]16理由有三:第一,歷史上,各個時代由于物質環境、知識、語言等等實際的生活內容是不斷變化進步的,因而,各個時代的哲學家必然有對于當時時代的見解,他們用當時的語言把自己的見解說出或寫出,即是那個時代的自己的新的哲學系統。第二,各個時代相對于它之前的時代,必有新的經驗和新的事物出現,這是古人所沒有經歷過的,所以各時代哲學家對于“一時代新經驗之分析解釋,亦可成為一時代之新哲學”[5]17。第三,人們的思維能力可能古今如一,但是各時代對于思維能力的開發訓練則有不同,現代人對于思維能力的培訓遠比前人進步。例如現代人對于邏輯的研究實是大有進步,以這樣的邏輯訓練培養出來的現代人,就完全可以見前人所不見者,或者能使已有的見解更為清晰。這也能促使哲學的進步。因此,哲學總是在發展,總是在進步。他說:“一時代之哲學家之哲學,不是全新底,所以‘上繼往圣。但其哲學是較新底,其力量是全新底,所以可‘下開來學。”[5]17
具體就“新理學”而言,“新理學”之所以新,是相對于“舊理學”的,自然也是“舊理學”的發展和進步。
這首先表現在形式上的進步。第一,“新理學”是屬于現代的哲學思想,它是宋明理學的發展和進步。馮友蘭說,“新理學”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因此我們自號我們的系統為新理學”[5]4。第二,“新理學”采用的方法是現代的邏輯分析的方法,方法上是進步的,是現代的方法。“馮友蘭把‘近代化的和‘中國的作為他的哲學活動的明確追求。哲學的近代化,對他來說,就是采用西方邏輯分析方法。”[6]第三,從實際的哲學系統和本然的哲學系統看,新理學是最哲學的哲學,它“較舊理學更依照此派哲學的本然系統”[5]147,所以從宇宙的角度來看待它們,新理學不僅比舊理學更加進步,而且境界更高,是新的境界。第四,新理學既講形上,又講形下,還講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完全現代哲學的講法,這與舊理學的講法完全不同,也是進步的。第五,新理學涉及的領域較舊理學更加寬廣。它不僅涉及舊理學的人生修養論、宇宙論、政治論、歷史倫理,更涵括了經濟、藝術、教育、科學、邏輯等等現代的學科體系,具有現代的形式和內容。endprint
在思想上,“新理學”以“新”為標示,就是要以中國傳統儒家哲學現代轉化為目標。中國的近代化或現代化,一直是馮友蘭關注的核心,這也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特殊國情所決定的,是與中國的生死存亡相聯系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是馮友蘭對于近代中國國情的思考。馮友蘭用西方現代的學術方法,對中國傳統的思想進行現代的建構,由此而建立起來的新的理論體系,確實使中國傳統哲學實現了現代轉換,從而開創了現代的中國哲學學科,不僅功不可沒,而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確立和發展。新理學的理論體系主要由“貞元六書”構成,包括《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在六本書中,《新理學》講哲學的觀念系統,《新事論》講現代社會民主政治和經濟生產,《新原人》講現代人生修養和境界,《新知言》講現代方法,《新世訓》講現代社會中青年人應有的知識、態度和理想,《新原道》講哲學史的發展。每本書各有側重,又相互聯系,共同構成“新理學”的理論體系。其中,《新原人》《新事論》《新原道》更是“新理學”的應用。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始終貫徹一個“新”字,以示哲學的進步與發展。正如朱伯崑先生所說:“盡管人們對新理學的體系有這樣那樣的評論,但有一點不容置疑,即馮友蘭先生在傳統的基礎上創建新體系,推動中國哲學從傳統進入現代,并面向世界,開創了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的新局面,這是功不可沒的。”[7]
在內容上,“新理學”吸收了中國古代哲學各種流派的思想精神,特別是宋明理學的精神。宋明理學在吸取前人的經驗上,已經把高明、中庸、內外、本末、精粗等對立統一起來,在哲學思維和境界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地步。但是,馮友蘭認為“宋明道學(理學),沒有直接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所以他們所講底,不免著于形象”[8]125,故而他們所統一的高明,尚不是極高明。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先秦的道家,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都是主講形上學的,它們構成了中國哲學史上的形上學的傳統。西洋現代以來,邏輯學有了很大進步,但西洋人并沒有利用邏輯學來建立形上學,反倒是用它來批判和推翻舊的形上學,這也給新理學的構建帶來啟迪。于是,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的高明,道家、玄學、禪宗的形上學,西方邏輯學,三者構成了新理學形上學的理論來源。他說:“新理學就是受這種傳統的啟示,利用現代新邏輯學對于形上學底批評,以成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底形上學。”[8]125至此,新理學的形上學得以建立。“新理學”不僅將高明完美統一,而且也使中庸獲得極好的確認。馮友蘭認為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國哲學精神,在“新理學”中才有了“最新的進展”。[9]因此,“新理學”不但是集以往哲學之總成,而且開現代哲學之先聲。“新理學”,“它是接著中國哲學的各方面的最后底傳統,而又經過現代的新邏輯學對于形上學的批評,以成立底形上學。它不著實際,可以說是‘空底。但其空只是其形上學的內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學以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與道家,玄學,禪宗的‘空不同。它雖是‘接著宋明道學中底理學講底,但它是一個全新底形上學。至少說,它為講形上學底人,開了一個全新底路。”[8]127
總之,馮友蘭將進步史觀運用到了自己的哲學史整理和哲學創作之中,不僅成功寫出了現代中國哲學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具有進步意義的中國哲學史,而且創作了“新理學”。后者既將傳統的理學思想現代化、哲學化,也為中國哲學的創作做出了榜樣。
參考文獻:
[1]馮友蘭.馮友蘭自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2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35.
[4]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4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62.
[5]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6]陳來.“近代化的中國哲學”——從馮友蘭的哲學觀念談起[J].學術月刊,2002,(4).
[7]陳戰國.馮友蘭哲學思想研究·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
[8]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5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9]宋志明.馮友蘭的文化三說[J].中州學刊,2005,(4):140.
(責任編輯 吳 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