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huì)嵌入視角下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研究
秦 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 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院,北京 100083)
·公共管理·
社會(huì)嵌入視角下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研究
秦 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 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院,北京 100083)
中國(guó)正在經(jīng)歷從老齡化社會(huì)向高齡社會(huì)的轉(zhuǎn)變,如何積極應(yīng)對(duì)人口老齡化的趨勢(shì),需要全社會(huì)的普遍關(guān)注。本文試圖在分析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對(duì)中國(guó)不斷變化的養(yǎng)老模式進(jìn)行梳理,并基于社會(huì)嵌入視角,將不同養(yǎng)老模式下的社會(huì)嵌入構(gòu)成要素分為結(jié)構(gòu)嵌入、政治嵌入和認(rèn)知—文化嵌入,探析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的社會(huì)制度背景和現(xiàn)實(shí)邏輯,就中國(guó)未來(lái)養(yǎng)老模式的發(fā)展走向和政策選擇進(jìn)行探究。
社會(huì)嵌入;人口老齡化;養(yǎng)老模式;家庭養(yǎng)老;社會(huì)化養(yǎng)老
一、 引 言
按照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標(biāo)準(zhǔn),世界各國(guó)都在經(jīng)歷著從老齡化社會(huì)向高齡社會(huì)的轉(zhuǎn)變。中國(guó)在2000年前后已經(jīng)開始進(jìn)入老齡化社會(huì)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2016年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guó)60歲以上人口數(shù)為2.3億人,占總?cè)丝诘谋戎貫?6.7%,其中65歲以上人口數(shù)為1.5億人,占總?cè)丝诘谋戎貫?0.9%。根據(jù)聯(lián)合國(guó)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人口司的預(yù)測(cè),中國(guó)到2025年將進(jìn)入高齡社會(huì)的深度老齡化階段,65歲以上人口將占總?cè)丝诘?4.2%。在人口高齡化特征愈發(fā)明顯的現(xiàn)代社會(huì),老年人失能化和空巢化將進(jìn)一步加劇,養(yǎng)老服務(wù)將從最初的市場(chǎng)需求演變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面臨的難題之一。如何積極應(yīng)對(duì)老齡化的趨勢(shì),需要全社會(huì)普遍關(guān)注。
在經(jīng)濟(jì)體制和人口、家庭等社會(huì)結(jié)構(gòu)面臨轉(zhuǎn)型的背景下,以家庭為主的傳統(tǒng)養(yǎng)老模式受到巨大沖擊,正規(guī)長(zhǎng)期養(yǎng)老護(hù)理的社會(huì)服務(wù)也面臨種種挑戰(zhàn)。如何選擇適合中國(guó)國(guó)情的養(yǎng)老模式,需要社會(huì)各界的反思和探討,也得到了政府部門和學(xué)者們的關(guān)注。本文試圖在分析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對(duì)中國(guó)不斷變化的養(yǎng)老模式進(jìn)行梳理,基于社會(huì)嵌入視角探析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的社會(huì)制度背景和現(xiàn)實(shí)邏輯,就中國(guó)未來(lái)養(yǎng)老模式的發(fā)展走向和政策選擇進(jìn)行探究。
二、 中國(guó)當(dāng)前養(yǎng)老模式選擇
本文的養(yǎng)老模式是指在物質(zhì)層面、生活層面和精神層面對(duì)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支持的制度安排。學(xué)者們對(duì)養(yǎng)老模式進(jìn)行了不同類型的劃分,通常做法是按照養(yǎng)老社會(huì)化程度的高低,將養(yǎng)老制度分為家庭養(yǎng)老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回顧已有文獻(xiàn)可以發(fā)現(xiàn),針對(duì)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主要存在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弱化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是否替代家庭養(yǎng)老等實(shí)證性研究、家庭養(yǎng)老需要扶持和需要大力發(fā)展社會(huì)化養(yǎng)老等規(guī)范性研究以及家庭養(yǎng)老與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將共同發(fā)揮作用等前瞻性研究。
1.家庭養(yǎng)老模式
中國(guó)自古就有“養(yǎng)兒防老”的說(shuō)法,家庭是老年照料的主要力量,依靠家庭成員或親屬網(wǎng)絡(luò)照料的方式是中國(guó)最普遍的養(yǎng)老選擇。家庭這一最基礎(chǔ)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不僅提供了養(yǎng)老的經(jīng)濟(jì)支撐,成為老年照料的最佳組織系統(tǒng),同時(shí)也是老年人情感依托、體現(xiàn)自身價(jià)值和晚年自尊的來(lái)源。與西方社會(huì)奉行的“接力模式”不同,中國(guó)社會(huì)一直以來(lái)奉行“反饋模式”,講究家庭的代際支持。家庭養(yǎng)老的活動(dòng)場(chǎng)域在家庭這一社會(huì)最基本的組織結(jié)構(gòu)中,主要由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親屬(特別是子女)承擔(dān)養(yǎng)老責(zé)任并提供照料服務(wù)。此外,自我養(yǎng)老也可以視為家庭養(yǎng)老的一種,主要包括在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基于退休工資或社會(huì)保險(xiǎn)的養(yǎng)老方式,以及農(nóng)村地區(qū)老年人基于土地的養(yǎng)老方式。從養(yǎng)老的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方面看,國(guó)家衛(wèi)生計(jì)生委統(tǒng)計(jì)信息中心發(fā)布的《第五次國(guó)家衛(wèi)生服務(wù)調(diào)查分析報(bào)告》顯示,城市地區(qū)老年人的經(jīng)濟(jì)來(lái)源主要是自己或配偶(80.1%),農(nóng)村地區(qū)老年人的經(jīng)濟(jì)來(lái)源主要是自己或配偶(51.4%)以及子女或?qū)O子女(43.7%)。從生活照料方面看,在生活起居需要照顧的老年人中,有50.7%的老年人主要是由子女或?qū)O子女照顧,另有46.0%的老年人主要是由配偶照顧。陽(yáng)義南和詹玉平[1]指出城市地區(qū)依靠配偶照顧的比重較大,農(nóng)村地區(qū)依靠子女或?qū)O子女照顧的比重較大。另外,陳芳和方長(zhǎng)春[2]的研究顯示,雖然家庭養(yǎng)老在農(nóng)村養(yǎng)老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隨著人口流動(dòng)和農(nóng)村人口空心化,農(nóng)村多數(shù)老年人失去了子女在家時(shí)的生活照料、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和精神慰藉,轉(zhuǎn)變?yōu)槔夏耆私?jīng)濟(jì)自給、生活自理和情感自撫為主。即如周祝平[3]所指出的,養(yǎng)老主要方式由家庭養(yǎng)老變?yōu)樽约吼B(yǎng)老。李永萍[4]指出農(nóng)村地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現(xiàn)狀更多的是“以地養(yǎng)老”,而非“養(yǎng)兒防老”。這種自我養(yǎng)老模式折射出了生活無(wú)奈(子女無(wú)法養(yǎng))與制度無(wú)奈(正式的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障制度缺失),因而被陳芳和方長(zhǎng)春[2]認(rèn)為是一種過(guò)渡型模式。
關(guān)于家庭養(yǎng)老的發(fā)展趨勢(shì):一方面,姚遠(yuǎn)[5]與周兆安[6]指出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人口流動(dòng)加劇、家庭規(guī)模縮小、代際傾斜嚴(yán)重、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zhǎng)而自理能力下降和傳統(tǒng)孝道文化衰落等,家庭養(yǎng)老功能已經(jīng)弱化。田北海等[7]認(rèn)為家庭養(yǎng)老模式正面臨若干挑戰(zhàn)。周瑩和梁鴻[8]認(rèn)為家庭養(yǎng)老模式由于制度性瓶頸和其他外生因素的沖擊,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續(xù)性。另一方面,戴衛(wèi)東[9]認(rèn)為家庭養(yǎng)老作為一種具有深厚文化底蘊(yùn)的傳統(tǒng)養(yǎng)老模式,不應(yīng)該被徹底否定,而應(yīng)該通過(guò)政策支持加以強(qiáng)化。郭慶旺等[10]認(rèn)為與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相對(duì),家庭養(yǎng)老對(duì)人力資本、長(zhǎng)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傳統(tǒng)文化信念有促進(jìn)作用。張正軍和劉瑋[11]認(rèn)為在較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養(yǎng)老應(yīng)圍繞穩(wěn)定、擴(kuò)展或補(bǔ)充家庭養(yǎng)老的模式展開。
2.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模式
社會(huì)化養(yǎng)老主要包括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障體系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機(jī)構(gòu)的建立與完善。在家庭養(yǎng)老模式面臨挑戰(zhàn)的情況下,尋求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支持逐漸成為替代家庭養(yǎng)老的一種路徑,劉一偉[12]認(rèn)為這一替代使得社會(huì)化養(yǎng)老的重要性日漸突顯。鐘春洋[13]指出為減輕子女壓力,有穩(wěn)定收入的老年人傾向于采用社會(huì)化方式改善自身生活質(zhì)量和生活水平。因此,需要通過(guò)構(gòu)建相應(yīng)的制度安排,從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滿足老年人在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弱化后無(wú)法得到的需求。
然而,當(dāng)前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面臨短缺問(wèn)題,表現(xiàn)為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主體嚴(yán)重匱乏,社區(qū)養(yǎng)老公共設(shè)施供給不足、服務(wù)滯后,機(jī)構(gòu)養(yǎng)老服務(wù)床位不足、配置不均,相關(guān)制度保障尚未健全等。根據(jù)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的數(shù)據(jù),2016年底中國(guó)養(yǎng)老服務(wù)床位數(shù)為680萬(wàn)張,每百名老年人擁有養(yǎng)老床位3張,遠(yuǎn)低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每百人5—7張的平均水平,僅僅達(dá)到發(fā)展中國(guó)家每百人2—3張的平均水平。2009年實(shí)施新型農(nóng)村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以下簡(jiǎn)稱“新農(nóng)保”),2014年提出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建立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居民基本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標(biāo)志著中國(guó)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建設(shè)進(jìn)入到一個(gè)嶄新時(shí)期。作為一種準(zhǔn)公共產(chǎn)品,中國(guó)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力求突顯出社會(huì)福利性和社會(huì)公平性的特征。
為數(shù)不多的實(shí)證研究集中在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模式對(duì)家庭養(yǎng)老模式的影響及其社會(huì)認(rèn)同度等方面。陳華帥和曾毅[14]與劉一偉[15]的研究表明,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在增進(jìn)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同時(shí),對(duì)于家庭代際經(jīng)濟(jì)支持有著顯著的擠出效應(yīng)。程令國(guó)等[16]的研究表明,“新農(nóng)保”改變了農(nóng)村家庭的預(yù)算約束,增加了參保老年人經(jīng)濟(jì)獨(dú)立的可能性,減少了其對(duì)子女的依靠,增加了其獨(dú)立居住的可能性,因而在生活和精神方面對(duì)來(lái)自社會(huì)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這引導(dǎo)了農(nóng)村居民開始從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試探性地轉(zhuǎn)向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模式,但家庭養(yǎng)老的基礎(chǔ)性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張川川和陳斌開[17]分析了“新農(nóng)保”對(duì)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的替代影響,結(jié)果表明替代效果非常有限。王增文和Hetzler[18]的研究表明,“新農(nóng)保”的社會(huì)認(rèn)同度較低,其福利性并沒(méi)有得到充分體現(xiàn),需要進(jìn)一步提升制度的水平覆蓋率和替代率。劉一偉[12]從城鄉(xiāng)差異視角分析了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對(duì)家庭養(yǎng)老的替代,城鎮(zhèn)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同時(shí)減弱了子女對(duì)老人精神慰藉和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方面的支持,農(nóng)村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僅僅弱化了子女對(duì)老人生活照料的支持,而對(duì)精神慰藉和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方面的支持沒(méi)有顯著效應(yīng)。
三、社會(huì)嵌入視角下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
根據(jù)社會(huì)嵌入理論,不管是養(yǎng)老模式之間互為替代還是互為補(bǔ)充,都需要理解養(yǎng)老個(gè)體與行為所嵌入的特定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Granovetter[19-20]指出作為社會(huì)行為的一種特定形式,存在于所有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經(jīng)濟(jì)行為嵌入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各類制度網(wǎng)絡(luò)所組成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是一種社會(huì)性的建構(gòu)。本文聚焦于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的演變,根據(jù)Zukin和DiMaggio[21]的劃分邏輯,將社會(huì)嵌入構(gòu)成要素分為結(jié)構(gòu)嵌入、政治嵌入和認(rèn)知—文化嵌入,探討在這些構(gòu)成要素的影響下,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是如何在相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變遷中不斷演化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化改革、國(guó)家對(duì)社會(huì)福利體系的建設(shè)和西方福利體制改革浪潮影響了養(yǎng)老模式中的結(jié)構(gòu)嵌入、政治嵌入和認(rèn)知—文化嵌入,這些構(gòu)成要素的變化繼而引發(fā)中國(guó)從家庭養(yǎng)老模式向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模式轉(zhuǎn)變。在養(yǎng)老模式轉(zhuǎn)變的過(guò)程中,以家庭核心化與空巢化以及老人失能化與獨(dú)居化為特征的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動(dòng),弱化了家庭養(yǎng)老和照料功能,促進(jìn)了社區(qū)網(wǎng)絡(luò)支持的興起,由此引發(fā)了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服務(wù)的發(fā)展,以解決家庭養(yǎng)老面臨的困境(結(jié)構(gòu)嵌入)。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隨著計(jì)劃生育政策的實(shí)行,中國(guó)逐漸開啟了基于市場(chǎng)導(dǎo)向的福利事業(yè)社會(huì)化發(fā)展過(guò)程,在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之外的社會(huì)服務(wù)空間中,形成了強(qiáng)調(diào)市場(chǎng)購(gòu)買與個(gè)人責(zé)任相結(jié)合的模式,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體制逐漸形成(政治嵌入)。此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家庭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和社會(huì)福利政策的轉(zhuǎn)變對(duì)傳統(tǒng)的以“反饋模式”為特征的代際倫理造成了沖擊,個(gè)人本位主義和家庭世俗化的趨勢(shì)突顯。隨著“反饋模式”文化基礎(chǔ)的變遷和權(quán)威主義孝道的轉(zhuǎn)變,“敬老”“養(yǎng)老”的概念也被重新加以詮釋和踐行(認(rèn)知—文化嵌入),如圖1所示。

圖1 社會(huì)嵌入視角下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
第一,以家庭核心化與空巢化以及老年人失能化與獨(dú)居化為特征的家庭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動(dòng)(結(jié)構(gòu)嵌入)。現(xiàn)代化理論認(rèn)為,隨著知識(shí)經(jīng)濟(jì)的到來(lái)和高水平專業(yè)化社會(huì)分工的普及,社會(huì)對(duì)知識(shí)的需求、特別是技術(shù)知識(shí)的需求不斷增加,這使得成年子女被迫離開家庭,尋求更多的教育機(jī)會(huì)和工作機(jī)會(huì)。因此,與主干家庭相比,核心家庭可以更好地適應(yīng)現(xiàn)代化社會(huì),其成為社會(huì)家庭的主導(dǎo)模式,這與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強(qiáng)調(diào)相吻合。
首先,隨著計(jì)劃生育政策的實(shí)施,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發(fā)生變化。伴隨家庭生育率的持續(xù)下降,中國(guó)家庭結(jié)構(gòu)越來(lái)越小型化和核心化。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表明,中國(guó)戶均人口僅為3.1人。其次,以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推動(dòng)了代際分居的趨勢(shì),造成主干家庭減少,老年人更有可能與其子女和其他親屬相隔離。同時(shí),社會(huì)福利的興起也削減了現(xiàn)代家庭子女照看其老年父母的意愿,空巢家庭和空巢老年人日趨增多。根據(jù)2016年《第四次中國(guó)城鄉(xiāng)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diào)查成果》的數(shù)據(jù),2010年城鄉(xiāng)空巢老年人的占比達(dá)到49.3%(其中獨(dú)居老人占比達(dá)到9.7%,僅夫妻同住老年人占比為39.6%),較2006年增加8.0個(gè)百分點(diǎn)。2000—2010年城鎮(zhèn)空巢老年人的占比由42.0%上升到54.0%,農(nóng)村空巢老年人的占比由37.9%上升到45.6%。2015年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達(dá)到51.3%,老年人家庭呈現(xiàn)空巢化和獨(dú)居化趨勢(shì)。子女離開家庭,不再與老人同居一處,兩者空間距離加大,使得老年人雖然在物質(zhì)方面仍有得到子女支持的可能,但在日常生活和精神寄托方面卻往往失去依靠,導(dǎo)致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功能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在許多家庭難以為繼。再次,伴隨家庭核心化與空巢化的是老年人失能化。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guó)部分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已經(jīng)達(dá)到4 063萬(wàn)人,占老年人總數(shù)的18.3%。對(duì)于這些老年人而言,由于行動(dòng)不便,他們的飲食起居、家務(wù)勞動(dòng)和求醫(yī)問(wèn)藥都需要照料或陪護(hù),加之家庭照料資源的缺乏,對(duì)社會(huì)服務(wù)的需要也日趨強(qiáng)烈。最后,Zukin和DiMaggio[21]指出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與社會(huì)關(guān)系不僅影響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運(yùn)營(yíng),也對(duì)行動(dòng)者自我規(guī)范的努力產(chǎn)生重要影響。居家的利益相關(guān)者構(gòu)成的社區(qū)網(wǎng)絡(luò)支持,促成了居家互助養(yǎng)老模式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社區(qū)網(wǎng)絡(luò)支持應(yīng)該同時(shí)包括正式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和非正式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正式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包括社區(qū)服務(wù)中心、社區(qū)服務(wù)站、社區(qū)社會(huì)工作服務(wù)組織、社區(qū)家庭綜合服務(wù)機(jī)構(gòu)和社區(qū)矯正機(jī)構(gòu)等社區(qū)公共服務(wù)平臺(tái),非正式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包括老年社、老年大學(xué)等與老年人生活緊密相關(guān)的社區(qū)網(wǎng)絡(luò)組織。這些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都有助于老年人擴(kuò)展社會(huì)關(guān)系,搭建新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通過(guò)交流使其得到友誼、情感和精神慰藉,自尊得到增強(qiáng),并進(jìn)一步獲得勝任感和成就感。
第二,計(jì)劃生育政策和福利事業(yè)社會(huì)化引發(fā)的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體制逐漸形成(政治嵌入)。按照諾思對(duì)制度的認(rèn)識(shí),可以將家庭養(yǎng)老看做是通過(guò)道德傳統(tǒng)、風(fēng)俗習(xí)慣和村規(guī)民約等“軟約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是通過(guò)國(guó)家法律法規(guī)、政策措施和社會(huì)規(guī)范等“硬約束”形成的正式制度。養(yǎng)老社會(huì)化正是養(yǎng)老服務(wù)從家庭走向社會(huì),從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的過(guò)程。這一發(fā)展趨勢(shì)受到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型和西方福利體制改革浪潮等內(nèi)外因素的雙重影響。對(duì)政治嵌入的分析需要提到對(duì)上文結(jié)構(gòu)嵌入帶來(lái)深入影響的計(jì)劃生育政策,它影響了家庭養(yǎng)老行為中利益相關(guān)者的生育決定和養(yǎng)老策略。從曾經(jīng)用來(lái)宣傳推動(dòng)這一制度的政策動(dòng)員令的變遷(從19世紀(jì)80年代的“計(jì)劃生育好,政府來(lái)養(yǎng)老”“政府幫養(yǎng)老”直到今天的“養(yǎng)老靠社保”),便可以看出這一特有的制度安排對(duì)支持家庭養(yǎng)老或社會(huì)化養(yǎng)老各自相關(guān)資源與方式的改變。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要求政府和企業(yè)逐漸擺脫“包辦福利”“單位福利”的包袱,這推動(dòng)了包括養(yǎng)老在內(nèi)的社會(huì)福利供給的社會(huì)化和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與此同時(shí),西方社會(huì)正處于福利體制改革階段,福利國(guó)家模式危機(jī)開始出現(xiàn)。公共部門試圖通過(guò)福利供給的私營(yíng)化和多元化等改革來(lái)應(yīng)對(duì)危機(jī)。對(duì)個(gè)人利益和個(gè)人責(zé)任的強(qiáng)調(diào)以及對(duì)市場(chǎng)機(jī)制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guó)福利體制的變革,開啟了福利事業(yè)社會(huì)化的發(fā)展階段。
1984年中國(guó)福利事業(yè)在“社會(huì)福利社會(huì)辦”方針的引導(dǎo)下,由“救濟(jì)型”轉(zhuǎn)為“福利型”,中國(guó)福利事業(yè)體制從國(guó)家包辦、封閉的模式轉(zhuǎn)變?yōu)槊嫦蛏鐣?huì)的多元模式,由國(guó)家、集體、個(gè)人等多渠道、多層次共辦。在當(dāng)時(shí)的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領(lǐng)域內(nèi),社會(huì)興辦就意味著動(dòng)員民間資本通過(guò)市場(chǎng)機(jī)制為老年人提供養(yǎng)老服務(wù)。但是,由于養(yǎng)老服務(wù)業(yè)的非營(yíng)利性以及缺乏公共財(cái)政稅收等優(yōu)惠支持政策,市場(chǎng)機(jī)制下社會(huì)資本參與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的積極性并不高。基于此,依托社區(qū)開展養(yǎng)老服務(wù)的制度化安排開始出現(xiàn)。1993年《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社區(qū)服務(wù)的意見》發(fā)布,使社區(qū)服務(wù)得以制度化。2001年全國(guó)廣泛推行“社區(qū)老年福利服務(wù)星光計(jì)劃”,使社區(qū)養(yǎng)老與居家養(yǎng)老相結(jié)合,居家養(yǎng)老開始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的基礎(chǔ)內(nèi)容。2006年國(guó)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社區(qū)服務(wù)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大力推進(jìn)公共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使政府公共服務(wù)覆蓋到社區(qū),鼓勵(lì)和支持各類組織、企業(yè)和個(gè)人開展社區(qū)服務(wù),并支持和鼓勵(lì)社區(qū)成立致力于社會(huì)救助、優(yōu)撫、助殘和敬老等服務(wù)的民間組織,為老年人、殘疾人和困難群眾等提供社區(qū)志愿服務(wù)。針對(duì)農(nóng)村居民的養(yǎng)老困境,政府于2009 年開展“新農(nóng)保”試點(diǎn)工作,這是政府社會(huì)保護(hù)責(zé)任的體現(xiàn)。養(yǎng)老金作為政府提供的一種金融支持,對(duì)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變遷產(chǎn)生了諸多影響。2013 年《關(guān)于開展公辦養(yǎng)老機(jī)構(gòu)改革試點(diǎn)工作的通知》公布,明確公辦養(yǎng)老機(jī)構(gòu)“托底”作用這一職能定位,優(yōu)先保障弱勢(shì)老年群體(包括有經(jīng)濟(jì)困難的孤寡、失能、老齡等老年人和優(yōu)撫對(duì)象)的服務(wù)需求,推行養(yǎng)老機(jī)構(gòu)公建民營(yíng)發(fā)展,鼓勵(lì)社會(huì)力量運(yùn)營(yíng),支持專門面向社會(huì)提供經(jīng)營(yíng)性服務(wù)的機(jī)構(gòu)在條件適宜時(shí)轉(zhuǎn)制成企業(yè),實(shí)現(xiàn)資源最優(yōu)配置。在這些政策措施的影響下,中國(guó)社會(huì)化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體制逐漸形成。
第三,個(gè)人本位主義發(fā)展、家庭世俗化和權(quán)威主義孝道衰落(認(rèn)知—文化嵌入)。中國(guó)傳統(tǒng)養(yǎng)老行為遵循的是代際“反饋模式”,而不是西方的“接力模式”。老年人選擇和子女同住,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得到子女支持,體現(xiàn)了中國(guó)農(nóng)村社會(huì)養(yǎng)老的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習(xí)慣。以家庭和血緣為人際交往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圈核心的差序格局展現(xiàn)了農(nóng)村社會(huì)的家庭本位主義。然而,現(xiàn)代化理論認(rèn)為,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水平越發(fā)達(dá),孝敬老年人的責(zé)任越弱化,老年人的社會(huì)地位也就越低。孟憲范[22]指出隨著市場(chǎng)化改革的推進(jìn),市場(chǎng)機(jī)制通過(guò)經(jīng)濟(jì)理性進(jìn)入到家庭,導(dǎo)致自我中心式的個(gè)人主義的發(fā)展。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進(jìn)入到農(nóng)村地區(qū),導(dǎo)致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發(fā)生改變,較為年輕的一代靠科技進(jìn)步和外出打工得以致富,老年一代雖然耕作技術(shù)熟練和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豐富,但原有的家庭地位和社會(huì)地位正在失去。閻云翔[23]針對(duì)農(nóng)村家庭世俗化進(jìn)行了分析,提出由于過(guò)去五十年來(lái)的社會(huì)變革和破除封建迷信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家庭和家長(zhǎng)神圣色彩日漸褪去,家庭開始世俗化,家庭價(jià)值出現(xiàn)扭曲,使得農(nóng)村子女的自私自利缺乏約束。孟憲范[22]將這一現(xiàn)象稱作“經(jīng)濟(jì)理性越界”的產(chǎn)物。受到經(jīng)濟(jì)理性侵蝕,農(nóng)村家庭開始出現(xiàn)代際關(guān)系緊張、孝道衰落和養(yǎng)老危機(jī)等問(wèn)題。國(guó)家提供的養(yǎng)老保障仍不健全,很大一部分農(nóng)村老年人仍完全依靠子女養(yǎng)老。在傳統(tǒng)上這種養(yǎng)老制度依靠倫理規(guī)范和鄉(xiāng)規(guī)民約來(lái)維護(hù),當(dāng)維護(hù)這一制度的體系瀕于解體時(shí),農(nóng)村老年人的養(yǎng)老困境就突顯出來(lái)了。
隨著現(xiàn)代化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核心家庭的增多,城市子女與父母同居一處的更少,對(duì)父母的家長(zhǎng)角色更加趨于淡化,較為年輕的一代尊老敬老的意識(shí)也逐漸喪失。隨著社會(huì)價(jià)值觀的變化,老年人的應(yīng)有價(jià)值和社會(huì)作用往往被忽視,現(xiàn)代社會(huì)對(duì)老年人人文關(guān)懷的弱化也使其社會(huì)地位明顯下降。李銀河[24]對(duì)家庭關(guān)系的研究表明,雖然絕大多受訪者都贊同孝敬父母的必要性,但這并不等于對(duì)父母意志的絕對(duì)服從,應(yīng)該以權(quán)利平等為前提重新闡釋孝敬父母這一觀念,這是對(duì)中國(guó)以權(quán)威主義為特征的傳統(tǒng)孝道的顛覆。因此,由于主干家庭減少和福利社會(huì)的興起,現(xiàn)代家庭子女照看老年父母的能力和意愿正在削減,家庭養(yǎng)老的主體責(zé)任與地位正在淡化。
四、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的未來(lái)展望
根據(jù)社會(huì)嵌入理論,為了避免社會(huì)化不足和社會(huì)化過(guò)度,需要在養(yǎng)老個(gè)體行為與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之間尋找一種動(dòng)態(tài)的平衡,并形成融合性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這正是近年來(lái)學(xué)者們對(duì)大量混合交叉型養(yǎng)老模式的關(guān)注,這些新型模式是在處于家庭養(yǎng)老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二者之間的其他養(yǎng)老模式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此外,除了不同養(yǎng)老模式內(nèi)部的融合和發(fā)展,近年來(lái)由于需要特殊照料的老年人人數(shù)逐年上升,老年人對(du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wù)的需要明顯增加,“醫(yī)養(yǎng)結(jié)合”的跨界發(fā)展模式開始興起。這是在新的社會(huì)背景下出現(xiàn)的、符合未來(lái)社會(huì)發(fā)展趨勢(shì)的養(yǎng)老模式。“醫(yī)養(yǎng)結(jié)合”通過(guò)整合現(xiàn)有養(yǎng)老資源和醫(yī)療資源,將老年人的養(yǎng)老服務(wù)和健康醫(yī)療服務(wù)一體化,是對(duì)養(yǎng)老模式和醫(yī)療模式的一種創(chuàng)新。從社會(huì)嵌入視角來(lái)看,“醫(yī)養(yǎng)結(jié)合”這一新型制度安排,是在快速老齡化與少子老齡化、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增加等現(xiàn)實(shí)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中國(guó)孝文化傳統(tǒng)鞏固并強(qiáng)化了居家“醫(yī)養(yǎng)結(jié)合”的地位,而養(yǎng)老機(jī)構(gòu)的轉(zhuǎn)型也加強(qiáng)了老年人對(duì)養(yǎng)老機(jī)構(gòu)的認(rèn)同和信任。隨著全民健康理念、積極養(yǎng)老觀念和保健康復(fù)意識(shí)更加深入社會(huì),以及國(guó)家從政策層面上對(duì)“醫(yī)養(yǎng)結(jié)合”的鼓勵(lì)和推動(dòng),社會(huì)力量也紛紛投資或興辦老年康復(fù)、老年護(hù)理等專業(yè)醫(yī)養(yǎng)結(jié)合機(jī)構(gòu)。
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fā)展的普遍趨勢(shì),中國(guó)政府也已經(jīng)深刻意識(shí)到了積極應(yīng)對(duì)老齡化的重要意義。《“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建立“以居家為基礎(chǔ)、社區(qū)為依托、機(jī)構(gòu)為補(bǔ)充的多層次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從而將《“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中的“機(jī)構(gòu)為支撐”轉(zhuǎn)變?yōu)椤皺C(jī)構(gòu)為補(bǔ)充”。根據(jù)本文的社會(huì)嵌入分析視角,可以看出這一轉(zhuǎn)變既折射出中國(guó)養(yǎng)老社會(huì)制度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又突顯了中國(guó)未來(lái)養(yǎng)老政策的新思路,同時(shí)符合中國(guó)居家養(yǎng)老的認(rèn)知和文化傳統(tǒng)。在打造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和長(zhǎng)者為善的社會(huì)進(jìn)程中,家庭養(yǎng)老和社會(huì)化養(yǎng)老這兩種主要的養(yǎng)老模式在中國(guó)形成了互補(bǔ)機(jī)制,對(duì)中國(guó)的家庭關(guān)系、家庭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中國(guó)養(yǎng)老模式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qū)膯我蛔呦蚨嘣瑥亩嘣呦蜥t(yī)療領(lǐng)域與養(yǎng)老領(lǐng)域的有機(jī)結(jié)合,以此來(lái)適應(yīng)不同老年人的需求,為其提供個(gè)性化的養(yǎng)老與醫(yī)護(hù)服務(wù)。為此,中國(guó)政府應(yīng)積極制定并有效執(zhí)行相關(guān)的養(yǎng)老政策,將養(yǎng)老的制度安排作為積極的社會(huì)福利,強(qiáng)調(diào)老年人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和責(zé)任,逐步增強(qiáng)老年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并對(duì)老齡化帶來(lái)的一系列風(fēng)險(xiǎn)采取疾病預(yù)防、早期干預(yù)、康復(fù)和臨時(shí)護(hù)理等措施,提高老年人的身體素質(zhì)和心理素質(zhì),減少醫(yī)療費(fèi)用支出,最終推動(dòng)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全面積極發(fā)展。
[1] 陽(yáng)義南,詹玉平. 農(nóng)村養(yǎng)老誰(shuí)是主體 [J]. 經(jīng)濟(jì)論壇,2003,(20):4-5.
[2] 陳芳,方長(zhǎng)春. 家庭養(yǎng)老功能的弱化與出路: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村養(yǎng)老模式研究 [J]. 人口與發(fā)展,2014,(1):99-106.
[3] 周祝平. 中國(guó)農(nóng)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戰(zhàn) [J]. 人口研究,2008,(2) :45-52.
[4] 李永萍. “養(yǎng)兒防老”還是“以地養(yǎng)老”: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模式分析 [J]. 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5,(2):103-112.
[5] 姚遠(yuǎn). 對(duì)中國(guó)家庭養(yǎng)老弱化的文化詮釋 [J]. 人口研究,1998,(5):48-50.
[6] 周兆安. 家庭養(yǎng)老需求與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弱化的張力及其彌合 [J]. 西北人口,2014,(2):45-49.
[7] 田北海,雷華,鐘漲寶. 生活境遇與養(yǎng)老意愿——農(nóng)村老年人家庭養(yǎng)老偏好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分析 [J]. 中國(guó)農(nóng)村觀察,2012,(2):74-85.
[8] 周瑩,梁鴻.中國(guó)農(nóng)村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保障模式不可持續(xù)性研究 [J].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06,(5):107-110.
[9] 戴衛(wèi)東. 家庭養(yǎng)老的可持續(xù)性分析 [J]. 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探討,2010,(2):22-26.
[10] 郭慶旺,賈俊雪,趙志耘.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信念、人力資本積累與家庭養(yǎng)老保障機(jī)制 [J]. 經(jīng)濟(jì)研究,2007,(8):58-72.
[11] 張正軍,劉瑋. 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 [J]. 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3):60-67.
[12] 劉一偉. 互補(bǔ)還是替代:“社會(huì)養(yǎng)老”與“家庭養(yǎng)老”——基于城鄉(xiāng)差異的分析視角 [J]. 公共管理學(xué)報(bào),2016,(4):77-88.
[13] 鐘春洋. 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的完善路徑探討——基于老年人服務(wù)短缺視角的分析 [J]. 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2):140-146.
[14] 陳華帥,曾毅. “新農(nóng)保”使誰(shuí)受益:老人還是子女? [J]. 經(jīng)濟(jì)研究,2013,(8):55-67.
[15] 劉一偉. 擠入還是擠出?新農(nóng)保對(duì)子女經(jīng)濟(jì)供養(yǎng)老人行為的實(shí)證分析——以河南省HX市為例 [J]. 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4,(9):77-81.
[16] 程令國(guó),張曄,劉志彪. “新農(nóng)保”改變了中國(guó)農(nóng)村居民的養(yǎng)老模式嗎? [J]. 經(jīng)濟(jì)研究,2013,(8):42-54.
[17] 張川川,陳斌開. “社會(huì)養(yǎng)老”能否替代“家庭養(yǎng)老”?——來(lái)自中國(guó)新型農(nóng)村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的證據(jù) [J]. 經(jīng)濟(jì)研究,2014,(11):102-115.
[18] 王增文,Antoinette Hetzler. 農(nóng)村“養(yǎng)兒防老”保障模式與新農(nóng)保制度的社會(huì)認(rèn)同度分析 [J]. 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5,(7):46-56.
[19] Granovetter,M.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 Acta Sociologica,1992,35(1): 3-11.
[20] Granovetter,M.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1): 33-50.
[21] Zukin,S.,DiMaggio,P.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36.
[22] 孟憲范. 家庭:百年來(lái)的三次沖擊及我們的選擇 [J]. 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3):133-145.
[23] 閻云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gè)中國(guó)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guān)系(1949—1999) [M].龔小夏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24] 李銀河. 家庭結(jié)構(gòu)與家庭關(guān)系的變遷——基于蘭州的調(diào)查分析[J]. 甘肅社會(huì)科學(xué),2011,(1):6-12.
(責(zé)任編輯:孫艷)
2017-07-15
秦 軻(1977-),男,河南焦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研究。E-mail:qinke@cass.org.cn
F840.6;C913.6
A
1000-176X(2017)11-013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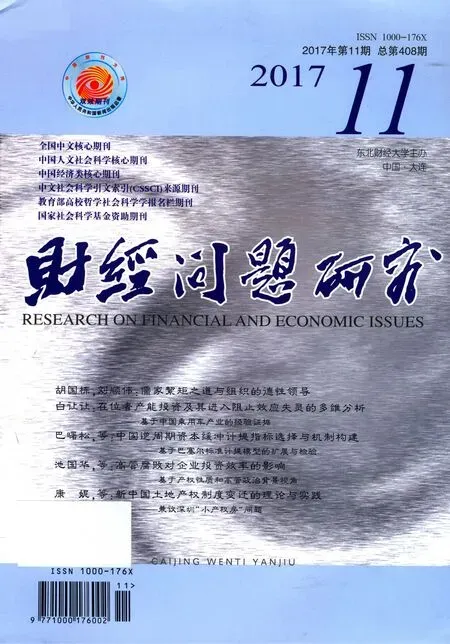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7年11期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7年11期
-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的其它文章
-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大國(guó)大城——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統(tǒng)一、發(fā)展與平衡》評(píng)介 - 新加坡老年保障體系建設(shè)的多元協(xié)同治理機(jī)制研究
- 企業(yè)眾創(chuàng)機(jī)制內(nèi)涵及作用機(jī)理研究
- 城市住房?jī)r(jià)格波動(dòng)對(duì)居民消費(fèi)的影響
- 高管腐敗對(duì)企業(yè)投資效率的影響
——基于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和高管政治背景視角 - 城投債規(guī)模、政府審計(jì)力度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