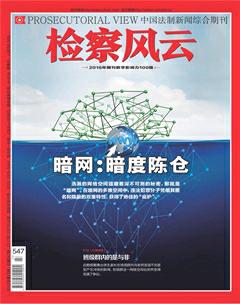提升供給質量,推動充分發(fā)展
李雙金
社會主要矛盾涉及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的因素。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斷深入的歷史軌跡。
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反映出經濟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們需要的多元化、個性化與更高標準。“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物質、文化等維度,還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環(huán)境、安全等維度。“美好生活”的新提法,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關注與理解。
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的轉變,一方面表明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已經脫離了“落后”的范疇,不僅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還在許多重要技術與生產領域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另一方面,這種轉變表明“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已經在發(fā)展領域日益突出,未來我國將從主要關注生產力逐步過渡到同時關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從單純地關注GDP增長總量與增長速度轉向關注更加全面的、更能體現“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fā)展。
圍繞“不充分”,緩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
主要矛盾的產生反映了我國社會供需兩個方面的結構性變化。在供給與需求這兩個方面,筆者認為,供給側尤其是供給側的不充分發(fā)展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是未來一段時間,緩解主要矛盾的重要切入點。
在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人民群眾并不是完全沒有對更美好生活,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環(huán)境、安全等內容的需要,只是供給數量的不足嚴重抑制了人們的這種需要。當供給數量問題通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得到解決,甚至出現產品和服務的結構性過剩之后,人們才有可能釋放出對于更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才有可能實現這種需要。
因此,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供給一直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不過過去更多的是供給數量方面的問題,現在則更多的是供給質量方面的問題。而供給質量方面的問題首先就體現在“不充分”上,充分的發(fā)展才有實力和能力實現更高質量、更加平衡的供給。這也是筆者認為今后緩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需要以“不充分”為關鍵切入點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不平衡問題仍然將是今后制約充分發(fā)展的關鍵性瓶頸。關注供給側的不充分發(fā)展,通過供給的充分發(fā)展最終促進不平衡問題的解決,決不意味著要重新回到過去“以GDP增長為中心”的發(fā)展模式中,也不是要等到完全充分發(fā)展之后再去關注不平衡問題,而是要通過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發(fā)展結構的優(yōu)化以及發(fā)展動力的轉換,不斷提升供給質量,并在此過程中同步關注各個領域的不平衡問題,將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不平衡問題作為是否充分發(fā)展的重要指標,緩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促進充分的、平衡的發(fā)展。
如何提升供給質量,推動充分發(fā)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階段,正處于轉變發(fā)展方式、優(yōu)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進一步提升市場產品與服務的質量
企業(yè)是市場產品與服務的主要供給者。從企業(yè)發(fā)展角度上看,一是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與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等手段,提升生產與管理效率,為消費者提供更高質量、更高標準的產品和服務。二是不斷提高生產管理的質量標準、技術標準,加強質量監(jiān)管,防止“假冒偽劣”等現象對市場秩序的擾亂,形成公平競爭的良好市場環(huán)境。
從產業(yè)發(fā)展層面上看,一是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通過新技術對生產流程、管理模式和商業(yè)模式的改造,促進傳統(tǒng)產業(yè)優(yōu)化升級,提升產業(yè)發(fā)展水平,進而提升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內涵,滿足消費者對多樣化、差異化產品和服務的需要。二是在新興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中進一步發(fā)掘經濟發(fā)展的新動能,培育新興產業(yè)、孵化新型企業(yè)、創(chuàng)造新的商業(yè)模式,為市場提供更多類別、更高質量的新產品和新服務。
進一步提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
提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從根本上要求政府進一步轉型為“服務型政府”。人民群眾“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wěn)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yōu)美的環(huán)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獲得感。這些都是未來服務型政府需要關注的重要維度。
對此,一是進一步滲透新的發(fā)展觀念和理念,提升政府工作人員服務意識,加強對政府公共預算的審查與監(jiān)督,強化問責機制,促使更多公共資金流向公共產品和服務而不是單純的項目建設。二是進一步放松服務業(yè)發(fā)展的相關管制政策,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領域,通過公私合作(PPP)等形式,不斷優(yōu)化合作機制,拓展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范圍,提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共同打造高質量的供給體系,最終促進充分且平衡的發(fā)展。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