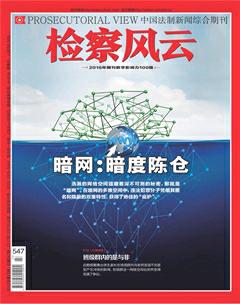因父之名:民間復仇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張寧
成龍在其新片《英倫對決》中,一改以往的嘻哈動作風格,以悲情的模式演繹了一位深沉、老態的父親。劇中,成龍飾演的華人關玉明和他唯一的親人——女兒生活在倫敦,開了一間小飯館,父女情深,生活幸福。然而,在一次恐怖襲擊中女兒不幸遇難。幾近崩潰的父親,在求助官方無果的情況下,獨自走上了復仇之路。
影片最后的結局頗耐人尋味。當關玉明完成復仇計劃返回餐館,遠處的特種部隊狙擊手已經把槍口對準了他的腦袋,并請示是否開槍,還好指揮官下達了禁止命令:“等等,也許我們欠他個人情。”也許是專業思維慣性,我在此前預想的故事結局是關玉明很可能在完成任務后從容自首,而不是回到餐館和劉濤飾演的紅顏知己親吻擁抱。因為自關玉明開車離開餐館,我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民間復仇,在何種程度上具有正當性和有效性?
無論是指揮官放了他一馬還是法庭有可能放他一馬,都是因為關玉明是站在正義的制高點為無辜的女兒和其他遇難的平民報了仇。“復仇”在東西方人類早期社會漫長時間里都曾因其“自然狀態”而具有正當性,因此也是合法的。古巴比倫王國的《漢穆拉比法典》保留了同態復仇的原始習俗,“自由民損毀任何自由民之眼則應毀其眼”“打死自由民之女則應殺其女”。古希臘雅典刑法也帶有血親復仇的遺風。日耳曼法對于殺人的處罰就包括血親復仇,是由被害人親屬團體對加害人或其親屬進行對等報復。中國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復仇是合法的。《周禮·秋官》載:“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孔子及先秦儒家主張以直報怨、正義復仇。商鞅變法以后,刑罰訴諸國家司法,禁止民間私斗,“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 自此,一度被視為孝義的血親復仇行為歸于非法。
《英倫對決》影片故事發生地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已經存在以血親復仇的方式懲罰犯罪者的法律制度,直到1066年諾曼征服以后開始限制了血親復仇,逐步代之以罰金抵罪。縱觀歷史,法律愈發達就會愈加禁止民間復仇行為,國家不會把生殺予奪之權交給私人。也就是說,關玉明的復仇行為有違現代法治文明。至少,他此前對副部長的辦公場所、住宅等地實施的警告性爆炸行動毫無疑問具有危害他人和公共安全性質,即便法庭很可能鑒于其在剿滅恐怖組織中的立功表現還他個人情,因此判其無罪、免予起訴或者從輕處罰,但在一個法治社會這個程序還是要走的。如果說復仇的正當性來自實在法之上的自然正義,對其有效性的檢視則無法背離實證主義精神。那么,在今天的英倫土地上,關玉明的行為可能依然正當,卻并不具備法律意義上的有效性。
然而,對于這部影片,我們還要考慮另外兩個故事背景:一是關玉明的人生經歷,二是政府高層的政治陰謀。特種兵炸彈專家關玉明在越戰中被美軍收編,前妻和兩個女兒被海盜殺害,第二任妻子難產而死,女兒此次又死于恐怖襲擊,而恐怖襲擊又與政府高層的政治陰謀有直接關系。作為北愛爾蘭反政府組織“真UDI”前首領的漢尼斯,投靠英國政府后謀得高官職位,又利用雙重身份在兩個政治力量的沖突中獲利。戰爭、海盜、政治陰謀、恐怖襲擊,在這樣一個法律被邊緣化的生態環境中,我們還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失去所有至親的關玉明做一個守法父親和模范公民嗎?
寫下這篇文章題目的時候,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經有一部名為《因父之名》的影片,同樣以北愛爾蘭人與英國政府的對抗為背景,講述男主角愛爾蘭青年格里遭英國警察誣陷為恐怖分子,受到極不公平的虐待和逼供,被判無期徒刑。善良忠厚的父親為救兒子也被關進牢中,在父親的鼓勵下,格里堅持不懈地抗爭,多年以后冤情終于得以昭雪。而這,來自真實的事件。試想,如果在法律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關玉明的行為不具備有效性,當司法為權力所左右,在黑暗與腐朽中缺席,那么有一位關玉明那樣的父親或許是每個受難者的渴望……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