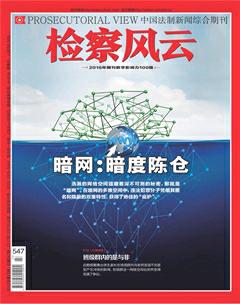地鐵時空:管道內的人們
楊皓
地鐵又被稱為城市軌道交通,是指在軌道上行駛或以導向系統行駛的、服務于城市的交通。最早的軌道交通系統是于1863年在英國倫敦建成的大都會地鐵,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過去的三十年間,軌道交通系統慢慢趨于成熟,克服了各種各樣的技術、設備、資源等難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擁有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城市已經多達320個,覆蓋43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正如學者亞當斯所言:道路面積的增加使交通阻塞暫時有所緩解,但因為這里交通暢通,就引來更多的車輛。不久,新增或拓寬的馬路又會恢復到昔日的擁擠程度。城市面積是有限的,道路的增長也將是有限的,而城市對交通量增長的需求卻是無止境的,因而大力發展快速、高容量的軌道交通已成為我國未來大城市交通發展的趨勢。
軌道交通以其路權獨占,高效安全、方便快捷、節約能源等優勢,正慢慢成為現代城市發展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越來越多的城市會把軌道交通系統的建造作為其城市未來建設的重要規劃之一。同時城市公共交通布局的變化又會對城市空間結構的發展產生強烈的沖擊,形成不同的城市空間結構類型。軌道交通系統的鋪設同樣會對城市空間結構布局產生影響,其結果便是城市按照高密度點狀的放射軸線布局。
可以說地鐵正在改變著城市的未來,我們的生活也因為地鐵的介入,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壓縮時空之中,記者在此暫且稱之為地鐵時空。
偶然相聚 心神相離
地鐵連結著不同空間的人們,來自不同區域不同階層的人都有可能在地鐵中相遇,可以說地鐵空間是一個偶發性的空間。這種偶發空間與人們生活、學習、工作所習慣的空間相比,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之處在于地鐵空間中的每個人幾乎都互不相知,熟悉之處在于地鐵這一公共交通卻又經常與人相伴。
在這樣的偶發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重新定義,人與人的相遇相近變成了一個被動壓縮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把地鐵空間描述成一個壓縮性的空間。除上文述及的空間被壓縮之外,地鐵的高速運行的同時也壓縮了乘客在空間之中移動所需的時間。乘坐地鐵的時間被壓縮且被置入一個同樣被壓縮的空間之中,人們處在一個獨特的壓縮時空中。
在此壓縮時空之中,面對形形色色偶然相遇的面孔,人們會本能地感到不自在,排解這種不自在最易得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使用手機。
不難發現,絕大多數乘客會選擇使用手機來打發乘坐地鐵的時間。究其原因,一方面地鐵時空本身是一個單向且線性的密閉時空,但是正如人們喜歡在馬路上東張西望一樣,人類具有時刻追求新信息、新刺激的本能,這樣的本能在地鐵的密閉時空中最簡便的滿足方法即是使用手機,通過移動互聯網來不斷向自己的腦中傳輸新鮮信息;另一方面,在人與人距離被壓縮的地鐵時空中,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會給自我反饋這樣一種情緒:與陌生人保持這樣的近距離是不安且危險的,而逃離這種不安情緒的最簡單易得的方法同樣是使用手機,以沉浸入自我的世界。
地鐵時空獨特且特點鮮明,你我都在偶然相聚,但心神卻遠遠相離。
時空記錄者——杜丹
杜丹是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的一位老師,從今年的九月初開始,她幾乎每天都會用自己的手機拍攝地鐵內的人物照片,并發布到自己的朋友圈上。
“因為我本身對攝影就很有興趣,然后我也一直在研究有關城市空間這一塊的學術內容,所以就想到了對地鐵空間做一些記錄。”杜老師告訴《檢察風云》記者,“地鐵這個空間其實挺獨特的,我覺得它是一個值得去記錄與思考的空間。很多攝影作品會選擇拍攝城市中的景觀、建筑啊等等,但我從沒有見過有人專門對地鐵空間內的東西做一些拍攝和記錄。由于工作原因,我現在每周會有三天前往上海,路途上在地鐵上花費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就想用自己的手機,對地鐵這一空間中的人間百態做一個記錄與呈現。”
地鐵時空中,最讓杜老師感興趣的是人的狀態。她認為,地鐵作為連接A點到B點之間的一種媒介,人們在乘坐地鐵時所表現出來的狀態與平時生活空間中的狀態往往是不同的,而這種空間之下人的狀態恰恰構成了人們在這個特殊空間中的生存、呈現與表達。
很多人會選擇地鐵作為每日通勤的交通工具,其中相當一部分會選擇利用地鐵運行的時間休息一會。捕捉地鐵時空中各式各樣人休息時的姿態,成為了杜老師作品的很大組成部分。
關于為何會選擇拍攝人們在地鐵上休息的姿態,杜老師置評道,“地鐵時空中的人們在選擇休息的時候,并不同于人們在家中時完全放松的休息狀態,他們是一種比較緊張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用僵硬這個詞來形容。只有偶爾在比較晚的地鐵班次上,才有可能看到某位乘客表現出很放松的休息狀態。”
不同身份的人群在地鐵時空中的不同行為表現也是杜老師在拍攝時比較熱衷的角度,其中一幅攝影作品反映的內容是一位城市裝扮的姑娘帶著一位老阿婆乘坐地鐵,阿婆的裝扮是典型的蘇州周邊農村老嫗。
“我一開始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并不知道她們相互認識,后來在下車的時候才知道她們是認識的,可能是姑娘帶著阿婆來城里辦事吧。” 杜老師告訴記者,“兩個人在列車上雖然毗鄰而坐,但兩人的行為卻有很大的差異。老嫗一路上東張西望,對城市的種種想必是充滿了好奇,同時也有一絲緊張,而小姑娘卻一直百無聊賴地等待列車到達目的地。”
我們總是能在地鐵上遇到各種各樣的人群,觀察不同人群的不同行為表現,就像觀察一個地鐵時空中的微觀社會一般,有趣且值得玩味。
杜老師同樣也關注到人們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對于手機的依賴問題。在眾多作品中有一張在高鐵上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一位中年婦女由于視力存在障礙,在把手機上的文字放大到非常大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把手機近乎貼在面部才能看清屏幕上的內容,照片非常具有沖擊力。
“我們的世界已經近乎于一種被中介化的世界,現代科學技術正在與我們的生活進行著反復且不斷地相互作用,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所說,人和技術之間是一種偶合的關系。手機在不斷給我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變著人們的生存與存在方式。” 杜老師表示,“正如我在拍乘客玩手機的狀態時,我恰恰用的也是手機。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明確解答那個困擾學術界已久的問題,技術究竟是好是壞?”
除了對地鐵時空里人物行為的關注以外,地鐵內的人物情緒同樣讓杜老師頗有興趣。“地鐵可以說是一個‘失樂園,因為陌生人之間的距離問題,很少有人會在地鐵時空內展現出笑容。一般來說只有孩子或者戀人,才會在地鐵內展現出非常歡樂的情緒,但是一旦有了小孩或者戀人所特有的歡樂情緒存在于地鐵時空里,就極可能會消融地鐵時空內那種‘冷酷的情緒。”
你我都是時空的構成部分
距杜老師把第一幅地鐵攝影作品在自己的朋友圈發布已經過去兩個多月的時間了,在這兩個月的時間中,有人對她的拍攝行為提出了關于人物肖像權的擔憂。
杜老師表示,“關于肖像權的問題可能是我的作品繞不開的一個問題。但是我必須聲明,所做的這些拍攝行為并非存在占有他們肖像的目的。我為什么要拍這些照片,僅僅是為了把地鐵時空這個容易被城市忙碌生活所忽略的部分給記錄下來。我想表達的也僅僅是我和他們一樣,都是這個地鐵時空中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已。”
杜老師告訴記者,她的微信好友有800人之多,把地鐵空間的攝影作品上傳至朋友圈,對她自己來說,就像在開辦一個小型的線上攝影展。日前蘇州大學校內舉辦攝影展,杜老師選送了部分作品參加展覽,她給自己的作品取名為“早安,地鐵”。
地鐵、手機等現代化設備設施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甚至侵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在使用種種現代化設備設施的同時,不知不覺地也在調整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活方式構成了人類的存在方式。
日本傳播學學者林雄二郎關注到電視對于當時人類的巨大影響作用,在《信息化社會:硬件社會向軟件社會的轉變》中,提出了“電視人”的概念。記者不禁聯想到,在地鐵無可取代地進入我們生活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被稱作“地鐵人”呢?